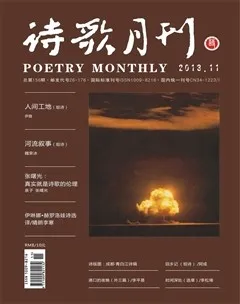南音:人声鸟声
2013-12-31浪行天下
对于生活,我已倦于思索
更深的麻木,让我从最初的窥视者
到半睁半闭,到现在
成为聆听者的姿态。多年来
在城市的茶馆里
一曲曲南音,一遍遍吹拂
仍然使我心如止水
但今夜,在乡下偶遇这曲南音
三弦被我听成了蛙鸣
琵琶听成了蟋蟀
这乡下草间的虫鸣协奏
让故乡的泥土、树木、河流
还有风雨雷电,和那久违的炊烟
如此逼近,丝丝缕缕地进入
我的心底,哦
我闻到了它熟悉的稻茬的芳香
这温馨的土壤
这母亲一年年,洒下除草剂的土壤
才没有让城里的仇恨
在我心底生根发芽
像南音一样生活
1971年10月生于福建泉州惠安县。入选多年度《中国诗歌精选》、《中国诗歌年选》、《中国散文诗精选》等。著有诗集《高处的秘密》、《情海泅渡》。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
夏敏(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浪行天下的“南音”系列《多情惟有南音最》组诗符合我眼中好诗的标准。这组诗各首以南音名段来题写诗名,关键词是“南音”。南音的珍贵不仅在于它是北方宫廷雅乐南流至泉州民间的“活化石”,更在于它的脱凡绝俗,独立红尘,与上层主流若离若即,与下层乡民濡染互动,即便流失于闽海乡野,也能展示其高贵、儒雅情致。浪行天下正是看到南音这一点,与其诗歌禀赋相契合,于是在他家乡的南音启发下,演绎出一组耐人寻味、格调高古的佳作来。南音系列组诗的每一首都借助了南音中的重要唱段或著名典故。每一首跟其他各首之间均以南音链接成一个貌似“十全十美”的整体,而每一首又各有重点,相对独立。统领和维系各首,没有一个可以让人感到明显起承转合式的逻辑构架,却有一个相对集中的题材和表述方式。作品的主要取材范围是散佚在泉州南音中那些为人熟知的、被悬念化的故事,作品巧妙地以诗的方式化解了它们(如《惰梳妆》、《金井梧桐》、《一身爱到君乡里》),或者是南音自身如泣如诉的表演所引发的浩叹(如《听见杜鹃》、《自别归来》)。写作本身却远远超越这些南音叙事本身或南音简介,他的书写更强调象征背后的沉思、玩味、挣扎或者批判。于是,所谓“南音”,不过是诗人借以抒发自己对于灵魂的反思和对生命的关切着眼点而已。
首先,这组诗的部分作品在对南音作品或表演引发的略带抑郁色彩的叙写中,呈现了一种逃逸与遁世心态,但同时显露着批判的锋芒。《惰梳妆》化解了南音演绎的某个故事,琵琶女演奏气氛的沉重、低靡,同时弥漫着“绝望的空”和“欣喜的空”,尽管万般皆为空,人应该变得很超越才是,可是诗人笔锋急转,以“她”对“我”的背叛和失仁的高声责难收束,写得非常富于戏剧性。《听见杜鹃》借助“杜鹃啼血”,展示“镂空自己,把疼痛向内折叠”这样一种自戕、自嘲状态,进而批判世间所谓的“美好物事”成为“掐住”歌喉的源头,带有浓郁的反思精神。的确,现世追求绝非天堂,例如,在古代具有“耕读传家”社会理想的农耕社会,读书成仕子剥夺了多少自由的意志,功名意识坑害了多少富有朝气的年轻生命,在《锁寒窗》一诗中,诗人通过“寒窗”内苦读的“骨肉”们如牢狱般地被“锁”,揭示了“道统”思想如何背弃“魂灵”,作践性灵。《对菱花》中,菱花作为“她”的一面“镜子”或是“忠实的宠物狗”,只有它(们)才会与她“无话不说”,朝夕与共,形影不离,这种表述的背后,隐含着对知音难觅的纠结和对庸俗世情的失望。
其次,在冷峻氛围背后,诗人也十分注意展示暖色调的生活,表达诗人对“诗意栖居”的审美境界的无限向往。《白云飘渺》中,演奏南音的“她”被想象成“播撒白云的人”,久之,云即她,她即云,人与自然“天人合一”,这是作者的最爱。而当云变雨,落入人世,梦想就会被击碎。所以,该诗实际上借助对理想破灭的拒绝,来表达对自由生命的向往。《小妹听我说》中,作者连续用了三个“小妹,你不能指责”,隐含着在“指责”(抱怨)状态中的人被“过去的生活”牵绊着不得自由。于是,他“奉劝”小妹“头颅,抬起来仰望”,有一种冲决旧我,进入新生的意味。《一身爱到君乡里》同样告诉人们,与其在人世间“艳阳高照的审判”,不如做一个行其所行、爱其所爱的人。
《多情惟有南音最》这一组诗歌借助“南音”为由头,站在思想的高度俯瞰人性的笔墨所以能够被读者接纳,或者被“破译”,跟浪行天下本人驾驭文字的功夫分不开。这与他多年的历练与摸索有关,更与他对文字的天然敏锐有关。他在诗歌中常常巧用某些技巧而不露痕迹,这是浪行天下的高明之处。例如在《中秋夜》里,诗人把中秋月喻为被回乡游子拉亮的灯,古今意象做了非常有趣的嫁接,如果不是有丰富细腻的生活关注和旁骛八极的自由联想,这样的精妙的表述,恐怕无从找寻;《金井梧桐》短短数行极具戏剧色彩,诗歌借用了一个有趣而富哲思的南音故事:九百二十五年前某生赶考途中住在“梧桐家”所演绎的“绻缱”、“旖旎”、“想入非非”、“无人知晓”的浪漫一夜,与住在“芭蕉家”、“柳叶家”的赶考生员们形成鲜明对比,读者可以从中复现某个生动有趣、充满戏剧色彩的故事,更可以在这则被戏剧化的故事背后,对违规犯矩的自由人性给予强烈关注,并在回眸悄然逝去的青春时,给予更大的宽容。与之相仿,
《自别归来》一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将树木变身琵琶暗喻躺在弹奏南音女子怀中的男人,这男人或许就是某个寺院里犯了戒律的寺僧,其“罪”也罢,“无罪”也罢,珍贵的爱情来了,人间的一切戒律似乎都显得苍白。
读完这组诗,我非常赞赏浪行天下能将视角投向故乡的土地,尽管字里行间不时透露着批判的锋芒,但看不到浅薄与浮躁,这使得整组诗歌显得清丽、干净。他引导读者去领略一个看起来显得有些模糊的文化遗产,而骨子里却展示着他心灵的故乡和想象的异邦。
主持人语:
浪行天下的诗在掠取传统生活的精髓赋唱层面有独到之处,以其剔选出的闲情逸致给予那种种可能性的语言角度:应是情感更多地丰富阅动对象体的所需;而这也是,期待在暂且诗意空白线索上的对象体都在迫切地从一个个我单向的情调感受内处逃离出来,向着诗人仅是作为“人”的其中一员的存在原生体聚拢。说诗给予阅动情愫,实质上也是尽可能地使这一“原生体诗性”渐渐显现其较为清晰的思索秩序。确切也就凭恃这一情感层面能与思考秩序的交背对应,诗人的诗便也有其察识气味,然后转呈至现代声息的运作机制。
——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