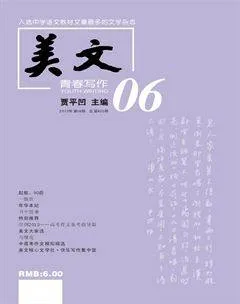波罗的海的歌
2013-12-29何杰

何杰,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会员。1996年至1998年赴拉脱维亚大学讲学、任教。同年于波罗的海语言中心讲学。1999年应邀赴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汉语教学研讨。2008年参加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2009年论文入选美国布莱恩大学语言学会议。201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赴美交流学术。
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语言学研究。出版语言学专著《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增编版)》等三部;出版教材、词典多部。发表及入选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论文三十余篇。
1972年开始发表小说。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论文和文学作品均有获奖。出版散文集《蓝眼睛黑眼睛——我和我的洋弟子们》。
入选《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词典》等。
1998年获评天津市级优秀教师。2006年荣获全国十佳知识女性。
第十届国际唱歌节在里加城隆重开幕!这条每个字都洋溢着喜悦兴奋的消息,一下席卷了整个拉脱维亚六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举国上下,从城里到乡村,处处都翻滚着欢腾的热浪,响彻着热烈的歌声。
我和先生都被这骤然降落的欢乐惊呆了。往日寂静的拉脱维亚大学公寓,大门“呼呼”地推开又合上。邻居出出进进,打招呼的声音都提高了调门。原是冰冻的脸也突然开化了一样,每个部位都飞扬着喜悦。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我们已被赶来的学生大呼小叫地拉上了大街。
哈,大街小巷都在鼎沸。真有火山骤然喷发的感觉。
我的心也随着欢乐盛开。
欢乐可以传染。
奇怪的开幕式
进老城,在伽利汣大街,彼得大教堂一侧,我们的好朋友韦大力帮我们爬上一堵围墙。站在墙头上,居高临下,对面街口涌出的队伍便一览无余了。唱歌节的入场式这样开始了。
歌手的洪流正从一条不宽的街里涌出。挪威、pSs3KG0DqbLUiSU4aZ3lEwKzeLfJG8zTM037AZqqOHI=瑞典、丹麦、瑞士、德国、英国、俄罗斯十几个国家。还有拉脱维亚各民族的歌手:男的、女的、老的,连同孩子的队伍。他们穿着各国的民族服装,鲜艳、热烈,既古朴又奇异。他们满载着笑声、歌声、乐器声,从四面方向这儿涌来。
上天怎么一下抛扔下来这么多人!我来拉脱维亚一年多了。这可是从来没有的!
人们手里拿着彩带、花束、乐器……奇怪!竟有人抱着石头,拿着斧头……干什么?
在街的入口,有一道用鲜花和树枝编起的大门。
学生们忙着给我解释。
来这的赛歌队伍都要过三道门:第一道门是里加的幸福门。把在门口的人会问你:
“你怎样过里加的门?”
拿着斧头的人回答:
“把坏心肠丢在门外。只有好心肠才有幸福。”
我们看见,拿着斧头的人一边挥动斧头,像把什么妖魔赶走,一边跳着舞蹈。当大家看着,满意了,高兴地为他们鼓起掌时,把门人才叫他们通过。接着是第二道门。
第二道门是用石头摆起的门,叫健康门。人们带着石头走过来。存放在那。
学生们告诉我,里加从前就是小渔村,都是低洼湿地。人们在穷困和疾病中挣扎。后来人们每出去一次,就带回一块石头。来里加的人也都带块石头回来。慢慢铺成小巷,小街。从那时,人们开始建起城堡,驱赶疾病,抵御敌人。
如今,里加老城的条条大街小巷,都是石头铺地。那磨得锃光瓦亮的石头都在说着它们久远的历史;说着这里的人们像石头一样坚强地活着。
人们过的第三道门是挂满彩灯的门,叫光明门。人们拿着花环,捧着鲜花。进到第三道门后,就把鲜花铺在路上,这时才戴上花环。他们咏唱着,表达他们永远崇敬太阳。他们顶礼膜拜太阳,象征把黑暗留在身后,前方永是光明。
开路的队伍走过,后面的队伍就是各国的歌手。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旗手,高举着国旗,雄赳赳地走来。
他们边走边唱。每到大街中心,就表演起他们自己国家的歌舞。唱着,跳着。每个人的心都在乐谱中跳跃。这里响起的歌,每一首都在迸发着激情和欢乐。
高兴的时刻倒哭了
我和学生随着音乐高兴地哼唱着,开始数着国旗,想知道有多少国家与会。
有红底白十字的旗飘过,那是瑞士的。蓝底边上有个黄色十字,那是瑞典的。我们发现北欧国家芬兰,还有丹麦都和瑞典的构图一样,只是颜色不同。有英国的米字旗,德国的是横着的三色条旗,俄罗斯、拉脱维亚也是构图相同,只是颜色不一样……
忽然我的眼睛凝固了。心在激跳。久违啦!大红底色,醒目的黄色五角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最为鲜艳。
我们的国旗,我祖国的国旗!
五星红旗后面,走着的是中国浙江少儿歌咏队的孩子们,我祖国的亲人。
我和我爱人一下激动起来,我们很久都没看见自己的国旗了。我们很久都没看见自己祖国的亲人了。眼一下模糊了,只觉得热血在周身奔流。
先生很长时间都在部队,是个坚强的军人,我从没看他掉过眼泪。可是那天,我们两人竟不顾学生就在身旁,一起哭起来。
我们这一代人和新中国一块成长。战火纷飞的年月,我们在母亲的怀里,是无数先辈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了我们。恢复建设的艰难中,我们长大了,我们抛洒汗水,收获心酸也收获坚强。在那风风雨雨的日月里,我们和祖国一样艰难。我们有过冲动,有过困惑,有过埋怨,然而在这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才知自己对自己祖国的爱是那样刻骨铭心,肝肠寸断。那爱是从我们小时,祖国用血和汗水浇灌的。祖国的痛苦、灾难乃至梦想早就种在我们心里的。
没有离开祖国的人决不知道思念祖国的滋味。都说,出国才知更爱国。真真如此。
那天,我们就站在墙头上,听着久违的乡音:浙江少儿歌咏队的孩子们唱的《春天多美丽》《茉莉花》在国内也听,却从未那么叫人感到亲切、温暖,令人激动……
那天,真是群情热烈,人们一直给歌咏队鼓掌。孩子们唱了一遍,又唱了一遍。那天最后,当孩子们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时,我们也忍不住大声跟着我们祖国的孩子们一起唱起来了。那是我们做孩子时就唱的歌。
从小唱的歌就像藏在你的灵魂里。
唱啊,世界的歌唱节也是我们的节。
回到家时,说起此事,我们大家都笑了。站在墙头上,竟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和先生还不由自主地做起划船的姿势。
学生和我的好朋友韦大力都说,他们真怕我们掉下来。而当时,我们周围的人,都先是瞠目结舌,然后竟在胸前画起十字,一度庄严。
学生说,歌唱节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中国人唱的,歌的名字叫“中国心”…… 学生说:“我们也感动了,也想掉泪。”
歌可以不分国界,不分肤色,不分年龄,一样融化人们的心。
那天,我忽然明白了,无论命运把你抛撒到哪里,无论在什么时候,祖国都在你心里。祖国就是你生命的根。
高兴的时刻倒哭了,新鲜的事还有呢。
唱歌节没有“民歌”
学生跟我说的。后来知道,我弄错了。不是唱歌节没有“民歌”,而是拉语没有“民歌”“音乐”这样的词。我说,那也是新鲜的事。语言现象是反映客观现实的。拉脱维亚没有“音乐”“民歌”吗?
学生跟我卖起了“关子”。 学生说叫我也研究研究拉脱维亚语。古拉语中有许多有意思的语言现象。
那时,我到拉脱维亚时间不长,我还不知道,波罗的海语言中心就在拉大。更对拉语一无所知。
那时也不明白,拉的人口不多,拉语言,却有许多语言学家关注。参加了欧洲语言会议,才知道拉语属印欧语系(汉语属汉藏语系)。拉语有悠久的历史。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变化很少。拉语在印欧语系语言中,是保存的古代因素最多的语种。
一个民族的民间音乐一定反映它语言的特点。和许多保存古代特点的语言一样,拉语中没有“音乐”“民歌”这样概念的词。和“声乐”有关的词只有两个:“芝达特”;“噶为勒特”。意思是“歌”和“喊”。
拉脱维亚人有许多仪式的唱曲、抒情曲子等,就是拉脱维亚所说的“歌”。他们的“喊”则是渔夫和农牧民的劳动号子。
我上班时每天都过道加瓦河,我的邻居大婶告诉我,她们小时还有纤夫,现在没有了,也听不到纤夫号子了。他们拉族人的号子,音符很高,音域广阔。
我小时在家乡大清河边,常听船夫号子。那伴着他们沉重的脚步,从他们胸腔里发出的声音。总是一下就拨动了人的心,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叫人感动。
音乐是加了音符的语言。
我是搞语言的,到哪里,凡与语言有关的都深深吸引着我。
那天我特别注意听拉脱维亚人的演唱。真的,他们的歌真的都有一种“喊”的感觉。很少有音符的变化。而“喊”的却叫你感到那样悠长、辽阔、宁静……像看到无边的山丘、原野和蓝天……歌是直接反映生活,直抒心意的。你们有过这样的感觉吗?你在听歌,却可以看到一幅幅你从没见过的优美的图画……
拉脱维亚的“音乐”“民歌”有一种久被压抑而呼出来的独特。它真的不同于任何一个与会国家的音乐。言为心声,歌更是心声的宣泄。
我真庆幸我赶上这里四年一次的歌唱节。我能听到世界鲜有的这样有个性的歌。
德语的歌铿锵;俄语的歌辽阔;瑞典语的歌绵长;拉语的歌直抒心意……
世界的歌像灿烂的云,磅礴的雨,变幻的霓裳,真有一种看一个巨大的万花筒的感觉。
都是歌手
从未看到过的表演,也从未见到过人们这样快乐。
那一天,我们的一个最严肃的邻居爷爷,大妈说,是管飞机螺丝的(估计是机械师)。他的外号叫“奶酪”(大概是凝固的意思),也笑得在草地上四脚朝天。我的学生笑得就差打滚了。
不信。我说了,你也得笑。不过你先等等,我先说我的感受。
那些天的歌唱节(一周),每件事都是我从未看到过的。
从未看到过那么多国旗;穿那么多样民族服装的人;从未听到那么多种语言的歌……从未看到过的火热。那是真正的全民的、世界的。演出也不是只在一处。老城、新城、郊外连我们附近的库库莎山,那几天也在欢腾。
库库莎山有一个很大的露天演出场。就着山丘的土坡修建的一排排的坐席,坐满了欢乐的人们。我真是奇怪,这些人们真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平时可很少见到人影。
台上挤着各种年龄的歌手,各种体型的,男的、女的。穿着,无论是女人的大裙子,还是男人的衬衫、裤子,都有非常漂亮的图案,特色鲜明。只是我分不清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但一点最清楚:那就是,无论哪个节目,都是在最自在的状态。
自在得谁想唱,谁就可以上台,挤上去唱。他们表演没有什么队形,反正是一大堆人。也没有人报幕。一拨下来,又挤上一拨。
那天,更有意思:演着演着,几个在台下的孩子大概觉得还不够尽兴。于是一个接一个地往台上爬。男女歌手们撑死也不过三四岁。大木台前的台阶需要他们四肢并用。于是我们观众们看到如下的情景:前面的男孩爬上去,下面的女孩上不去,赶忙去拉前面男孩的短裤。聚精会神看演出的大家看到了什么,就可想而知了。不能不大笑的是,几个孩子一个拉一个的裤子,如法肇事……哎呦,这群小可爱,叫我们看见了最可笑的演出。
这不,那一天,不但我们,而且我们叫“奶酪”的邻居爷爷也无法“凝固”了,笑翻在草地上。我和先生还有学生们笑得肚子疼了好几天。
我还要特别说明,那几天,我的同行,拉大教授斯达布拉瓦也来和我们一起参加节日。斯达布拉瓦是拉脱维亚著名的汉学家。永远是正襟危坐,我很少看见她的笑模样(不像我,爱说爱笑)。那天,她自己笑得眼镜找不到了,笑得擦眼泪了呗。我们大家赶忙一块儿在草地上找。后来竟发现就顶在她自己的脑袋上。学生说,这回可有了词,再见教授时害怕,就提起这段。
大家这通笑。
那天,最叫我骄傲,叫大家最感动的,是我们中国浙江少儿歌咏队的孩子们。他们不但唱了许多中国歌曲,最后他们竟能用主办国的拉语(拉语很难)唱起了拉脱维亚的儿童民歌《小蜜蜂》。嚯——全场一下欢腾。那简单欢快的曲调打开了全场人的歌喉:
“小蜜蜂呀,小蜜蜂,
你飞到西来,飞到东。
高兴呀!
快乐呀!
嗡嗡嗡——
嗡嗡嗡——
你採来甜蜜,
放到我心中。
嗡嗡嗡——
嗡嗡嗡——
你採来甜蜜,
你甜,我甜,大家甜。
谢谢小蜜蜂。”
草地上,树杈上坐着的,台上,台下,老人、孩子;男人、女人都在使劲地拍着手,摇晃着身体忘情地大声唱……
从没有这样的甜蜜!从没有过这样的节!从没有。
没等什么一定要迟到十几分钟的领导,没等什么名人。也没什么极浪费的剪彩,更没什么懒婆娘裹脚的讲话、祝词……有的,就是自在的表现,自在的高歌,自在的欢乐……
快乐的音符在美丽的波罗的海海湾跳跃;不同语言的歌在心与心中间画优美的五线谱连线。
歌可以穿越时间,可以跨越国界,可以融合民族的心。人们要唱歌,天下人们的心都向往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