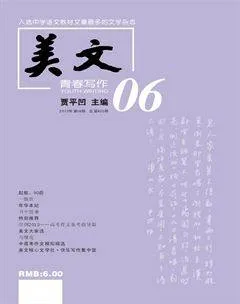夜路
2013-12-29
还记得我们家搬进县城的那个冬天的夜晚,七八点钟的光景,我和妈妈沿着护城河散步,路灯、车灯和各式各样的商店门廊上的闪灯,伴着喧哗琐碎的声音,整个地填充了我们俩的外围,犹如把我们困在了一个港剧的移动电话亭里。我们都不言语,只是走,有时快,偶尔也慢,母女的“节奏”在这里呈现出了远超过“陪伴”的意义。直到我们走到小区的楼下时,她突然对我说:“以后,终于不用担心大黑天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便执拗地说:“我从来都不担心啊!我不害怕天黑。”妈妈看着我,对我一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隔着墙灯打下的光,我似乎看到了妈妈嘴角的微笑,有着意味深长的味道。
两三年之后,我认识了最要好的朋友齐齐。我们谈天说地,无话不聊,她快乐得像个疯子,我几乎没有看到她有过稍许不高兴的样子。直到有一天夜晚,她哭着找到我,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她突然抱住我,喊着“我不要自己一个人走夜路,我一辈子都不要”。那一刻,我的脑海中随即出现了妈妈对我说那句话的样子,抱她的胳膊也因此紧了又紧。
后来,我知道,那晚她和男朋友出去玩,中途吵了架,她男朋友一气之下,自己先回去了,只留她自己在荒无人烟的小路上。我听后立即吼道:“别那么娇滴滴好不好?不就是走个夜路吗,至于吗?”她这时也来了脾气,带着哭腔说到:“你是没经历过那么多无助的夜晚啊?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她告诉我说,她刚上高中的时候,对学校很不适应,每当感觉压力大,或者心情烦躁的时候,就等晚自习放学之后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回家。一般晚自习结束的时候,差不多就十点了,当她到家时,基本上家人也都睡了。她说,爸妈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也不懂得心情、感伤之类的东西,哪怕她回家说一声“我想家了”,父母也几乎不会再追问下去。等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要提前赶回学校,去上早自习。她说差不多每两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一次,有时也会想放弃这个“行动”,但是每当心情烦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只能这样做。
她说,那时的路上隔着很远才会有路灯,路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行人了,偶尔经过的车辆多少会给她一些安慰。有一次,她父亲说:“孩子,你哪一天若是想回来,就给我个电话,我去接你。”她嘴上答应着,但还是每次都是“随心所欲”地骑自行车回家。
“那时,因为心里有满满的不快乐、烦闷,也就没有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心上,即便害怕,也会在心里觉得是一种紧张的发泄”。齐齐告诉我这些时,眼角里的泪水也就流下来了。那一刻,我明白了她这些年脸上的快乐的来源,那是一种毫无压力的暂时放松,是“大灾难”过后的彩虹啊!同时,我也体会到了她眼泪的味道:她真正害怕的不是这个黑夜,是高中三年迎面袭来的伤痛和压力!我闭上眼睛想想那个黑夜里骑单车的少女,被风吹得“花枝招展”的头发,朴素的双肩包,一脸的苦愁,一点都不拉风。真的,就像荒原上嚎叫的独狼,满身疲倦,却还让自己的心保持着高度警惕。
于是我想到了母亲,一个深深地说过“再也不怕天黑”的女人。想必她也有过曾经让她无可奈何的孤独的夜晚。有一年春节回家,姥姥正好在我们家,闲谈时聊起妈妈的童年趣事,从那之后,姥姥提到的一件事情在我心里再也挥之不去。
有一年夏天,妈妈和她的同伴张阿姨,一起约好去邻村看大戏。对于出生于60年代初的人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可以看场露天的大戏也算的上是一件特别隆重的事。她们等到大戏全部结束,快十点多的时候,才结伴步行回家去。其实那天白天的天气虽然算不上晴朗,但也是无风的,谁知道恰好在她们走到中途的时候突然间有了狂风大作的意思,她们紧赶着,加快了步伐,可是也就是两三分钟的时间,大风就应验似的刮起来了,而且开始有雨滴下落,她们心里害怕极了,只能半闭着眼睛往前跑,风越来越大以至于她们前进的速度也缓下了许多,当时张阿姨哭得厉害,她害怕马上就会有大雨,妈妈让她闭嘴,不要说些不好的预言,没想到雨真的就瞬间下来了,妈妈说张阿姨当时像极了神仙,一说要下雨,马上大雨就瓢泼着下来了,她们找不到任何可以躲避的地方,周围都是庄稼地,想回到家也还要十几分钟的时间,妈妈提议说:“咱什么也不要管了,牵着手一起往前冲吧!”说着,拽起张阿姨的手就往前跑。跑了一会,听到后面有驴奔跑的声音,回头一看,隔着细密的雨帘,一头拉着农车的驴正在她们身后只有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她们反应过来就直接往路边躲,就在这时,我妈脚下一滑一陷,就掉进了路沟里,紧接着牵着我妈妈手的张阿姨也随之掉了进去。驴车此时也停下了,下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边牵着驴的缰绳,一边试图去拉妈妈她们,可是脚下太泥泞,老人的脚也是不断地往深里陷。没有办法,他们都不能再挣扎了,否则都会陷得更深。妈妈后来说那时候的无望,对于那个年龄的她来说,简直就是天要塌下来了,让她喘不上气来,她不知道怎样才能上去。老人牵着驴在路上想看看是否会有路人过来,可等了几分钟却一个人影都没有。妈妈说:“其实也就是五分钟左右,但却显得特别长,我都想放弃了,要不等到天明算了……”最后,是二舅因为担心她们的安全,去路上寻她,才拉她们上来了。
姥姥在说这些的时候虽然满脸堆着笑容,显出一副很有趣的样子,但事实上,我知道她的心里也是后怕的。而妈妈在听这些的时候,还是有着不能释怀的表情。有人说,童年发生的事情就是你的性格基因。我想,在这件事上,对妈妈来说,是合适的。只是,在这之外的我,却想到了另外的一些事情。
我中学时是走读生,学校就在我们家不远处,我可以每天晚自习之后回家。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学回来,妈妈就在胡同口等着我,当时还把我吓了一跳,我想这么晚了谁还在外面站着啊。后来,我每次回去都能看到妈妈,我不断地给她说,路上有小伙伴做伴,就不要再等我了。她就会不高兴地说:“可是到了这个胡同里面就没有人再和你做伴了啊。”我取笑过她的无聊,她依旧不听,每天晚上都去接我,一天没有落下过。有时候到了寒暑假,她倒是比我还积极,说:“没有晚自习,不去接你,还真不适应呢!”以前每次听到这儿,都会觉得她矫情。可是到了那一天,我才知道这背后的意义。
而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人生的夜路,并且很经常。我们谁都无法逃避掉阳光明媚的春天,同样也无法对寒风刺骨的冬季视而不见,我们的一生就是四季,酸甜苦辣的味道都尝个遍,才算味蕾健全。月黑风高的故事总是悄然而至,更多的时候,走夜路是种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修炼。比如我们深深地暗恋过一个人,也就是走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夜路。
有一年,我用了三百多天的时间来准备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考试,虽然算不上心无旁骛,但也是属于挑灯夜读型。考试终于在那个冬天最冷的两天结束了,在我焦急等待了一个多月后,得到的结果是——与它失之交臂。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天气晴朗,阳光透过淡蓝色的窗帘倾斜在阳台上,我的床就像架在地中海边的阳光里,周边有波涛汹涌的纹路,那一刻,美得让我痛哭流涕。我抱着枕头呆坐着,仿佛房间被分成了两块:一边地中海的阳光普照,一边暗无天日如同地窖。我的脑袋也是被分数之斧尖锐地分成了两半:笼统地绝望和希望。整整一个月,我就处在这种分裂中,那不是无望,而是绝望,你看到的路全部都是一黑到底,我不吃饭,甚至几乎不睡觉,沉浸在黑夜和白昼的交替中,顺着自然的变化,来固执自己的心。我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第一次尝到了“崩溃”的感觉,所有的人都不能帮助你,你也不祈求自救,你要放弃自己。对于二十三岁的我来说,这个失败是人生的句号,仿佛人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陷进了一个死胡同,把自己不断抛空,然后让它自己下落,我不是我自己的了。直到现在,想起那段日子还是后怕,它是一个魔咒,诱惑你,而后消灭你。
那一段路走得比每条夜路都要惊心动魄,都要翻云覆雨,可是此刻,在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之后,我坐在梦想的地方,喝茶、读书,云淡风轻,温柔地过着我喜欢的生活。这不是不费力地满足,而也许只有我自己知道——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晚归走夜路的我了,而我的闺密齐齐,也必将在生活的广场上,做着只属于夜晚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