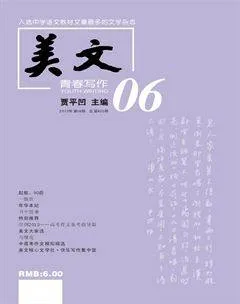一样
2013-12-29
上小学的时候,妈妈每次给我买了新衣服,我都不会像其他小朋友一样上午买了,下午就穿,而是必须过一段时间才穿上,有时候是一两天,偶尔也可能是一年就过去了。妈妈每次都很生气,说:“难道你不喜欢新买的衣服吗?”我总是不吱声,因为我确实非常喜欢,可是就是不愿意穿,也说不上原因,就是不想穿。有时候,看到别的孩子穿着漂亮的新裙子,会特别羡慕,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狠狠地下决心明天就穿上那已经不算新的“新衣服”。好多年过去之后,和别人聊起这件事,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哪有小孩子会不喜欢新衣服的。直到有一天,我和一位做心理分析师的朋友谈起这件事,他说:“看来你小时候就是一个保守、谨慎的孩子啊!”我不明就里,他问我:“你每次穿上新衣服是不是觉得特别不舒服,好像周围的人都在看你,对你指指点点?”我突然意识到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矛盾而又不舒服的感觉让我想逃离人群。朋友哈哈大笑:“你小时候很自恋嘛,又怕别人看出你的自恋,就只好等到别人都有变化的时候,你才会发生变化,以便不会显得太突兀。”我悲伤地说:“我一个小孩子哪有那么多心思,只是不愿意穿而已嘛!”朋友说:“这是科学分析,你不信就算了,我倒觉得和现在的你很像。”一场聊天,因为被看破,不欢而散。
多年后,我读到郁达夫的代表作《沉沦》的时候,又感觉到了这种微妙心理的存在。小说的主人公在日本留学,因为“支那人”的身份而自卑,便觉得走在哪里都会被人耻笑,连女孩子不和他说话都会觉得是瞧不起他。而我在这里面却读出了那份属于他自己的深深的自恋:太爱自己,以至于不能有任何东西对他有一丁点的伤害。所有自恋的人都有不自觉地放大伤害的本能。这些人通常渴望被关注,一旦被关注却又觉得不舒服,大概抑郁之类的病也就多由此而来吧。
在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那时我们家因为某种原因搬去农村,村子是很贫瘠的,大多数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所以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孩子来说,这是心中的一种隐痛——没有钱买新衣服。我爸爸是有正式工资的老师,非常疼爱我,我就有源源不断的新衣服穿。那时,我每天会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学校,有时甚至在头上戴三四个金光闪闪的发卡,当时我兼任班里的文艺委员,好不风光!我对自己身上的一切都感到满意,在这种好心情的驱使下,成绩也不断进步,名列前茅。我每天都觉得明媚如画,耳边常常萦绕者动听的歌,无限欢乐。只是有一天上体育课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边几个女孩子围在一起做游戏,那边几个女生躺在草地上欢声笑语,而我独立于操场中央,没人理我。我尝试去靠近她们,可从她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来,远没有欢迎的意思。那一节体育课让我觉察到了什么。后来在教室、在食堂,这种糢糊的意识不断得到验证。那是沉浸在自我欣赏的世界里永不会注意到的。旁若无人、一意孤行的下场就是舞台上只剩下你,跳着独孤舞,自怨自艾。后来渐渐地,我不再不停地换衣服,而且尽量去接近他人,和别人分享一些零食或者杂志,可是她们并不领情,也就是说自从我意识到这种“孤立”之后,我就一直处在孤立之中了。所以那之后的一两年,我过得一点也不快乐。那个年龄的我觉得不公平,爸妈也没办法帮助我,那些女生“执拗”得很。我没有朋友,孤独极了。
那一两年的时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当我有一天看到“枪打出头鸟”时,就突然明白了那种生活的意义所在。我不知道这种观点到底对不对,只是知道人群信奉,我便无法逃遁。之后好几年,我谨小慎微地过活,像是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文革”情景,我便生活在其中,连走路都尽量不要发出声响。那似乎给了我根深蒂固的意识——万万不要特立独行,要淹没在人群中,要和别人一样。只有这样,才是安全的,有人陪伴你的。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不再穿鲜艳颜色的衣服,黑灰色的衣服是我最经常的选择,现在想来,那个年龄穿上这种衣服,多少会有点黯然失色,装老成的味道。
2009年我考上了大学。那一年的暑假格外漫长,于是,我选择了坐火车出游,一个人,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告诉父母是因为编辑的邀约去参加活动,并找出了一个以前参赛的证明,蒙混过关。我想那时的父母或许真的觉得我该长大了,故意给我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我在火车站买了从家到昆明的最后一张火车坐票。之所以去昆明,我早就有一种感觉——昆明是中国文人的结。因为西南联大的关系,好像不去那里,不到天之南走一趟,便是辜负了写作者的身份。真是一场长途跋涉,我拖着箱子,做了近三十个小时的火车,在沉沉的早晨到达昆明。在火车上我看到了好多新奇的事物,觉得自己的世界顿时被人打开了一扇窗,透过这里,看到了满满的新鲜。特别是到了贵州境内的时候,火车上开始有了很多穿民族服装的人,我不住地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把随身携带的车票弄丢了。当列车员查票时,我哭得泪水泛滥,但一点作用不起,即便周围的人都给我作证,列车员也一点都不含糊。实在没有办法,旁边的人教给说让我去找列车长,于是,我一边哭着,一边穿过长长的通道去找他。他查了我的身份证,问了我的详细情况,但是还是不起作用,非得让我在下车的时候去取钱,把车票补上,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面对三四百块钱的车票,那对我来说真是很大的数目,我脑中一片空白。列车长见我无动于衷,继续开导我说:“这是法律规定,出站的时候一定要有票据的。”我依然不说话,不是不想说,而是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求情的话既然不起作用,我也就没有话了。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和我同车厢的一些人觉察到我好久都没回去,怕发生什么事情,两三个人作为代表就去找我。我们虽是萍水相逢的路人,但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还是心里一热,有种“亲人来了”的感觉。那是几个来自山东的硬汉,身上透着一种大气。他们也不说话,只是站着,偶尔说声“别哭,这都不是事儿!”之后就狠狠瞪着列车长,大约过了有十几分钟,列车长不耐烦了,说“你们回去吧,这次就算了”。而我没有一丝高兴,他们也好像很失望的样子,突然其中的一个人问“下车不会再查她了吧?”列车长说“应该不会吧。”就走了。接下来的一路,我满心谴责,怎么可以把票丢了呢?怎么这么不仔细呢?我一遍遍地拷问自己,而他们就在一旁玩扑克、喝啤酒。有那么一刻,我羡慕他们的生活,浑身都是豪气和自由之气,不像我,哭哭啼啼中都是不自在。然而下车的时候,我还是被截住了,一个我没见过的列车员非得让我补票,我又开始哭,而这时他们也下车了,就围过来,重重的行李使得他们的每一步都很艰难。他们高声喊着“说话不算数还是人吗?”然后就开始骂出一些很粗鲁的方言。列车员也很气愤,和他们争吵,大声地争吵,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多到已经影响了正常下车,我在一边哭着,像个局外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甚至有些蛮不讲理地为我力争。最后他们放下行李,说:“不让她走,我们就不走了。”有人好像弄明白了事情,也跟着说:“算了吧,一个孩子家的,就算了吧。”人群的议论声越来越大,列车员最后迫于压力,终于很气愤地做出了让步。
他们一路带着我,把我围在中间,生怕会有人把我拉走似的,一路护送到我坐上公交车。我哭着和他们告别,不停地说着谢谢,他们都是外来打工的人,身上都是被子和衣服,仿佛全部的家当都在里面,沉甸甸地却很幸福的样子。他们憨厚地笑着,说:“孩子,别哭了,这样的事情以后多着呢,你要记住,世界上的方法不只有一种,只要你坚持自己的原则,只要是对的,就能解决问题。哭是最不管事的。”我哭得更厉害,深深地点着头。
那一次的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人生往往如此,你在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学到的东西最多,对你的影响也更深。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打工者怎样地拥有了这样的体会,我只知道他们用最朴素的方法向我诠释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这件事情让我学会了远不止这些,但是坚持这一道理,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
后来我去上大学,用心观察着,发现周围很多人还是一种无意识的盲从,做什么都要和别人一样,选一样的课,甚至去吃同一家餐厅的饭,人云亦云的现象到处都是。而我却用之前的泪水教训了自己——和别人一样,在一个小范围里是适用的,但是当你拥有更大的视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那么容易地就被淹没了,而且很难再浮出人群。
于是,有了今天的我——过的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我,和生命的丰富欢愉的感觉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