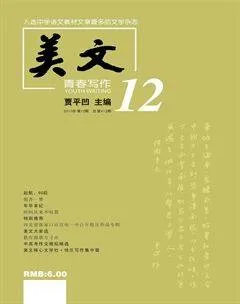在荷兰吃了一个风车
2013-12-29何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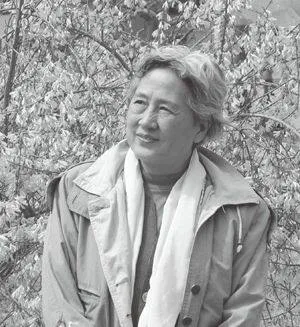
何杰,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会员。1996年至1998年赴拉脱维亚大学讲学、任教。同年于波罗的海语言中心讲学。1999年应邀赴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汉语教学研讨。2008年参加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2009年论文入选美国布莱恩大学语言学会议。201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赴美交流学术。
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语言学研究。出版语言学专著《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增编版)》等三部;出版教材、词典多部。发表及入选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论文三十余篇。
1972年开始发表小说。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论文和文学作品均有获奖。出版散文集《蓝眼睛黑眼睛——我和我的洋弟子们》。
入选《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词典》等。
1998年获评天津市级优秀教师。2006年荣获全国十佳知识女性。
小“皮肚”和风车哥哥
我小时就爱看书。那时的童话书好像也不少。我特别喜欢看一本叫《皮杜和风车哥哥》的童话。“皮肚”(皮杜)名字好记,风车形象鲜明。
风车哥哥给我的印象更是深刻。他是那么英武,侠义。“皮肚”是个小可怜。当风魔鬼要来抓他时,风车哥哥把“皮肚”藏在了他的大风叶后。然后挂上战甲,转动起他的风叶胳臂英勇奋战,赶走了风魔鬼,救下了小“皮肚”。至今记得,小“皮肚”站在风车哥哥巨大的风叶胳臂上,和云朵小姑娘一起玩耍的图画样子。小“皮肚”是个牛皮大王,胆小,却敢吹大牛。他见到小云朵就吹开了牛:
小云朵问:“昨天,怎么刮起了那么大的风?”
“皮肚”说:“嗨,那是我生气了,出了口粗气。”
正在逃跑的风魔鬼一听,忍不住笑了。谁知一笑,笑出个屁。一下把吹牛的“皮肚”吹下了风车,吹到了沼泽地里。“皮肚”大喊救命,灌了一肚子水。风车哥哥赶紧伸出风叶长胳臂把牛皮大王捞上来。小“皮肚”一边吐着水,一边继续吹牛:
“哈,大哥,要不是你把我捞上来,我就把那里的水都喝干了。”
风车哥哥笑了,说:“那好吧,我再把你放回去。”
小“皮肚”忙说:“不去!不去!那么点水,不够我喝。”
从那,不知怎么地,小“皮肚”再也不吹牛了。风车哥哥是那么高兴,托着小“皮肚”和小云朵一块玩耍。
说真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时,我那么想也到风车的长胳臂上去,在蓝天和小“皮肚”和小云朵一块玩。
儿时,风车就把去看看它的渴望吹进我的心里。现在,我终于站在了风车的故乡,像走进了童话……
风车的童话
我看到了风车。真切、生动。
在荷兰,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荷兰的风景,你一定能看到地平线上竖起的风车。风车在那宽广地平线上,和天上漂泊的云朵,地上的湖泊都带给人无数的梦幻和想象。
一望无际的绿野上,一座座古老的风车高高站立。他们像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厮守着,彼此爱惜地相视。色泽鲜艳的风车叶,像伸长了的胳臂地转动着,只是发出的语音永远是不改变的“吱呀!吱呀!”是啊,他们有倾诉不尽的劳苦。风车下,溪流却没有时间听风车的絮叨,竟是跳起来,顶着水花,闪着亮光忙着去磨坊赴约。他们得打工呦。
曲折的小道铺着蜿蜒的彩带。溪水潺潺,涓涓流淌,把晶莹安装在大地上。小桥扭来扭去,你拉着我拉着你,在绿野上架着通道。小木屋静静地藏在绿荫里。阳光慷慨地把眼前的一切都镀上了金色的亮光。
一片诗意。诗意藏着人们的劳绩和欢乐。
不是像童话,而是就在美丽的童话中。风车叶上好像还站着小“皮肚”和小云朵。
儿时傻傻的童话像一坛陈年的老酒,历久弥香……
我情不自禁地赞美:“多好的居住环境。真羡慕呀,纯净的田园风光。”
我的旅友有个德国同行,我叫他老德。老德撇着嘴说:
“嗬,别总是‘鼹鼠出门——见什么都稀罕。”老朋友老德总开玩笑,说我是出洞的鼹鼠。没办法。
“荷兰风车最早是从我们德国引进的。可惜德国在大工业发展时期,移情别恋,爱上了蒸汽机,忘了他的老情人。结果闹得莱茵河都污染了,荷兰却躲过了一劫。”
我说:“人家荷兰把风车发展到了极致。”
“他们有条件。”每当我赞美荷兰,老德一律不屑。
是啊,上帝总是公允的。上帝没给他们土地,却给了他们造大地的风。荷兰正处在从北海长驱直入的大西洋季风带里。
我说:“不管怎么样,人家风车的使用真是太巧妙了。一举多得。”
风车的功勋
荷兰风车最早只是用来磨面粉,碾谷物,后来磨香料,榨油……人们不但建起了风车的磨坊,还建起了锯木厂和造纸厂。后来我到美国,知道美国独立宣言的羊皮纸就是荷兰用风车做动力制造的。
风车是上帝给荷兰人的补偿。听说,在历史上,全荷兰的风车有一万二千多架,现在还保存了一千多架。 在埃尔斯豪特村,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最大的风车群。每一个风车都用悠然的姿态,镶在蓝天之上,和那白白的云朵组成一幅优雅、古朴的画面。
真的就在童话里。
我还走进一个很大的风车塔楼,有几层楼高。风翼长达20米。进塔房就像进古堡一样,中间是木梯,分几层。有睡觉、吃饭的地方。生活用具一应齐全。布置温馨、简朴。有的家族在风车塔房里已生活了二百多年。更吸引人是那些穿着17世纪衣服的大人孩子。他们在风车下展示着他们祖辈淳朴的民风:
农妇头上戴着红三角巾,穿着带条的大裙子,脚上穿着大木鞋。带腿的南瓜一样,做着永远飘香的奶酪。(在国外见了奶酪就想吐,回国却特别想吃奶酪。可惜没有叫我想吐的味了也不香了。)我最看不够的是一个表演的孩子。他穿着短坎肩,学着大汉的样子晃着膀子,眼却盯着一个游人手上的蛋塔,眼珠都不转了。我想他和他的祖辈一样,都得为生计辛苦。令人欣慰的是,时至今日,荷兰人祖辈的家业,又以另一种形式养育着他们的子孙。
看来想啃老,怎么啃的都有。
荷兰的“老”是苦命的。上帝把他们放在北海边,又放在沼泽地里。而聪明的荷兰“老”们却用风车排水造地,变沧海为桑田。免于他们大部的土地沉沦于水下。在荷兰的经济发展中,风车功不可没。至今风车焕发着人们没有意想到的优势。现代化的风力电站,已出现在地平线上。风车创造着最清洁的动力传奇。我真希望我的国人来看看受些启发。
荷兰人感念风车给他们的恩惠,他们每年5月的一天(第二个星期六)为“风车日”。
这一天,全国都悬挂国旗、鲜花彩灯。装饰一新的风车一块转动,举国欢庆。为了叫人永远记住风车飞转的岁月。
我记得我的一个荷兰学生就写过一篇作文《风车日——我最难忘的一天》:
“……
那天大家都要吃一种黑燕麦做的面包。面包是用从风车磨房拿回来的新鲜面粉做的。
那种面粉发的面包特别大。
我的屁股那天也发得特别大——叫我爸差点打成了面包。因为那天,大家高兴,我也高兴。
那时,我还没上学。我最愿意玩的游戏就是到处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风车叶上。心想坐在那上面一定最美啦。在那,也一定能抓一块云彩。
那天,大人们做吃做喝,忙成一个疙瘩时,我就决心到风车叶上一游。只可惜,要不是多管闲事的邻居大妈多嘴,我就真的撕下一块云彩了。大人们却说,要不是大人们发现早,要不是停了风车,把我抱下来,我就没胳臂,没腿了。不过那天,不管妈妈怎么护着我,爸爸还是给我来了一次‘发面包’。爸爸打完我的屁股还说:
‘哼,这次给你个两半的面包,下次就叫你看不出缝来!’
在欧洲流传着一句话:‘上帝创造了人类,荷兰的风车创造了陆地。’
我说:‘我爸爸创造了肉的发面包。风车日真难忘。’因为至今,我一坐下,就能记起屁股真像面包一样,发起来是什么滋味……”
想起学生写的这段趣事我还想笑。没想到,现在我也站到了风车下。那天,看着这特别漂亮、特别神气的风车,心痒痒地又生出了儿时的梦。真的,心想,要是真能上去,屁股被打得没了缝也值得了。只可惜,风车“呼呼”转动着,只叫你站在安全线外看。
遗憾,我没赶上风车日。那天看得更认真,竟然发现有的风车挂着小红旗,有的不挂。一问才知道 ,哪家有喜事,哪家就挂小红旗。而且还知道了,那么大的风车竟是一个家族的。
没出国时,去看敦煌,过了兰州,一路大漠,看见许多风车。国内的风车苗条。高高的身材,清秀的风叶点缀在一马平川的沙漠上,生动,充满了生气。只可惜太少了。真想我们国内也像荷兰,到处能看到风车,而不是油田井架。
在荷兰就想买一个风车带回去!特别想给我的家乡带回一个风车。
带回一个风车真不易
为了买风车(当然是艺术品啦。买不起大的,买小的。)我决心逛商场。嚯,一去,我们这些“老外”都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了。
荷兰人鬼点子真多。
有创意的商业点子,可以叫顾客赴汤蹈火。没想到,我也获得了一次这样的恩赐。
那是去一个展览馆。展览厅不大,出了展厅同一楼层便是商场。本来是看展览,却又可以逛商场。那商场正在展销,不需要再买门票!
玻璃窗内,色彩斑斓,各种商品好像都在搔首弄姿地以各种姿态召唤着你:“快来看呀!”
可惜还没等我去看,只听“咚”的一声,和我同来的小Q ,本来走在我前面2米,此时,只见他“噔噔噔”一个大屁股墩又礅回了2米。我和老爱什么也顾不得看了,忙看他的头。
小Q喊着:“脑袋没事,眼镜!”
我们忙把眼镜给他找来。是啊,在国外换个眼镜得多少钱呀。幸好眼镜没坏。不过,小Q起来更像小Q了。
小Q是中国留学生,小个,站直了也像团团着。(小Q,我给他的雅号)小Q团着身子一会儿摸脑袋,一会儿摸眼镜,大骂了一通。我们就下楼了。
世界上有人的记性“好”到居然下一层楼,就什么都忘了。
下楼,一扭头,呀!又是商品大厅,里面又是琳琅满目,又是各种商品好像都在召唤着你:“快来看呀!快来买呀!”更不可抗拒的是,一个醒目的大牌子,我敢说,谁看了,都走不动了。
“4荷兰盾,你拿走!”
才合1美元呀!什么呀?这么便宜?
我快步上前。接着就是和小Q一样,“咚”的一声,这回“噔噔噔”礅回2米的不是小Q,而是我。我晕乎了好一阵子,之后,我们又大骂了一通:你说,这商家光知道招揽生意,却不想想把门开好。有把门开在两边的吗?中间却是通顶立地的大玻璃窗!
后来我们才知道,从历史上,荷兰人造房子就是小门大窗子。那因为他们凭着门的大小纳税。人们为了少掏钱,宁肯从窗户吊物品进屋也不把门开大。难怪荷兰人的房子顶上,都有伸出的一个铁钩。
钱,这玩意真怪。现在不这样纳税了,但人们的思维还是惯性的。其实,想想,何止是惯性?人家会做买卖。
展室和商场连着,那大窗子里的东西真吸引人啊!商品都只有一件,而且你买完,老板立即喊:
“这个样子的,没有啦!”
多勾心啊!荷兰人真会招揽顾客!
在荷兰,你只要走进商店,就不可能不买东西。特别是工艺品商店充满了幽默感。那里全然就是一个小型艺术展览馆。光小船、木鞋就不下几十种。
展示水国荷兰特色的木屐精致多彩,多种多样:有园艺型、新婚型、滑雪马靴型……特别新婚型的木屐精雕细琢。据说,荷兰婚礼上,新郎新娘父母各给新人送一只木鞋。两只鞋上分别刻上新郎新娘的名字。婚礼过后,这双木鞋便要永远珍藏在他们的卧房。象征走到一起,一生相伴。了解这一风俗,许多情侣都买。遗憾,老板不会刻汉字,否则我和老爱也一定买一双。
我的一个老外朋友却非要买一双,而且还一定要小鞋:
“我买小的,我愿意穿小鞋。我愿意穿小鞋。”
等我告诉了他们汉语“穿小鞋”的比喻义,老外说:“买了也不穿。”大家一通“哈哈”。
不同民族,语言的比喻义不同。这种文化误解也就成了我们的笑料。那天我们真是笑料不断。
在荷兰,我还认识了一个大概是尼泊尔人(我最爱交朋友了)。他说他可不买木鞋。他们古时候,有一种叫“木站鞋”。人穿上就站在那不动了。我忙抢着说,那我买一双。穿上也好歇歇脚。出来,整天跑,累死了。谁知,我的老外朋友们一块大笑起来。
原来那种鞋是一种刑罚。在一块板挖两个洞,叫受罚的人站到木板里,两只脚不能动。那是用来惩罚传老婆舌头和偷情的人。
你说,我还要买一双?真倒霉。听说我们西藏,过去也有。
我们又一通“哈哈”。跨文化交际,因文化背景不同总有歧义,歧解。
木鞋不买了,买小船吧。
小船造型也颇富想象力,有的是摇篮,掰开的花生壳、仰面朝天的小熊肚皮。无论什么都可见人家思路活跃。有个烟碟干脆是个小孩蹶起了屁股,妙趣横生。连他们的国鸟琵鹭(嘴像琵琶的白鸟)也都人格化了:抻脖瞪眼表示惊讶的、跳伦巴舞的、下跪求婚的、穿着大木鞋的……最严肃的人看了也不能不笑。
我终于看到我最想买的风车。
小风车更是构思独到,好像是用树叶、草棍儿编扎起来。古朴、逼真。这些小风车、小船、木鞋、国鸟的成本寥寥可数,成品价格却叫你瞠目。然而凡是来这里的人都买。说实在的,需要买的真多。人家国家特点鲜明:只是国花:郁金香不好带; 国鸟:琵鹭不能带;钻石(国石)带不起,也怕丢。 只有木鞋、小帆船、小风车好带,都昭示着这水上之国的特色。
我咬了咬牙买了一个风车。想带回国,摆在客厅,昭示:到荷兰一游!
走走,觉得不对劲,细看,呀!风车是巧克力!同行旅友皆大欢喜。我们大家高高兴兴地把风车分吃了。一个小风车40荷兰盾,等于10美金(那时汇率1比8多),相当80多元人民币啊!
艺术无价呀!
真没想到,就这样了却了我儿时的风车梦。 长见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