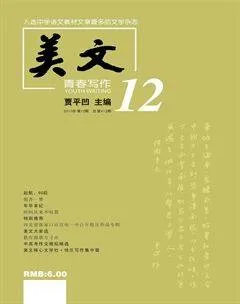道道道
2013-12-29
尼采说哲学已死,我想这是真的。
前些日子去北大哲学夏令营,听了三天的凡人之争,看了三天别人的眼睛。
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看别人的眼睛,无论是陌生人的还是熟人的。通常,我爱引一个有趣的话题,然后默默地听他或她讲。同时,我开始享受地看他或他的眼睛。人的眼睛真的好奇怪,它与人的年龄不总是同步的。孩子可以有浑浊的眼睛,少年的眼睛最冷漠,而老人的眼睛也可以像婴儿一样充满好奇。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圣经·雅歌》里良人漂亮的眼睛被比做鸽子眼。我仔细看过好多人的眼睛,像鸽子眼的双眸很少见,除了婴孩外,我只发现两个人有这么好看的眼睛。只是我不敢正视那双活灵活现的鸽子眼,我怕它的主人会生气。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悖论,通常长着寻常眼睛的人在侃侃而谈,尤其是面对一个少说多听的好听众(如我)时,总不会注意到我在认真瞧他或她的眼睛。相反,若我偷偷瞥那鸽子眼,便可以感到我的目光顺着这双眼睛悄悄地滑着跌进这眼睛主人的心里。我不忍心我的目光像磨钝后长满毛刺的竹器把他或她的心揪地一挑,所以我总不愿瞧他或她的眼睛。虽然那眼睛真的很美。
还好,哲学夏令营没有给我机会让我再面对这种想看却不能看的矛盾。的确,那些为往圣继绝学的哲学夏令营营员们都是国之栋梁。他们不仅熟悉哲学史,熟悉哲学原典,而且博闻强识。我见到带圆形镜片满口之乎者也四书五经的北大附中学生,我见到那么远又那么近的黄冈中学学生。当然,我还是习惯性地沉默,安静地听教授在希腊文德文古文里跳跃,安静地看同龄人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心里默默笑着,想起一位教授惊异地问:不知是因为哲学,还是因为北大,这届夏令营竟有这么多人。其实我知道那个选择问句错了,真正引来这么多人的是优秀学员自主招生免初试的蜜糖。为了成为优秀学员,自然要“秀”。于是,我看到好问的优“秀”同学们拖住了教授,被大学生们冷落许久的教授被这股来自优“秀”中学生的热情感染竟错过了午饭时间。于是,我看到善思的优“秀”同学们在主题不限的班会课上竟主题异常鲜明地讨论了一晚上“自杀”这种终极话题。
若是以前的我,行文至此,定会如决堤洪水,透着尖酸刻薄一路写下去。但正如沈从文曾写道“难道不知道讽刺同鲁迅一道死去了吗?”我们通常喜爱犀利的文章,不羁的笔调,而且写这样的文章(或者叫做杂文)最为简单,只需将一腔愤怒一股酸劲用笔记下,这样便是直插敌人心脏的匕首了。可是,细细想想,却终是可叹了。姑且将中国人数定为十三亿,如果我总是站在十三亿减一的立场上说话,自然潇洒痛快。可是事实上,我不过是十三亿分之一罢了。我在那夏令营中,便是其中的一份,优与劣我皆占着。
我说夏令营里没有很美的鸽子眼,可是我对镜自视,同样没有看到十分漂亮的眼睛。相反的,这眼睛布满血丝与不屑,还有透着嫉妒的滑稽可笑。十几年未曾掸过灰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总是雾蒙蒙、脏兮兮的。我突然想起食指的诗句“她有洗去历史灰尘的睫毛”,心肌陡然收缩,差些涌出些无用的泪来。这未涌出的泪让我记起夏令营里一位高个子的大男孩,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他的眼睛。我现在可以再看到当教授与我们讨论时,所有人包括我都在“秀”自己的“优”,我们极力地口吐莲花,句句用典。当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常从我们嘴里滑落,尼采的强力意志,康德的观念论,叔本华关于欲望经验的理论悉数登场。可以说作为哲学的哲学史正在我们头脑中滚动。那个大个子男孩眼圈发红,抱着胳膊,蜷伏在桌上一言未发。我记得他自我介绍时说他对哲学家并不了解,只是喜欢自己想想世界。我记得他后来发言说他很失望。很奇怪,我觉得我的心能听懂他的话,可是在优秀学生极力“秀”优时,我攥着奥勒留和《炼金术师》卖弄学问,扮演着令他讨厌的角色。我总在想我何以为了一个“优秀学员”的称号做令我的心落泪的事。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每一个来此的同学都背着学校与家庭的包袱,耳畔总能想起那句“好好表现”的叮嘱。其实,我们何时不都背着这样的包袱?我们总是整体分之一,我们做不到与所生活的环境脱节。
在夏令营同学发言里,我又听到了那句“这是一个浮躁的社会”的话。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浮躁的话了。正所谓“欲洁何曾洁”,我们其实都不干净,做洁癖想清高还不如抛开这句话,在风雨中奔跑,在泥潭里打滚,至少是“维摩诘”。我想只要为心留一寸安宁的干净地方就实属不易了。
我记得《色情男女》里的一句话:“我以前做人很可笑。”其实我以前做人也很可笑,可笑到让现在的我哑然失笑。我以前总以为公道自在我心,刻薄自傲,现在才明白:道可道非常道,天道地道人道剑道,一道二道三道四道,东道南道西道北道,左道右道前路后路,都是胡说八道。
好有意思,我说我去哲学夏令营这事,竟扯出这么多无关的话,可是这些都关乎哲学。然而可叹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说哲学已死,却不能像尼采那样在判语下定后开创自己的哲学,这就是凤凰涅槃与飞蛾扑火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