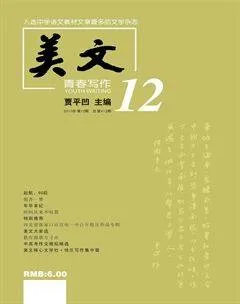银杏一梦
2013-12-29
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我细想,发觉植十年的树木可以活过十年、百年甚至千年,相反百年所树的人却只能活几十年,至多不过百年罢了。于是我想做一棵树。
我去乞求众神,让我成为一棵树,一棵一生用世纪为单位记下春秋年轮的树。众神发笑不语,良久,一位神答应了,那是周公。周公说我的前世是他酒葫芦里剩下的一滴女儿红,只因他醉去太久,梦得太深,那滴女儿红终在仙界吸尽万物芳华,化了一个有灵的魂魄去人间戏耍轮回,到我这一世已不知过去几千年。但酒水化为的魂灵终还带着醉意与痴念,好不容易修得人形,如今却还想做一棵树。
周公并未让我真正成为树,只是让我睡去,元神进入梦中,神再让我以树为身活在梦里。神说这样对我最好,我既可在梦里真真切切地做树,倘若后悔仍可挣脱梦,回到现实,重新做人。况且人世间只以为我沉沉睡去,不必太过担心。
周公说,如此这般的法子他已多次用过。只因神太嗜酒,总有几滴酒剩下,而这些酒化为的人总会在某一世渴望成为一棵树,他只有满足像我一般人的心,在梦中将人化成树。因此世上总会出现不生不死的植物人,那便是周公某次马虎剩下的酒。末了,周公叫我不要后悔。
我心中默默发笑,觉得神多虑了。我怎会后悔,树比及人有更少的碌碌,更多的自由,我怎会有悔且再去做人?但在神前我不语,只默许梦中为树。
神顿顿,让我选择愿成为何种树。我这才发觉树仍有不同,一番思量后我说我要成一棵极长寿的树,这样方不枉为树。
神想了想说,那就成为胡杨吧。胡杨生而不死三千年,死而不倒三千年,倒而不朽又三千年,共能活过九千岁。我却不愿,可怜胡杨九千载,夜夜相伴风与沙。我不想九千年只与一片一成不变的荒漠相伴,那样太无趣,枉成为树。
我想到了银杏,听说银杏极长寿,祖辈种下,孙辈乘凉,因而又名公孙树。且银杏还会开花结果,单是银杏叶便有极不同古质的相貌。
然后我就成了一株银杏树。
我的躯干是褐色的,长着纵裂,笔直向上成了树干。我的叶子是扇状的,如一只只手伸在空中,但这叶子其实便是我的手。我的眼睛长在每一片叶子上,它生在我掌心处,所以我看到的景物与人大不相同,应该与苍蝇相仿,都是复眼,像一面镜碎成七零八落再拼凑回去,既而镜中之物缩小分散重置在每一块镜中。由此我看到的一切没有视觉死角,360度全景入目。我欢欣成为树后看到的世界。
不久我就习惯成为一株银杏树。一只极其聒噪多舌的蝉用一个盛夏极力与我讲话,但我不懂蝉语,直至这只蝉死去。来年,这蝉的后代竟只说一个词并又重复了一夏。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脚下的狗尾草何义。
狗尾草说自然中的语言向来只有植物中相通,动物中相通。植物听不懂动物的话是自然,若想听懂,需要媒介。而媒介之中有名的是虫草,因为它介乎动物、植物之间,我可以寻得虫草以求翻译。
我想起行寻虫草,迈步时发觉两脚已埋入黄土不得动弹,恍然怔住:树的视野是全知的,是因为树不能行走。
百年后,我终于等到一只虫草过路。这百年间,每到盛夏便有蝉对我说同样的话。这些话像符咒一样魅惑,令我好奇。
虫草听我将话复述完,告诉我蝉所说话的意思。我终于明白蝉与银杏已是老相识了,而我作为银杏是孤单的,我独属一纲一目一科一属一种。我原来很早就出现在世上,与恐龙一起在全球称王称霸过,后来恐龙灭绝了,与我同时代的一切都在大灭绝大冰期中成为地质层中的化石,只有我银杏奇迹般地活至今日。若我还是一个人,我会说我是孑遗生物。
至于蝉的后代不断重复的词则是“知了”,他们想问我是否知道自己是老古董。
虫草做完翻译后便走了。我心里仍然回味着蝉说的话。我终于明白我为何如此不同,单是叶子,也与一切树木相异。原来我本不属于这个种子植物的时代。
我极伤心符咒解开后竟是悲剧,呜呜抽啜,叶子也生得差强人意。叶子小时仍是扇形,待到长大些,扇子便被撕开一小牙豁口,每一片都是如此,我只好说这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吧。
一只蜘蛛对我说不要伤心,我吓了一跳,她竟听得懂植物话语。蜘蛛解释她已成精,懂得植物间的言语。她耐心把豁口用丝缝补,还告诉我每一株银杏得知自己是上个时代的遗物都会伤心,她饮银杏露成精理应报恩,所以告诉每一株银杏,其实风也是时代的遗物,银杏苦闷时可与风叙旧谈天。
我便注意风,发现风无影无踪无形。风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要到何处去。我捕捉不到风,只在每一次风起时招手示意,发出“簌簌”之声示意风停下。
风只管继续吹,不愿停留。
银杏毕竟是树,是静止的,不可动的。我总想追风,却总是办不到。我求停在我枝头的麻雀帮我捎口信,追上风,求风稍作停留。
我想问风远方的景色,我晓得风在天地间游荡,一定有不少新奇见闻,不似我这般在一处树立已有数年,看不到新鲜与不同。
然而麻雀回来告诉我:风不能停留,静滞的风便不再是风。我有些凄然,蜘蛛告诉我,可以撒下叶子随风远去,我的双眼便可以随着手掌在空中乘风旅行了。
我喜欢蜘蛛的好主意。在秋天我的眼睛雀跃着跌进风里,乘风万里行遍。我的天地顿时开阔。冬日里仍有未枯的眼睛带来北国雪的晶莹。我将看到的说出来与蜘蛛分享。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只蜘蛛瘦胳膊瘦腿,躲在树洞里缩成一团,形将槁木。可我每说一只眼看到的景色,她便眨眨眼以示欢愉。
我对蜘蛛说我感谢风,感谢不羁的风让我游于天地。我又说起风的神秘,无影无际亦无形,我说这风定是绝代风华。蜘蛛听着瞪大了眼,继而吃吃地笑了。
来年春日,我又要生出新的叶子,且极奋力地生更多来,因为我想看见更大的世界。那只蜘蛛仍为我生出的叶子缝补豁口,她每日只饮晨霜即可,全没有结网捕食活物的习惯。
夏日的叶子全都绿了、盛了,像一团绿色的火般跳跃舞动。风到来时,我便卖力地晃动手臂招手示意,但风只是不管不顾地流向远处。更多时风不再吹来,或许风不喜盛夏吧。我的世界因而在夏,犹是盛夏沉闷许久,因为我又被困在这一方小天地间了。我的眼睛不能乘风而行,我就艾艾然对着蜘蛛抱怨。
我抱怨风不能常来,又盼着风早日来,带着我的眼睛在天地间游戏,蜘蛛缝补着我叶子上的豁口,默默无言。
我望着蜘蛛,突然意识到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便去问。蜘蛛讶然,她不曾有过名字,她只当自己是蜘蛛,无名无姓的蜘蛛。我说叫她“风”好了,蜘蛛她很欢喜有了名字,但只是淡淡笑笑,未欢快地眨眼睛。
这样,我这株银杏便不再忧心风不常来了,虽然夏日的“风”并不是真正的风,也聊以慰藉。
如此这般又过了百年。
风再起时,我发觉随风飘动的还有一些尘埃颗粒,这些颗粒尘埃常常欢笑着叫着。我极艳羡,我问他们何以如此与风常伴。
尘埃中的一粒说这需时间的造化。他本是九千年前的胡杨,三千年生而不死,三千年死而不倒,三千年倒而不朽,如今终是脱离了固态的束缚,悠意在风中翻筋斗。
呵,胡杨,九千年的胡杨竟终会以灰烬的形式翱翔天地之间。我也想早日死掉枯倒腐朽为灰烬。我对“风”说出我想到的,“风”紧张地盯着我,最终叹气说她再也饮不到我叶子上的晨露了。
我嬉笑她可以到别的树或花上品咂甘露,但“风”黯然不语。天黑时,“风”悄声对我说:“听,秋风要来了,你又可以眼观六路了。”
如此这般,我盼着成为灰烬又是百年。
百年里,我总想某日便能如游气一般随着风追着风。但我长寿地活着似乎没有尽头。
我突然想起我作为银杏只是一场梦,只是从三百年前开始的一场长梦。那时我是人,渴望长久地活着。现在我已知长活百无聊赖,我只想与风相伴,而树是静物,不可常与风相伴。于是我心内有悔了,我想挣脱梦了。人是活物,追风极易。
我对“风”说起了这般,“风 ”一副凄凄然的模样,她知道她依托的银杏会随梦结束而成为幻影,可是她终是未言什么。
周公听我要结束梦境,笑了,如当初众神了知因果际会的笑一般。转而又皱眉,神说迟了,三百年太久了。
我才知明白梦境与现实本是相对的,我为树的梦也可以是现实,我为人的现实亦是一场梦。三百年光阴,我为人的肉体已朽掉,我的元神回到那个世界是没有依附的。我为树成了本来的现实。
倘我执意成人,除非将树的实体用烈火燃为灰烬,为人的世界方会再有一具肉体供我的灵魂依附。神说两个世界的物质皆是守恒的。
我渴欲追风,决然决定将银杏用烈火燃去捎带人世间,于人间与风长伴。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风”,我对“风”说我将在人间的春天放风筝,随风行走,不再因无风而抱怨了,因为我有了双脚。
只不过我得用烈火焚身,这火听说是有名的三昧真火,一昧便可销去一百载的梦中事,三昧真火燃尽,三百年已成现实的银杏事就会成了一梦,然后我会醒来,作为人隐约记得或忘记一个作为银杏的很长的梦。
周公叫我等待二十五年,电母会在一次闪电中将我劈中,电中会擦出天庭的三昧真火,火将燃九日,我作为银杏正式归为梦。
我将这一切告诉了“风”,我欢喜道我可以常感风来拂面了。
“风”默默听着,喃喃着:“记得或忘记一个作为银杏的很长的梦。”
我的心境好了很多,银杏叶上的豁口也小了,“风”的缝补工作轻了许多。每天她仍是早起,且起来得更早,然后饮晨露更久些。
三百年来,我多半念及风。想到今后与风常伴,而对于这“风”倒真见不到了,我第一次认真观察“风”的一天,好奇地问她晨露何种滋味。
“风”些许惊讶,说晨露是无味的。我的问本是无端的,因而对回答无意。
二十四年很快过去,这对于一棵银杏来说只是树生一刹,一年也是最后期限。
“风”问我人是否可以记清梦,我毋知。
“风”又问我是否想早日梦醒,我恍然可以看到春日融融,我拖摇着五色风筝在风中奔跑,我急快点头。
“风”末了问我知晓何为三昧真火,我毋知。
九日后,“风”向我告辞,她说她是精,已有灵性,可以帮我回到人间。“风”走得如风般悄然。
又九日,周公唤我醒来,我睁眼,我又是一人,梦结束了。
现在我是活物,只要奔跑起来,耳边便可生出风来,无须静滞等待。
只是我总记得一个长长的关于我成了银杏的梦,荒唐怪诞却极真切。
某日的短梦里,一只蜘蛛对我说她是“风”,“风”说她讲了一句谎话,她饮的甘露不是无味的,相反,叶子上的液体都是我的眼睛流出的眼泪,三百年相同的苦与涩,除了最后二十四年竟带有醇甜味。
这个梦同样记得真切,直到我作为人离世前。人活不过百岁,六十九年后我就要辞世,方发觉我心之所向的风从未真正瞧我一眼。风总是不知从何处而来,不知到何处而去,我永远只是过客。因为风永恒不羁,不能也不肯停留。
此外是亢龙有悔,我忘了成了人,只有二目,再未有眼睛随风畅游,也未有与“风”说我看到的奇峰怪石的机会了。
我的魂灵来到周公身边。周公又提及了“风”。周公说,“风”知道三昧真火实际上会销去记忆,且对作为银杏的我有裂肤之痛,故而用三百年造化换回我记忆长存,还有便是那个长记着的短梦,算是“风”的告别吧。
难怪我再见到的银杏叶上都长着长长的豁口,再没有蛛丝缝补。
最终,我化为了一壶酒,周公确切地说是三百年的女儿红,醇香与甘露一般。
只是不知这次周公是否在饮完我之前醉去,剩下几滴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