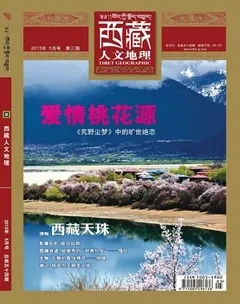德木寺:尘与梦
2013-12-29杜冬冯帅




古刹化作黄尘,“滚羌”舞步飞旋,往事遗忘,足迹模糊。如今的德木寺,在寂寞古道旁,依然踏着旧日的步伐,为鲁朗保留着那些不为人知的古老传奇和梦想:最后一世德木活佛成为西藏第一代摄影师,和他的儿子旺久多吉用图像记着西藏的传奇。
而历史上,满怀抱负的湖南人陈渠珍,他所率领的清军曾在德木寺驻扎,进攻波密遭遇惨败,后又从这里开始万里流亡之路。
尘之篇
早课
清晨五时,德木寺70岁的主任拉巴敲响了铁钟,清脆的钟声在小小的庭院里回响。几个僧人戴着鸡冠帽,披着猩红色大裘,顶着黑暗走上大殿,没有对话。
我跟随着一个面庞紫红、身材极高的年轻僧人,他擎着一面陈旧巨大的法鼓,沿着木质的台阶上行,狭窄的楼板在他身体的重压下吱嘎作响。
此刻,湿重的空气从黑暗的雅鲁藏布江面上袭来,裹挟着这个位于林芝县米瑞乡山上的小寺。
德木寺原址建造于现鲁朗东巴才村冷泉河畔,当年帕巴拉活佛翻越德木拉古道,在此兴建噶当派寺庙,以自己的叔叔镇守此寺,这便是德木(又译作第穆)活佛世系之始。当时恐怕没有人想到,一个雄踞工布要道上的寺庙,居然会三次执掌全藏摄政之局。
二楼右拐,经过一道狭长的走廊,便是窄小的护法神殿,德木家族的保护神,工尊德木女神的塑像就位于此处,昏暗的灯光里,护法神被厚重的帷幕遮住面庞,隐在小小的神龛内。
这位工尊德木女神法力极强,据说曾是吐蕃早期恰赤赞普的妻子,恰赤的哥哥纳赤与大臣比武失败,和弟弟一同流亡工布地方,纳赤成为阿沛家族的起源而恰赤的妻子工尊德木则成为德木家的世代护法,从此也可见阿沛家族与德木家族的渊源之深。
拉巴和我们说,当莲花生大师前来收服她之时,工尊德木女神露出鸡爪双脚。莲花生大师不禁失笑:“原来是一只鸡。”女神从此被收服,成为十二仙女之一,并以三身出现:慈悲相、忿怒相和鸡爪身像。德木也因女神而得名。
在德木世系沉浮的岁月里,无论是遭遇地震的劫难还是政治风暴,唯一随之迁徙流转的只有不言不语的工尊德木女神。我们后来拍摄女神像时,僧人要求我们不要刊登,担心读者将工尊德木女神像随意丢弃,引发女神的狂怒。
7位僧人盘腿而坐,厚重的大裘将小小的神殿挤得满满。5点47分,随着八字胡的领诵师摇动手中的铜铃,高低不一的诵经声次第响起。
由于波密王的骚扰,原本位于鲁朗的老德木寺僧众于16世纪被迫翻越德木拉山口,移居至如今林芝县米瑞乡一个状如法鼓、俯瞰雅鲁藏布江的山头上,是为新德木寺。寺庙最盛之时有僧人千人以上,而1950年震撼全藏的墨脱大地震,又将新德木寺毁于一旦。如今所见的这座德木寺,仅有大殿一座,乃是地震后由十世,也即最后一代德木活佛主持重建,规模大不如前。即便这座大殿,也是地震后重建而成。
诵经声依旧,伴以清脆的铃声和浓重的鼓声,时间如同恒河细沙般的流逝。
诵经声包裹着德木寺,如同孤舟漂移在粘稠的时间之河上。这条河里万物静止,人是其中唯一的游鱼。当年10岁出家的宗萨林村小儿拉巴,如今已经是70的耄耋老僧,他眼睑低垂,双手合拢。
6点23分,住在寺庙里服务的几位阿妈蹑足而行,提来了两大壶热酥油茶。小僧人扎西尼玛提着裙子起来,为众人倒茶。一时念经声中断,充斥着连续而响亮的啜茶声。
7时13分,在念经和断续的喝茶声中,两壶热茶都已喝完,早课即将结束,狭窗外一片铅灰色,寒冷更甚。
由于僧人较少,所以德木寺的早餐不像大寺一样严整,反而有家庭般的温馨,黝黑滑腻的旧石锅里煮着粉汤。僧人们围绕着矮桌一同吃早饭。
住在寺里的工布大妈们操着沉重的木槌,砸开新鲜的山核桃,露出洁白如奶的核桃肉。德木寺已经醒来,住在寺庙书屋的汉族包工头老王戴了太阳帽走下楼来,他负责为寺庙修建一条不长的水泥路,从小山脚下的曲尼贡嘎村通向寺庙。
山脚下已经响起轻淡的哨声,早起的工布男人在试射响箭。从德木寺可以俯瞰宽阔的雅江,江面吹拂着尘暴,一时黄尘滚滚,在水浪之上还浮动着凶猛的尘浪。路上都络绎走着远近而来参加法会的村民,他们在齐膝深的灌木丛中走着,山风掀动他们宽大的工布服饰下襟。
这些村民近来自脚下的曲尼贡嘎,远至鲁朗各村甚至东久。德木寺对面就是苯教的圣山:苯日神山。从秋季开始,这条转山之路上就日以继夜地走着众多的苯教徒,他们从昌都和那曲的遥远山乡赶来,裹着工布少见的厚重藏袍,或走或拜。
对面的山顶,就是一个重要的苯教寺庙。僧人拉巴说:“我们和他们(苯教僧人)没什么往来。”
隐居
尼玛次仁拿着古老陈旧的白海螺,守候在寺门外的草地上,这里已经架设了两具沉重的大法号。主任拉巴抚摸着光头,频繁进出寺庙大门,显得忧心忡忡。这个没有活佛住持的小寺,已经倾其所有,全体出动,准备迎接附近一所寺庙年迈活佛的光临。
他们不知道活佛的车从哪个方向来,所以四下张望。当年他们自己的德木活佛从拉萨远道而来时,这位西藏的摄政和有大清皇室亲封呼图克图称号的权贵,其迎接仪式大概要胜过今日许多倍。
每年的“贡羌”节日期间,德木活佛一般都会亲自来祖寺参与。德木活佛世系全盛之时,所主管的寺庙除了祖寺德木寺和拉萨的居所丹吉林寺之外,还有大名鼎鼎的桑耶寺等,拥有众多庄园,从工布直至康地,富倾一方。当拉萨发生饥荒,物价沸腾之时,德木活佛曾让其主管的庄园向拉萨大举运送糌粑、酥油等物资,其驮队规模之大,据说前面已经到了冲赛康(今大昭寺附近),驮队之尾还在过拉萨河。
不仅财力雄厚,德木活佛系还可依靠自己求学的哲蚌寺最大札仓(僧人团体,多以地域加以区分)洛色林札仓四五千僧人的强大势力。清代光绪等列位皇帝都曾直接下圣旨任命德木活佛出任摄政,也足以说明德木活佛系和“文殊室利大皇帝”的密切关系。
1910年,在九世德木蒙冤而死后十年,刚即位的宣统皇帝御笔直接指定1901年出生在阿沛家族的灵童为十世德木活佛。
1921年,活佛20岁时进入下密院,后成为执法僧(格贵),如果在此路上一直研读,有望登上甘丹寺方丈,也即甘丹赤巴的宝座,执掌宗喀巴大师的教权。但是他决定奉还比丘戒,成家。
西藏传说德木活佛为吐蕃高僧、大译师贝若遮那的转世,这位高僧曾演说过:婚姻如同鞍犍,孩子如同马笼头,不外乎是人生的枷锁,是求法的障碍。如今末代德木活佛却决定奉还比丘戒,迎娶了拉萨著名尼姑寺——仓姑寺(该寺如今以甜茶著名)的一位尼姑,虽然依据藏传佛教仪轨,德木活佛的宗教和政治地位名义上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然而这一大胆的想法,依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经过德木活佛在哲蚌寺的同学,当时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活动,德木的庞大产业有一小部分在1934年归还德木活佛(德木世家的所有产业都在九世德木被害后由噶厦政府没收)。这位有家室的活佛早在闭关之时,曾师从一位潦倒的尼泊尔摄影师学会了摄影和发电等技术,成为西藏最早的本土摄影师之一。
德木活佛拉萨闲人生活过的有滋有味:他念经、修行、画唐卡、琢磨金银的手艺;他会驾驶摩托和汽车,会自己设计房屋,制作风筝,当然更多的精力用于拍摄和冲洗照片。他会自己放映电影,还曾录下拉萨一位著名女巫降神时的吟唱,并放给女巫自己听。
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热振活佛曾有意将摄政一职让给德木活佛,被德木活佛坚决拒绝,或许是自己的前世,九世德木活佛的惨痛遭遇,以及随之引发的丹吉林寺对抗藏军的苦战,让德木活佛下定决心远离政治。事实也证明他的正确,上世纪前叶的西藏政坛波诡云谲,最后连热振活佛也不得善终。
然而这并不表明末代德木活佛从此对自己的祖寺不闻不问,1950年,也就是他的九儿子旺吉多久出生后一年,林芝发生大地震,德木寺毁于一旦。道路险阻,没有人知道林芝大震的消息,此时赋闲在家,以拍照为乐,不闻窗外事的德木活佛还是从印度报纸上得知了大地震的消息:雅鲁藏布江水冲来许多藏式家具和民居的碎片,让下游的印度当局揣测上游的林芝发生了巨大的灾难。
这之后许久,有一些工布打扮,衣衫褴褛的人在德木拉让(德木家官邸)门前逡巡,当他们见到德木活佛之后,号啕大哭,诉说了寺庙被毁的惨状:全寺被毁,只余一尊强巴佛像。赋闲已久的德木活佛对此事极为关注,他释放出惊人的能量:以崇高的地位上下疏通,并且得到了他本人出身的家族,同样为工布豪族的阿沛家族的大力支持。
不久之后,他亲自带队,带着一支颇为庞大的工匠大师队伍、他亲手设计的图纸和足够的资金,踏上了前往米瑞,重修德木寺之路。他还想带着自己心爱的照相机,拍摄大地震的惨状,但未被西藏政府允许。
神舞
“活佛来了。”人们指指点点,尼玛次仁他们手捧哈达迎上前去。一位高大的年迈活佛下车,为僧人摸顶,尼玛次仁为他的前导,引领他和几位扈从走入大殿。
拉巴让罗桑达吉去拿砖茶,我跟着这个39岁的僧人弯着腰走进饭堂边的小库房:这里的地板已经塌陷,里面搁着几长条砖茶和几口袋面粉。罗桑达吉有些惶惑地笑笑,摸摸寸把长的黑发,这个小寺的库房就这么大。罗桑达吉有个习惯,有时候自称普布次仁,那是他24岁出家之前的名字,他就来自米瑞乡,不过父亲却是康巴人。
“当时我普布次仁24岁,如果结婚的话,现在孩子都和我一样高了。还是当喇嘛好,我心里想。”昨天晚上他如此说。德木小寺的夜晚有些清冷得无聊,唯一的小卖部也关门了,钥匙在领经师腰上挂着。几只瘦长的狗在芍药丛中钻来钻去,罗桑达吉一把冲过去,挟住一只小白狗狂奔,这时他又成了普布次仁。
小小的院场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躲在芍药枝下,躲在桃树和柏树下,树荫中散发出越来越浓的酒气。和卫藏地区烈日炎炎的广阔中庭不同,德木寺庭院里草木摇动,在二楼的墙壁上还有寺庙的绘画,虽然谈不上精美,但一眼就能看出是德木寺的工布建筑。更重要的是,画上几个带着鸡冠帽的喇嘛是走在密林中的。
大殿内热气腾腾,僧人们互相帮助为对方穿上厚重的跳神礼服,在头顶缠上发带,好佩戴狰狞的面具。一个文弱如女人的僧人带上面具,数着“吉、尼、松”的步点,在中庭的阳光投影下独自演练舞步。我的快门声一响,他猛地回头,犄角下血红欲裂的大眼怒视着我。那是面具的眼睛,他自己的眼睛则在獠牙之下,几乎看不出来。
回头一看,另几位高人一头的神灵袒露着肩膀,正在和站在门口的乡亲用工布话聊天。不知说了什么,他们微微点头,摇晃着巨大的犄角。工布方言和拉萨官话大不相同,例如“是不是?”在拉萨话中是“日瓦?”在工布则变成“侬给?”;而饼子“帕勒”则变成了“佐罗”。
头戴沉重的面具,眼睛的视界又受到阻挡,这些说着工布话的可怖神灵很久才能在昏暗的中庭里列好队,似乎即刻要出征。八字胡领诵师在最前面,他穿着肥大得夸张的靴子,一步跨出大门,左手抓了一把青稞粒,右手拿着颅碗,外白里红,有人在颅碗里倒了满满一碗青稞酒。在绘画中,颅碗中盛满脑浆和血液,表示智慧。
尼玛次仁等两人吹响了一种类似小铜号的乐器,略有颤音。片刻,大殿正对面的乐器上也以大法号回应。小铜号再次吹响时,乐席上敲响了大鼓,“滚羌”正式开始。
领诵师突然挺直了腰杆,他左手一松,青稞落了满地,他高高抬起左脚,迎着鼓点的节奏,极其缓慢地舞动着下了德木寺的窄台阶,进入院场。洒下青稞,等待鼓点,这个神灵的长队一个个从黑暗的大殿中走出,舞入中庭。
六尘
我退到德木寺的帷幕之外,看到那位年迈的活佛已经登上二楼的小看台,他拿着一台小小的数码相机,闪光灯一闪一闪。
德木寺的“滚羌”仪式复杂,极为著名。历代德木活佛从早已消失的寺庙大殿栏杆上向下眺望神舞,那些狰狞的手势和面孔,是否会让他想起拉萨的风云变幻:布达拉宫主人的频繁更替,难测的宫廷阴谋,一夜到来的巨大声势可能瞬间成为泡影。同样仿佛是三尺戏台,刚才还是欢喜的笑容,一瞬间又换作凶恶的嘴脸。
初世到三世德木活佛的潜心佛法,四世和达赖喇嘛结缘,远赴北京,六世、七世执掌摄政,八世的云游四海,九世的冤死。跳神的脚步重重落下,激起尘土 风向变换,通向拉萨的小径一路尘土。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翻滚,人人如行在雾中。寺庙轰然倒塌为一片尘土,又重新建立;前世拥有的无论是荣华或惨痛的流放,又会转世而来。
鲁朗的百姓则眺望着栏杆上的红袍身影,是他将一个广大而不可思议的世界带到了这个小山村。人们说他是吐蕃高僧贝若遮那的转世。当这位高僧从印度学法归来之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曾经披散自己的头发,铺展在地上,让贝若遮那走过,以示尊崇。此外,他还是曾经前往唐朝求亲的吐蕃大相禄东赞的转世。因此他在全藏的重要地位,和汉地文殊大皇帝的密切关系,在生生世世的前辈就已打下基础。
人们传说德木活佛法力广大,能降伏可怕的护法神。旺久多吉回忆,丹吉林寺的楼上曾供养着萨迦巴姆女神,每日要燃烧山羊油向女神献祭,有人忘记献祭时,半夜就听到女神沉重的冲撞声和脚步声,轰然响动。
脚步声就在庭院里,舞者带着骷髅面具,较为紧身的衣服绘着肋骨条,脚掌和手掌都有裁剪出的尖爪。它们嬉笑着拉动两根长绳,长绳中心可见有一个红色的小人,可能只有20厘米长短,和这些巨大的、跳舞的骷髅比起来小得可怜。
不知道这些骷髅是否象征着死神,而那小人又象征什么,难道象征死神将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吗?其实即便显赫如德木活佛,依然躲不过多变的命运。1895年,由于向刚刚亲政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献上了一双藏靴,退下摄政职位的九世德木活佛陷入了一场噩梦。
达赖喇嘛的身边人索杰喇嘛声称,他一将鼻子靠近这双靴子,鼻子就会流血不止,他建议彻底检查这双靴子。于是西藏最著名的神巫乃琼神汉做法并进行了检查,结果令人不寒而栗,靴中有密咒师诅咒达赖喇嘛的咒语。九世德木活佛被拘禁在布达拉宫,后来据说被活活溺死在一口巨大的铜水缸内。
把这个小人在泥土里扑打之后,骷髅们跳踉着回到寺庙深处,最后一位进去的显然已经十分疲劳,有些力不从心。他们背后夹着的微型麦克风没有关掉,全场愕然听到他们回到大殿之后粗重的喘息声和嬉笑声。
我又跟着进去,刚脱下木头面具,还穿着骷髅衣的八字胡领经师颇为费力地用血红的尖爪捏住几张写满的信纸,将麦克风扶到嘴边,大声念出捐钱者的名子、所在的村子等。这里有山下曲尼贡嘎村的,也有鲁朗甚至东久的,大多以一百和二百元。
大殿里依旧昏暗,脚下的木地板上已经洒满了青稞粒。大殿的正面能看到十世德木活佛的塑像和法座,法座上交叠着德木活佛的法衣。塑像颇为写实,面容祥和,我后来看到旺久多吉为他的父亲拍摄的肖像,发觉有八分相似。
如今德木活佛世系已经中断,旺久多吉曾经在1986年开始主持重修德木寺,但是他并非是活佛,也不是丹吉林或者德木寺的主人。这个法座将不会有人来坐。
十世德木活佛过世于1973年,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他还在担任大昭寺维修工作。工匠们特意最先修复了禄东赞的塑像,希望他早日康复,因为传说德木活佛是禄东赞的转世。
此时,十世德木活佛已经灯尽油枯,他推荐了甘丹寺的大喇嘛接任。
在约60年前,由于愤恨九世德木的冤死,丹吉林寺协助清军,从而卷入清军进入拉萨的事件,导致德木家所有产业被没收。那时十世德木活佛就住在大昭寺旁的嘎如厦,只有工尊德木女神与之作伴。
那年他12岁。
神舞的中间还有滑稽戏,同样是喇嘛表演,剧情简单,剧中人戴着粗朴的面具,穿着工布的兽皮装,手持火枪或长刀,或是抢夺猎物、或是抢夺帽子。
末代德木活佛的镜头中保留有半个世纪前这些表演的珍贵镜头,他已经不穿着喇嘛红袍,也不是高高在寺庙的阁楼上观看,而是就在表演者中间。他的镜头闪烁,将家乡的喜剧摄入镜头。此时,我们身后一个女人声音极尖地笑起来。
笑声里,表演者气喘吁吁地退入大殿。有人在喇叭里大声喊了一句藏语,接着又用汉语翻译了一句:“明天再有哦。”
而明天我们将离开德木寺,去寻找老德木寺的遗迹。沿着河谷向前,就会走上一条茶马古道,翻越德木寺最初建立的德木拉山口。
梦之篇
大军之中一羽毛
我们走上古道,俯瞰德木寺,一栋大殿孤零零地伫立在如鼓般的小丘上。除了地形依旧,一切都和德木活佛在20世纪40年代拍摄的德木寺大不相同。
“德摩,居工布极东,居民二百余户。有大喇嘛寺一所。”湖南人陈渠珍如此描写他看到的震前德木寺。
1909年清军入藏作战,两年之后,由于辛亥革命突然爆发,东南诸省一夜易帜,清军分头东归。这段历史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政治,对于德木活佛世系的遭遇,都有极大的影响。
根据陈渠珍的记载来看,早在1910年,德木寺就已经搬迁到米瑞。地因寺名,这片肥沃的平原被称为“德摩”。1953年在德木寺出家的僧人拉巴回忆道,老德木寺搬迁的原因,是“波密王”派兵来征讨老德木寺。
陈渠珍笔下那“极壮丽”的第巴府邸,就是新德木寺脚下的德木宗所在地。三层楼高,屋顶已经大半倒塌。我们推开宅院大门,走过齐膝深的野草,绕过倾颓的香炉,站到大宅门前。这里没有上锁,将铁丝拧开,即可进入一条狭窄的过道。
由于年久失修,墙面已经鼓突剥落,据村民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里才不再使用,我们的确在墙面上看到了日久黯淡的毛主席语录。整个建筑为回字形,房屋众多,木质回廊宽阔。下层木柱粗大,房屋开间很大,据说为马房和耕牛房。上层则房屋众多回环,可见有灶台等痕迹,为居所。
拉巴掰着指头回忆,德木宗管理下超过二十个村庄都要来此处纳税。其中今日的米瑞有12个村,鲁朗有5个村,在米林县还有一些村落同样属德木寺管辖。
中庭深草过膝,当年这里正是钟颖和陈渠珍密议讨伐波密之事的地方,也正是此处见证了陈渠珍和工布姑娘西原的婚礼。
走过书中称为“三十九族”那漫漫的长征,又数番经历生死的陈渠珍,终于来了到山明水秀的德摩,这里是他的小小天堂。
当时陈渠珍已有妻室,年纪近西原两倍。然而命运怎能揣测?当日后陈渠珍远逃羌塘,豆蔻之年的西原万里相随,而一路保护他化险为夷,直至兰州,此时贫病交加、远离家乡的西原终于一病不起。一个工布少女,家山万里,其中的坚贞勇敢,文字怎能承载?
弥留之际,西原又梦见了故乡的青青风景,母亲一手持糖,一手递给她青稞酒,这是一个当年仅19岁少女的最后之梦。
24年之后,53岁的陈渠珍旧梦重温,写到此处,终于“肝肠寸断,余书从此辍笔。”我们来到这处渐渐化为尘土的老庭院,距离西原去世已过百年,陈渠珍也已经去世61年。
翻越德木拉
德木是陈渠珍率领的清军驻扎之地,德木活佛世系世代与清廷有密切关系,这要从四世德木活佛为顺治皇帝做灌顶开始。而在这一年,其间的关节更为复杂。
首先是德木寺不堪波密王的入侵,虽然将寺庙从鲁朗迁移至米瑞,却有心借助清军之力,彻底摧毁这个世仇。早在四世德木活佛时期,德木寺就被波密人焚毁一次,可谓积怨已久。而驻藏大臣联豫和统帅钟颖同样梦想消灭波密,剪除工布地方最大的割据势力,和赵尔丰一竞高下,建立声威。
九世德木和联豫又是世交,在九世被害之后,正是联豫直接上书光绪皇帝,要求皇帝指定其转世,其后的宣统皇帝遂下诏指定了十世德木活佛。德木世家也希望借助清廷之力,东山再起。
在众人的梦想推动下,1911年早春,陈渠珍率先锋越过积雪未化的德木拉山,横越鲁朗,用兵波密。
“波番乘势侵入,危害不堪言状。第巴等屡请为策久远。余亦不忍工布被其蹂躏……余决定先抚后剿,拟率兵三队至鲁朗,意在耀兵绝赛,宣扬德威。”陈渠珍如此说道,然而在鲁朗——东久——拉月一带的狭长通道上,他所在的钟颖军遭遇了惨重的失败。
时间已经是秋季,德木拉古道上依旧草木不衰,我们可以看见路基铺设有大块青石。不久之前的一次山洪暴发冲毁了河边的道路,只有沿着山脊前行。人烟逐渐稀少,只有孤单的石砌牛棚在路边。回头能看到红色的工布式铁皮斜屋顶,更远则是雅鲁藏布江。
小路蜿蜒而上,天气颇冷,背阴处土地结冰,日晒后融化,极其泥泞。我们走走停停,受伤的膝关节不停颤抖。
行至山顶,鲁朗在望,山脚下是老德木寺的遗址、鲁朗花海和密林中的东巴才村,再向前就是平缓山谷地上的鲁朗各村。左为色季拉山,318国道盘旋其上;右边如刀锋般横列三座雪山:贡布拉尊、加拉白垒和南迦巴瓦,大峡谷在云层之下,隐不可见。鲁朗形胜,尽在德木拉山一览之中。
朔风东来,公路正在修筑,路基下的土层中突出锋利的冰刃。沿这条泥土路基向下,就是老德木寺遗址,就此进入鲁朗。
当时鲁朗不过是一条狭窄的走廊,居民颇少,东久沟反倒是一个居民点。“沿途长林丰草,乱石塞途。”陈渠珍率先锋抵达东久官寨后,皇室亲贵,少年得志的主帅钟颖率领步兵一标,炮兵工兵各一营,也进驻东久。
清军的战略很简单:步步推进,由东久至拉月、排龙、通麦,肃清两翼,并指向倾多寺,最终战败波密王白马青翁。这是一条狭长的山谷走廊,一面为高山,一面为大江,惯常山岭作战的波密军早有准备。
陈渠珍部前进至排龙,即遭遇埋伏。波密军正面据险防守,两翼则攀援山岭,截断清军后路。清军前锋和主力隔绝,如同长蛇被困,陈渠珍不得不带兵退守东久,与主力汇合。亲贵钟颖对此完全束手无策。几日间,波密军翻山越岭,浩荡而来,已经完全包围东久附近山岭,隔河与清军对射,战法多变,或推石下落,或从绝壁攀绳而下偷袭。若不是西原提醒,恐怕陈渠珍也早已被杀死。
清军所能控制的,只有通向鲁朗的一条小桥为后退的命脉,如果不是清军有新式“格林炮”(即仿制的加特林机关枪)等先进火器,此桥一被夺,只有全军覆灭一条路。
不得已,又以陈渠珍开路,通过小桥,以强大火力掩护突围。当夜,“弹火喷飞,光明如昼。”主帅钟颖害怕卧床不起,最后被士兵们扛着突围。“(波密军)猝不及防,火枪土炮,发射迟缓。”清军才能突围成功,退守鲁朗,至此战局僵化。
突围成功的陈渠珍,拿着一个面饼还没吃几口,就倒头睡去。而对于一心想建立不世之功的钟颖,更是美梦破灭。他被驻藏大臣联豫立即撤职调回,以罗长裿取而代之。在德木拉山东麓脚下,老德木寺遗址旁,他与陈渠珍等话别。
钟颖以此为大耻,将罗长裿认作不同戴天的仇敌。日后兵变突发,罗长裿被乱军所杀,据说就有钟颖的作用。他在拉萨统军,以德木活佛的丹杰林寺为基地,和藏军对抗竟达数年之久。等到钟颖离开西藏之后,德木寺的全部产业被彻底剥夺,年仅12岁的十世德木活佛被软禁。
后来在袁世凯政府的审理下,前清皇室贵戚钟颖因治藏不力,谋害罗长裿而被处死。
梦中之梦
钟颖当年离开德木拉山时,还在愤愤踢着脚下的青石。这些青石都是老德木寺建筑的遗址,如果不仔细看,无法看出这里曾有一个规模可观的建筑群。如今已经找不到完整的建筑,只剩下一两堵石墙,石墙上有寺庙特有的狭长窗台。寺庙墙上的彩绘早已毫无踪影。
走在这里,你无法分辨你究竟是走在一条古道上,还是走在寺庙的墙基上;你跨过的原先究竟是一扇窗,还是一扇门。这里坐落于鲁朗花海牧场旅游区的狭长草原上,如今是种牛场,牧民们将德木寺的石块垒成牛圈,石墙后面时常露出巨大的犄角。
更多的石块陷进地里,已经和土壤板结在一起。小河横穿遗迹,更让人无法辨别原先的寺庙结构。就是在这里,四世德木活佛从这里出发,和五世达赖喇嘛会合,一同前往北京去拜见顺治皇帝,那是大清帝国刚刚兴起的16世纪,德木寺如同幻梦一般的历史,从此开始。日后八世德木活佛疯游西藏大地,人们还传言:如果德木疯了,西藏就会幸福。
同样是在这里,在大清帝国的最后几个月里,陈渠珍走在这片废墟中,思索着自己的梦想。几个月后兵变爆发,主帅罗长裿当即被乱军杀死,陈渠珍带着西原和百余乡亲,踏上茫茫北归之路。数月之后,最后残余的11人抵达兰州,未过数日,西原病故。陈渠珍回顾这两三年西藏之路,茫茫如梦,也难怪他用《艽野尘梦》为自己的回忆录命名。
老僧人拉巴说,德木寺是一座迁徙的寺庙,早在第一世德木活佛的时代,就预言了德木寺在西藏大地上的迁徙路线:这座奉鸡爪女神工尊德木为护法的寺庙,先从昌都出发,到鲁朗(旧德木寺),然后到米瑞(如今的新德木寺),按照预言,之后还要渡河去米林,据说会在岗噶大桥一带建立新寺。
之后去哪里?这个古老的预言已经丢失,拉巴说他记得会经过很多地方,最终达到拉萨,来到德木活佛住锡的丹吉林寺。
然而这并不是终止,这只是德木寺永久迁徙中小小的内圈,此外还有中圈和大圈,层层嵌套。在永恒的时间里,德木寺不过走了最初的几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