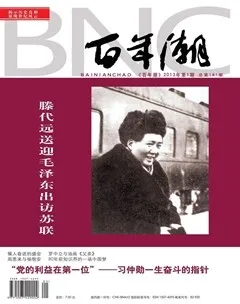寻人启事
2013-12-29曲跻武
已进入耄耋之年,就木之期,难卜朝夕,还要打空拳似的,寻找一个70年前相处只有四个月的同学,似乎近于开玩笑,但命笔的时候,却是十分郑重的。因为,他是奇迹般地逃出日本野兽南京大屠杀虎口的一名国民党军士兵,他的证言,应当是对日军在南京灭绝人性行为的最有力证明。但是,在经历了新中国诞生63周年的今天,我一直没有看到或听到有关这个董某的任何记叙,甚至一点风闻也没有。看着他那一段奇迹般的经历行将湮没,我也只能挥笔作这样的一搏。
事情要按时间顺序来说,原来,1938年8月至12月,笔者在陕北枸邑(今旬邑)陕北公学分校(第四期)学习,编队为第三十九队第一分队第一班,分队长兼一班长高扬是河南人,1938年终,我们都随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到了晋东南,嗣后,高又随校去了山东,全国解放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检察长。
后来长期担任《文艺报》副主编、文艺评论家的侯金镜同志(“文革”中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迫害致死),属于这个队的第三区队,负责编全队的壁报,笔者所在的班,有一位同属山东籍(鲁西莘县或堂邑)的同学董慎五,也就是他原籍县立中学毕业的学生。1937年7月,全面对日抗战爆发,董慎五投考了国民党军队通讯兵部队。日本军队进攻南京时,他属于守城部队,从12月10日起,他参加光华门的守卫战,防御工事就是城堞和城墙顶端临时挖掘的简单的掩体。南京古称金陵,是六朝古都;到了明代,更加固了城墙的修建。因而城墙较厚,所以战士们可以临时挖掘简单的掩体,以资防御。但由于日军的武器相对先进,且有空军助战,所以在城门墙垣守卫的士兵,还是死伤累累。据董称:为了留出掩体位置让别的战士参加守护,伤者与死者都被抛掷城墙内侧,血肉狼藉。这样的防御作战,也只坚持了两天。
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内的国民党士兵,有些仍在和日军激战,但由于分散行动,近于各自为战,且没有重武器,这些英勇的战士,没有多久,便死亡殆尽。
国际红十字会,从日军进攻之日起,便在金陵大学校院设立了难民收容所,一些市民也聚集该处,希望能藉国际公法之助,躲避日军的抢掠奸淫。那些没有在激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军士兵,也就脱去军衣,从居民家中换一身便服,混迹于难民人群中。董本人便是这样做的成员之一。不过,他本是一名青年学生,为他换衣服的那家市民,出于同情和怜悯,为他换的便服甚为合体,一眼望去,就是一个真正的市民。自然他也混迹于难民营中,解决饮食问题。
董讲了日军筛查的三道关,和他本人逃出南京的奇迹。开始几天,日本占领军,首先占据了国民党政府各个官署及所附公共建筑,使侵略部队安顿下来。接着便开始搜捕躲藏起来的国民党军士兵。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到难民营筛查。董叙述了他在三次筛查中的具体情况。
第一次筛查:日军包围一片场地,把难民营的一大批人汇集起来,接着宣布:南京本市的人站到一边,非本市的人站到另一边。董读过初级中学,自然能讲普通话;再者,江苏、山东两省是邻省,而南京还不属于江苏,所以董就充作南京市民站到一边。日军和翻译员逐一查询,他能够应付裕如。而那些明显外地口音的,便是屠杀对象。
第二次筛查:日军包围场地后,宣布在本市有家属的人站一边,没有家属的留原地不动。因为,除国民党部队以外,南京还有警察、宪兵一类武装人员,他们在南京居留较久,语言关容易混过去,但除军官外,一般成员不能带家属。所以,有无家属一关,可以把这类非正规军队的武装人员区分出来。董这次动了脑筋,他左右用眼扫了一下,看到右侧一位半瘫痪的老太太扶着一根拐杖,颤巍巍地在流眼泪;董于是弯下腰来,把老太太的一只手臂搭在自己肩上,走进在本市有家属的人群一边了。换句话说,他已经使自己完全摆脱了国民党武装人员的圈子了。
但是,他没有躲过第三次筛查。
原来,这些噬人的野兽第三次筛查的做法是,把所有在金陵大学校院避难的中国人(男性),统统赶到广场上,宣布自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统统站出来,董根据自己的经历判断,这些人都被作为国民党军士兵屠杀了。因为,他就是从广场上直接被驱入被屠杀者的行列中的。
董作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当即被拉到像流水一样被驱赶到长江岸边即将处死的所谓中国士兵队伍中,沿着城北门内大街前行。队伍已经走进城门洞。这时,负责执行屠杀任务的日军军官,把系在肩上的一个皮包解下来,从面前即将处死的人群中,信手把董拉了出来,同时顺手写了一个纸条,命令董按纸条所示地址送到那里。恰好是董被拉了出来,事情虽属偶然,但也可以理解。因为董既属青年,又身材修长颇有几分女性气质。同时也不难想见,这些日军指挥官,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些将要被屠杀者,不过是一些适于兵役年龄的市民。却说董当时等于从死神面前抽身,拿了纸条提上皮包,如飞一般离开赴死的队伍向后奔跑。在惊惶中,他连皮包中是什么东西都不清楚,因为他不敢触动。他按照地址,向警卫日军交了东西,便立即向城的西门疾走。那张纸条成了他出城门的路条。一夜狂奔之后,他逐渐看到愈来愈多的难民队伍,他一路向农民乞讨,终于到了新的政治中心武汉。他没有向国民党的军事部门报到。因为他已经明白了,国民党政府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法西斯的进攻。回忆从八一三淞沪会战,到12月13日南京失守,为时不过四个月,从军事上说,日军由上海到南京,中间还有一条被比拟为“马其诺防线”的国防工事。但国民党军队并未能利用坚固的防御工事作稍长时间的防守。
董希望自谋出路,但没有任何就业或就学的机会。他于是向几家鲁南、苏北的商店乞食若干时日后,找到了中共驻武汉的办事处。此时,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已公开招生,他便被介绍到枸邑的陕北公学(关中分校)学习。我和他一个班,一次,全班同学闲话个人经历,董沉痛地讲了这一切。
在陕公时,侯金镜负责编全队的壁报。他得知董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后,让我把董的这段经历写篇壁报稿,登在全队的壁报上。
令人奇怪的是,董没有于陕北公学结业之后随抗大一分校到华北敌后(先到太行山区,然后到山东根据地)。董身体修长且有几分女性气质,擅长唱“芪腔”(在山东各地流行的地方戏,也叫“肘姑子”)。在陕北文化娱乐贫乏的情况下,连当地的“秧歌”(农民唱的小调)都被发掘出来,编出如《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少数业余京剧爱好者,还组织了京剧团,自编节目演出。如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届京剧院院长史若虚(原名史宝玺),山东第一师范学生,他爱好京剧,到延安后,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后来到太行区鲁艺晋东南分校下设立的京剧团工作,颇获好评。1941年,史自编自导自演《孔雀东南飞》,引起轰动。同一节目的晚会,连演四个夜晚。驻村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有三个青年妇女自杀(根据地建立妇女救国会,对妇女进行文化和政治教育,提出她们有各种“自由”。但是长期的封建家庭的改造,非一日之功。《孔雀东南飞》的剧情及表演的成功,让这几个青年妇女痛不欲生)。野战政治部下令停演。以后,因为政治运动和急剧的对敌斗争,这个剧团解散了,我们之间也失去联系。
董慎五唱山东地方小戏很有水平。但在延安的文化娱乐活动中没有看到他的影迹。1943年后半年“整风审干”的史料,也没有发现他的名字。总之,自1938年我离开陕北公学以后,他就消失了,特别是与文艺界人士多有联系,而且当年留延安时间较久的侯金镜,也不知道董的下落。另外一位长期在部队工作,一位在后勤部门工作多年的同志,都知董的经历,但这三位原陕北公学同学均已仙逝。
南京大屠杀已过去75年了,作为最直接有力的见证人,董慎五何处去了?是否还在人世?可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望知情者见告,十分期待!
2012年10月25日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