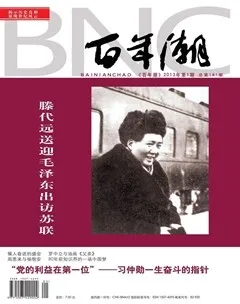邓小平为深圳火车站题写站名
2013-12-29吴松营
邓小平在第二次视察深圳的半年前,就亲笔为深圳新火车站题写“深圳”两个字。邓小平的题字,又恰恰是我受委派从北京中南海取回来的。
1990年4月“退休”之后,邓小平已经很少给各个地方题词。1991年,在中国仍然被“姓社”、“姓资”的争论困扰的时候,邓小平欣然为深圳新的火车站题名,有着很特殊的意义。
深圳罗湖火车站是古老的广九铁路的“边境”站,也是中国内地南大门的重要口岸。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进出口物资转运,尤其是中国内地运往香港的各种粮油肉菜等生活必需品,都必须经罗湖火车站。可是,原来的深圳罗湖火车站的设施不但落后,而且十分残旧,候车室只有100多平方米,运力方面也只有2条正线和4条到发线。这显然不能与深圳特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不断扩大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形势相适应。加上香港回归的日子越来越迫近,总不能让香港和海外同胞,还有外国友人进中国内地南大门时,留下不良的第一印象,感觉进入中国内地还是破旧不堪。
经中央批准,深圳新火车站的建设于1989年11月23日破土动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亲自担任深圳火车站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这不但是一项当时属于大型的经济建设,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深圳市委、市政府,铁路部门和施工单位都全力以赴,大力支持。深圳新火车站建设进展顺利,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新火车站的主体工程就基本完成,开始进入装饰阶段。
1991年初,有一天,李灏到火车站工地检查工作。具体负责火车站建设工作的郭胜林请李灏题写深圳火车站的站名。
李灏笑着说:“不合适,我写不合适。”他想了想,又说:“如果能够请邓小平同志写,那就好了。”在场的所有人无不拍手赞成,同时又都担心能不能真的请到小平同志题字。
于是,李灏这位从50年代初期就被调到北京中央机关工作的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开始启动“另一个工程”——想方设法,请邓小平为深圳新火车站题名。
1991年4月底,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音像出版整顿工作会议。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接到李灏的秘书刘润华从深圳打来的电话:“是吴副部长吗?中央办公厅通知,邓小平同志已经为深圳新火车站题写了站名。李书记说委派你到中央办公厅去领取小平同志题字,尽快带回来。”
我高兴地连声说:“行,行。正好我们的会议今天就开完了,你把同中办联系的具体办法告诉我。”
第二天上午10时整,我坐车到达中南海西门。中办的同志看了我的工作证件之后,领着我到秘书局二楼的一个办公室。秘书局的同志了解我的心情,马上把邓小平的题字给我看:在相当于一张报纸大小的宣纸上只有“深圳”两个大字,而不是我们原来希望邓小平题写的“深圳站”三个字,也没有落款签名和日期。好在附有盖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公章的一份文件,说明“这是邓小平同志为深圳新火车站的题字”。文件还要求深圳市委要妥善保管和使用,可以在当地的党委机关报上发表。我在文件收发簿上郑重签字之后,秘书局的同志就小心翼翼地把邓小平的题字折好,连同秘书局的那份文件装进一个公文袋里,交给我带回深圳市委。
我心情无比激动地离开中办秘书局,离开中南海。在路上,我好像突然醒悟:邓小平这个时候能够亲笔为深圳题字,意义绝非一般。老人家没写“深圳站”而写“深圳”,意义更加深远!而我能够把邓小平的题字带回深圳,其任务有多光荣!
回到住处之后,我马上收拾行李,把装有邓小平题字的文件袋放在小行李箱中间,在招待所办妥退房手续,当天中午就直奔首都机场坐飞机,下午就到达广州白云机场(深圳机场还没有通航)。从广州下飞机之后,我又乘坐机场大巴到市内,再坐火车回深圳。到了深圳火车站以后,我再坐公共汽车回通新岭的市委宿舍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当我刚刚下公共汽车,在车门边还未站定,一个二十出头的男青年见我对行李箱这么紧张,以为行李箱里装着不少钱或很贵重的东西,竟乘着人多混乱,扑过来要抢我的行李箱。
我心里一急,一股巨大力量涌了上来,沉下身子站一个大马步,一手紧紧抓住行李箱的提把,一手护住行李箱的边上,用尽全力狠狠一甩,把那个家伙摔出两米开外。
有人大声地喊:“抓小偷!抓小偷!”很多乘客都见义勇为,去追赶小偷。
我心里记挂的是行李箱里面的重要文件,顾不得其他,快步回到通新岭三栋的家里。
晚上,我除了同李灏书记的秘书刘润华打电话,还给市委秘书长任克雷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同志的题字已经带回来。
第二天一早,我和任秘书长、刘秘书都来到李灏书记家里。
李灏正准备吃早餐。在客厅里,我把邓小平的题字和文件交给他。李灏马上把邓小平的题字在茶几上展开,认真观看,好一会儿都没有做声。估计他大概是在思考邓小平为什么没有按深圳方面的希望,写“深圳站”,而写的是“深圳”两个大字,还在琢磨其中的含义。
至于邓小平为什么不写“深圳站”而只写“深圳”两个大字?这恐怕不是为节省笔墨的问题。广义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试验田。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后,深圳都不能“靠站”、“停站”,而必须勇敢地闯,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一直向前,向前!
我和任克雷也都跟着认真地观看邓小平的题字。我自己看得比在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时更仔细。总体上看,邓小平的“深圳”两个字还算苍劲有力。但毕竟是快90岁的老人,“深”字下部的“木”右边的那一捺抖了一下,像一个人站立时两只脚中一只略为斜放似的,有点不大平衡。
其实,当时在场的几个人应该都看明白“深”字右下捺有些过高的问题,但又都不好说明。我却终于忍不住,指着“深”字下部“木”字的那一捺,直率地说:“这一画要是稍稍往下放一点就好了。”
李灏听了哈哈笑起来,看了我一眼,不置可否。然后就叫秘书把题字折好,装回文件袋,交给任克雷处理。
李灏对任克雷说:“要按中办秘书局对文件的要求,妥善保管和认真处理好。可以通知火车站郭胜林他们和特区报社。”
市委办公厅很快通知广深铁路公司派人领取邓小平题写的“深圳”两个大字复印件,以便按要求制作牌匾,同时又通知《深圳特区报》派记者拍摄、按规定公开报道。邓小平题字的原件则保留在市委办公厅的档案室。
据深圳市盐田区委书记郭永航在2011年6月的一次回忆,2000年初,他在市委办公厅任会议处处长的时候,有一次碰巧路过档案室门口,看到一大堆准备销毁的资料里面有一个中办秘书局的大信封,写有“深圳市委李灏同志亲启”字样。他马上拾起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就是邓小平题写的“深圳”两个字的原件。他又在废纸堆里继续查找,又拾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盒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深圳时谈话部分内容的录音带。他马上向上汇报,通知深圳市档案局派专人前来领取两件重要档案。档案局的一位局长领到那两件贵重文物档案时,情绪激动,手都有点发抖了。而那两件重要历史资料,都是过去经我亲手交上去的。郭永航同我谈起此事时,我们两个人都无限慨叹。
1991年国庆节,深圳火车站的建设工地仍然一片繁忙。建设者们没有放假,而是在赶最后的建设项目和装修工程。
10月12日清晨,南来北往、川流不息的客人首次看到新火车站天蓝色幕墙顶部镶嵌着金光闪闪的“深圳”两个大字——却都还不知道是邓小平亲自题写的。
下午16时,在深圳新火车客运大楼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出席典礼仪式并剪彩。国家铁道部部长李森茂、深圳市长郑良玉致词。出席典礼仪式的有国务院有关部门、广东省、广州军区负责人,以及港澳知名人士,新加坡、埃及、科威特等国家的驻华使节。在落成典礼仪式上,最引起轰动的是嘉宾揭开新站大堂中间鲜花簇拥的大台上的红纱,显示出放大了的“深圳”两个金字,宣布这是邓小平亲自为深圳新火车站题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当天特地赶到深圳新火车站视察。
新火车站大楼落成典礼之前,我特地去看了邓小平题写的“深圳”两个大字的放置情况。一看,“深”字下部的“木”字右边那一捺给放下来了,使两个大字显得更端正、好看。
1992年1月19日上午,当邓小平乘坐的中巴行至火车站前面的时候,大女儿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上方镶嵌在蓝色玻璃幕墙中“深圳”两个大字,对父亲说:“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二女儿邓楠则打趣地对父亲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
车上的人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只是露出笑容,对他亲笔书写的“深圳”这两个字表示默认。也很可能,邓小平的内心里面还有一层人们不知道的意思:同意给深圳题字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再次到亲自创办的特区来看看,说说话、吹吹风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