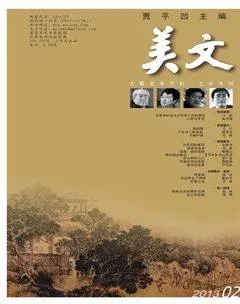远去的牧歌
2013-12-29杨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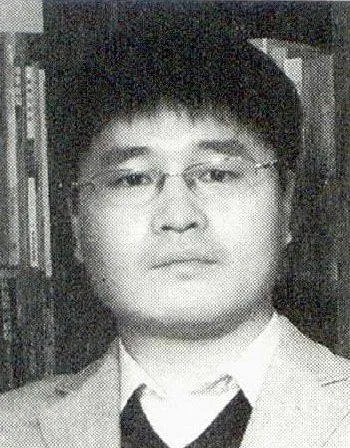
对于我们这些命定只能生活在别处,却又无可救药地慕恋极其神秘的游牧生活方式彻底的美和自由的人而言,草原只能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独特存在。她就在那里,在遥远的他方或者文字的极深处,如母亲般博大的胸怀始终向无限敞开,容纳着远去的大雁和归来的游子,任由他黑灾、白灾、旱灾、鼠害轮番折腾,过后仍是绿茵一片芳草遍地化育万物。她就在那里,在心灵的最深处,时时映衬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平庸和逼仄。每一次内心向她的切近,都是一次近乎朝圣般的精神仪式。她早已凝结为永恒的乡愁,我们成了游子。
游子与额嬷格的相遇,一如额嬷格与草原母亲的相遇。这种相遇,乃是一种精神的发生。
然而,又有几人知晓,额嬷格,草原上的额嬷格,曾经经历过的苦痛和正在经历的选择的艰难。这种苦痛和艰难,乃是因着一种对精神的执着守护。
曾经喝过一百个阿妈熬的奶茶的额嬷格,经历过“爱喝酒的弟弟”松布勒的含冤而死,为了为松布勒伸冤,她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肉身上”,任由“鲜血浸透了羊羔皮的蒙古袍”,最后却只能把悲痛埋藏在心底;她还在暴风雪肆虐的夜晚,为了解救不知如何抵抗暴风雪的汉人邻居,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冰天雪地,从而使自己必须面对丧子之痛,也把自己的家庭推向了悲痛的深渊……即便如此,即便悲痛让她一夜白头,让她只能在儿子遗留的最后一泡尿液中嗅到儿子的气味。五十岁的额嬷格仍然跨上马背,担起了儿子远去之后留下的苦日子。她的“歌声带着一辈子的孤独和凄苦”,却“把忧愁踩在马蹄下”“把眼泪埋藏在心里”“一年又一年,无论日子过得多么难”,“脸上总是带着无声的笑”,把整个家庭的负累连同悲痛“默默无声地扛起来。”
心比蓝天还辽阔的额嬷格,她对草原母亲的忠诚守护,守护的,乃是一种精神血脉的延续,一种与天地万物交往之际的无比宽广无限涵融的精神姿态,一种超越了族群、阶级甚或种群的博大的爱。这种爱施与之处,天下一切生灵和人类一样都是草原的孩子,他们之间“不能互相使用鞭子。”而此时的额嬷格,则成了草原万物的母亲。
如若草原真有魂,这魂,必定与额嬷格血肉相融密不可分。
“轻轻一抖缰绳,英勇无畏地穿过风雪雾霭,把碧绿的年华留在了草原的岁月里”的额嬷格,已然老去的额嬷格,不愿把蒙古包扎在没有草的地方,不愿意把草场卖给他人,不愿意在蒙古大营吃低保。她要把孙子培养成为草原上心胸宽广的马拉沁,她告诉他巴尔虎人不能离开自己的三个母亲,告诉他“不要向往城市的热闹,骏马在楼房的森林里找不到回家的路……”告诉他“草原是一本大地上的书,蒙古人一辈子在马背上读这本书。”告诉他“我的草场不能交给不心疼草原的人”,告诉他“要善待天下一切生灵”……
就这样,额嬷格“一点一点把草原交给了我”。
然而,额嬷格祖孙二人,还得面对现实的困境。
为了给敖登高娃治病,他们必须把草场使用权流转出去五年。在这即将来临的一千多个日夜里,七十八岁的额嬷格坚持要和孙子一起,精心守护草原,以便“一起走过这条五年的路”,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事里。”
与回荡在草原上空的牧歌的悠远历史相比,五年的时间实在算不得漫长。然而,我们总难免忧心:耕地会代替草场,会叫的摩托和汽车会代替骏马,蒙古大营会代替跟着羊群走的蒙古包,连巴尔虎人也不再放牧,没有人在意长生天高兴不高兴……属于这个古老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传统,属于额嬷格艰难守护的世界,会与我们的现实渐行渐远。
她或许终将幻化而成为一个凝固的形象,与诗意的纯美的田园生活一起,永留在我们文学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