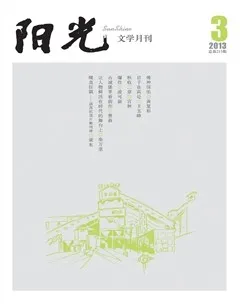让人物鲜活在时代的舞台上
2013-12-29秦万里
小说是故事,故事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在小说家笔下,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中闪耀着动人的光彩。因此又可以说,小说是时代的镜子。小说映照了时代,时代又会作用于小说。小说家把他的小说放置在时代的框架之中,当他的故事从一个时代行进到另一个时代,这个故事就会发生逆转,故事虽然是小说家制造的,这种逆转却常常不能以小说家的意志为转移。
最重要的还是人。小说家的故事是小说家制造的,生活中的故事却是人制造的。其实,时代也是人制造的,时代是大人物小人物千千万万人物的综合力量制造的。生活中的故事是人制造的,人们总是在用自己的行为制造故事。生活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故事,是因为生活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制造了不同的故事,使我们这个世界丰富多彩。按照这个逻辑往下说,小说家的故事也是人制造的,小说家塑造了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让这些不同性格的人物去制造不同的故事,就产生了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小说。
千千万万人物的综合力量制造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个体的人物,作用于人的命运,也作用于人的思想和行为。这仍然会涉及人的性格问题,当一个时代不可阻挡地扑面而来的时候,不同性格的人物会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人物会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命运的通道。敏锐的小说家善于在芸芸众生中发现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人物,高明的小说家让他的人物鲜活在时代的舞台。
让我们来看看陈建功的小说。
陈建功是著名作家,他写了很多小说,在这里我只挑出一个短篇小说来谈,这篇小说叫做《辘轳把胡同9号》,发表于1981年。小说的故事也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前前后后,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许多被否定的事物恢复了往日的光彩,许多曾经在一时间辉煌起来的东西又黯然失色了。这种变化本身就耐人寻味。在那个年代,许多小说家都写了这种变化,许多作品产生了轰动效应。陈建功的小说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篇《辘轳把胡同9号》就很有意思。
在小说开头,陈建功先给读者们讲解一个了词:“‘敢情!’——这又是北京的土话。说‘敢’字的时候,您得拖长了声儿,拿出那么一股子撒漫劲儿。‘情’字呢,得发‘轻’的音儿,轻轻地急促地一收,味儿就出来啦。别人说了点子什么事儿,您赶紧接着话茬儿来一句:‘敢情’!这就等于说:‘没错儿!’‘那还用说吗?’甚至可以说有那么点儿‘句句是真理’的意思。”
如果我们把这座小院,把辘轳把胡同9号当成一座小小的舞台,那个冯寡妇就该出场了:“这里有一位姓冯的寡妇老太太,也和别的老太太一样,喜欢接在别人的话茬儿后面说:‘敢情!’——您可别大意了。冯寡妇的‘敢情’却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您要是不够那个‘份儿’,不足以让她羡慕、崇拜,人家还是金口难开呢。”看来这个冯寡妇还挺牛的,不是什么人说话都能得到她的赞赏,就连她那个当上了厂长的儿子,也不被她放在眼里。在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冯寡妇只佩服一个人,那就是锅炉工出身韩德来,不仅仅冯寡妇,“整个小院儿,除了住南屋‘刀背儿房’的张老师和冯寡妇的儿子大山,谁不以东屋住的韩德来为荣?有了韩德来,整个9号院儿在辘轳把儿胡同就牛起来了,腰杆子硬起来了。”因为韩德来当了工宣队,成了什么“代表”,甚至还吃了国宴。更重要的,韩德来竟然和毛主席握过手。于是,这座四合院里的人们就有了一个看得见的偶像:“从这天起,只要韩德来端着茶缸子,往门前的小板凳上一坐,冯寡妇肯定拿着手里的活计凑过去听他开聊,又肯定瞅准了话茬儿,时不时来一句‘敢情!’”其实,韩德来完全是根据道听途说和自己的想象在胡侃:“‘他大妈,知道吗?苏修、美帝那儿,都闹上红卫兵啦!’韩德来的谈锋,又引向国际问题了,‘家伙!您看看咱的文化大革命,这招儿多英明!等着吧,甭长了,赫鲁晓夫(他就知道赫鲁晓夫)、尼克松,也都得挂牌儿上台,撅着去了……’”就这样的胡说八道,冯寡妇也要随声附和,表示出百分之百的支持和赞同。有了冯寡妇和院子里的忠实听众们,韩德来的胡侃更是没边没沿,他不仅侃政治,侃国际问题,还侃经济:“瞧你们这沉不住气的劲儿!什么赤字白字的,怵什么?告诉你们,咱中国,心里有底!要不,干嘛老说形势大好?那是瞎说的?咱就光说那水吧,咱中国的水都卖钱!没听说吗,山东那地界,崂山,那水,值老鼻子钱啦!弄个瓶子咕咚咕咚一灌,往大鼻子那儿一搁:掏钱呗您哪!家伙!水呀,有个流完的时候吗?光这就够赚的啦……四化?八化也化了……这话说得冯寡妇连连说‘敢情’!乐得拢不住嘴。四周的人自然也喜气盈盈,好像觉得心里踏实了好多,韩德来呢,说完了,在人们轻松的笑声中,耷拉着眼皮,细细地品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越发自得其乐了。”
其实真正能侃的是陈建功,他把老百姓的语言模仿得惟妙惟肖。
韩德来不仅自得其乐,还给了我们这些读者好多乐子。在那个年代,确实有很多荒唐的“乐子”,更发生了很多无法挽回的悲剧。在那个年代过去之后,有的小说家写悲剧,有的小说家寻找“乐子”,在高手笔下,“乐子”和悲剧同样会成为好小说。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没有忘记这篇小说,是因为“乐子”,是“乐子”让人物鲜活起来,人物鲜活了,就进入了人的记忆。还有典型性和独特性,抓住了典型性和独特性,一篇小说就更不容易被忘记了。陈建功刻画韩德来,已经抓住了典型性和独特性,但是他还不满足,还要朝着人性的深处行进。
后来时代变了,可能还是那样,大人物小人物千千万万个人物的综合力量让时代变了。时代变了,因前一次时代变化而辉煌起来的韩德来,又因这一次的变化而失去了光彩。没有人请他去吃宴会了,也没有几个人爱听他胡侃了,他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不重要了。更让他受不了的是,住在北屋的赫老太一家,过去因为历史上有点儿问题,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在他韩德来面前永远唯唯诺诺的,这回落实了政策,退赔了被抄走的东西,有钱了,抖起来了。那个叫二臭的小子,买了进口摩托车,穿条兜屁股的牛仔裤,成天到处显摆。还有那个张春元,喜欢写什么小说,更不把他放在眼里,竟然还当众更正了他的胡说八道,让他下不来台。甚至于,连院子里最不起眼的王双清,也因为卖了俩早年间的瓷器,发了财。其实“他自己也明白,有什么法子?赫老太太这号的,腰杆儿硬了,自己呢,还镇唬得住谁?啥‘代表’也不是了,退休居家,大场面,也见不着了,陈谷子烂芝麻,总抖露也没劲啊” 。
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韩德来了,韩德来的内心严重失衡了。他曾经是时代的宠儿,他为制造那个时代,或者说,他自觉不自觉的,为增添那个时代的某种气氛,贡献了自己的一点点力量。这与他的性格有关,如果换一个人,同样遇到一个辉煌的机会,可能就不会是他这种表现,这个故事就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当年陈建功还发表了《找乐》,《找乐》刻画了李忠祥,李忠祥也是劳苦出身,却和韩德来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走过的道路也不一样。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性格推动着人物,在属于他自己的命运通道里行进。当然,在小说里面,一切都是小说家推动的。小说家塑造了人物性格,按着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向前推进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就会更加真实可信。
我们来看陈建功接下来如何操作。
某一天,韩德来和邻居生了一肚子气,就跑到大街上,说是要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看见不少人正在排队买电影票,出于某种心理,他一下子就买了四张。家里没有人陪他去,第二天他就一个人去看电影了,“离电影院还有半站地,三三两两的小青年们就捏着毛票儿,眼巴巴地站在路口问上啦:‘同志,有富余票吗?’‘师傅,有票匀一张欸……韩德来从他们眼前走过,心里忽然间升起一种什么感觉呢。他知道自己有四张票,而他们,没有,一张也没有。自己富余的票放在兜儿里,他几乎舍不得轻易撒手了。”让韩德来意想不到的是,受到了长久冷落之后,竟然在这里找到了这么一种独特的精神满足:“他一张一张地把票退出去。每次,退完了,在人们的包围中,板起面孔说:‘没了没了。’心里呢,却享受着一种不可言状的快乐。嘿,简直有一种腾云驾雾之感。”读到这里我们该琢磨一下了,我们会发现,韩德来内心藏匿着一种连他自己都没有觉察的渴望,那就是优越感,时代给了他优越感,时代又夺去了这种优越感,他便欲罢不能饥不择食了。
那是两个时代交替的时期,这个故事发生的前好多年,人们根本看不到好书好戏好电影,造成了某种饥渴。于是,当文化政策打开了一条门缝,一些翻译影片进入中国,便产生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这种现象成了当年北京的街头一景。而韩德来呢?韩德来却在这种街头一景中找到了新的快乐,为了这种快乐,他把留给自己的那张票也给转让了,他转让了电影票,获得了自欺欺人的优越感。“在韩德来的生活里,恐怕只有过去在辘轳把儿胡同9号院儿里神聊,看着赫家老两口恐惧的目光,听着冯寡妇‘敢情’的应和,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享受过这种舒坦劲儿。”打这天以后,“老头子养成个毛病啦,三天两头,在院儿里呆闷了,一颠一晃就上了街,路过珠市口影院,只要见人在那儿排队,就忍不住凑过去,买票,退票,其乐也陶陶。有时留一张,自己进去看一场(举着票,在许多人羡慕的目光中走进影院,也是一种乐趣咧),高兴了,干脆一张也不留,全方便了别人。而后,分开人群,回家。”
后来就出事了,韩老头和几个卖高价电影票的小青年发生了口角,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去了,曾经吃过国宴的韩德来被当成了倒卖电影票的了,韩老头有嘴也说不清了,警察就到辘轳把胡同来调查。还好,老邻居们都特别的善良:“谁能那么缺德,往人家老韩头儿脑袋上泼粪呀?大家伙儿一致认定,老头儿是闷了,闲了,没事儿干,找点儿消遣去啦。二臭更‘嘎’,还翻着眼皮,把这和‘学雷锋,办好事’挂上了。连张春元都说了老韩头儿的好话,这才把这事告个了结。那位年轻的警察把老韩头儿送回来了,临走,对他说:‘闲着不闲着的,甭去那儿干这种事儿了。想看电影,自己买张票,进去看,甭找麻烦。您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我们也相信您。可您要是让那些小流氓揍一拳,来一脚,这辈子不交代了?’”
小说再现生活,敢情!这道理谁都不会反对。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一个巨大的时代就会摆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目光中,同一个时代就是同一个时代,没有什么两样。在一个成熟的小说家目光中,大时代应该更复杂一些,成熟的小说家能够看到时代的肌理。重要的是发现。陈建功发现了辘轳把胡同,发现了电影院门前的街头一景,发现了辘轳把胡同和街头一景中的韩德来,发现了“敢情”,发现了韩德来失去了平衡的心灵,更发现了典型性和独特性。
韩德来是典型性和独特性的结合体,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制造者。无论他是什么,他都在小说家们塑造的人物的海洋中凸显出来了,因为他鲜活,如果他不鲜活,他就什么也不是。还有冯寡妇,还有二臭,还有张春元,还有老街坊们,甚至还有电影院门前的小青年们,他们都在陈建功笔下鲜活起来。他们在时代的舞台表演,他们的表演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秦万里:湖北黄冈人。《小说选刊》 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短篇小说《泥人程老憋》《王小晓飞往东京》以及文学评论等若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