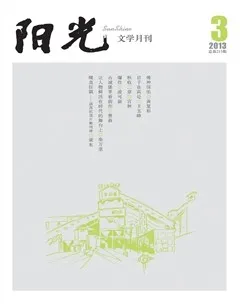普遍的光芒正在照亮
2013-12-29江耶
合上庆邦老师的长篇小说《遍地月光》时,在我的内心,一轮满月正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冉冉升起。我并没有刻意走到阳台上或者下楼去验证一样地寻找它、关注它,也没有感觉到它的光芒越来越强烈,把已经暗下去的地方又重新照亮,把已经埋没、隐藏的事物再一次打捞,并暴露在天地之间展示在众人的视线之中。但我感觉到了光亮的存在,感觉到了这些光芒的强大。不过,强烈的月光也不会带有任何热度,它像悲悯的目光,似乎要将众生一一安抚,使人仰望时即刻升起肃穆的感觉,认识到这样的时光,是庄严而凝重的。
我始终认为,阳光给了我们生活,月光给了我们信仰。阳光照耀世界,成就万物生长,使我们有了源源不竭的可用物质;月光照彻人间,把本来已经沉溺于黑暗的事物拯救了出来,使我们有了敞亮的思想,又用并不遥远处的朦胧遮蔽,引导我们进行无限的美好想象。我读《遍地月光》,感觉到的是,庆邦老师在用故事的方式,试图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普遍的真理,呈现出月光与阳光的紧密联系,呈现出光亮与人类生存、发展的紧密联系。
人类社会终究是从大自然中衍生而出的,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自然演化的一部分,在自然规律之中的,反自然、反本性就是反人性,反人类。然而,就是这样无视自然规律反人性、反人类甚至反自然的体制却能横行很多年,活生生地把人的内心完全地扭曲,使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几乎完全颠倒、崩溃。主人公叫黄金种,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他的名字是“黄澄澄的金色的种子”的意思,很显然起上这个名字的父母是崇尚和敬畏自然的,渴望孩子的一生在自然的生态中会有一个好的收成。但事与愿违,他出生在地主家庭是当时最恶劣的土壤,再好的种子也长不出好庄稼。他父亲病死,母亲在大年初一上吊自尽,两个姐姐出嫁,妹妹送了人。他和弟弟黄银种只好跟同样是地主成分的叔叔黄鹤图一起生活。黄金种选择不了家庭,同样也不像当时宣传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所说的那样,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就能走到贫下中农的阵营中,无论他做出多么巨大艰难的尝试,这个出身像命运一样一直紧紧地把他压得低低。他认为他出生在新社会,他与叔叔黄鹤图有本质的区别,他主动地与地主家庭划清界线并作坚决的斗争。事实上,无论是队长、社员还是小伙伴们,并没有谁真正在内心认他这个账,在所有人眼里,包括他本人,他永远是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他身上永远流淌着地主阶级的血液,他永远不能够真正翻身。
这算不算是人间的一个长夜呢?我们先不讨论这个话题。现在月光正在照亮,我们回到生活现实之中。我们看到,黄金种算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他的心气极高,但他明白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他有足够的生存智慧,他在表面上尽量向社会妥协,压低自己的高度以获得可怜的生存空间。小说像普遍的月光一样对他进行继续关注,用文字把这个狭小的空间打开,把他极度弯曲的身子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月有阴晴圆缺,月在阴晴圆缺中显示出月独有的特性,并与人的情感发展一一对应。月亏就盼满,月满了就盼着下一轮的循环和成长。黄金种已经长大成人,他想找一个女人,他希望自己有一个圆满的归宿,体现出生命的基本意义。他充分考虑到自己的现实,以此作为基础在有限的范围内寻觅。在千思万虑中,他觉得地主家的闺女赵自华与自己差不多,他也真的喜欢上了她,他想方设法地去接近她。但赵自华的目标是要找一个贫下中农的后代,以改变自己的处境,所以她对他很反感,坚决拒绝了他的追求,甚至还讽刺黄金种不知道自己是谁。这第一段情感之旅还没有开启就已经结束。此时,他就想到要离开这个处处压抑的地方。他去找他的大姐,他的大姐为他介绍了一个叫小慧的傻闺女,黄金种觉得太委屈自己,不想同意。经大姐的反复开导,他勉强答应下来后,让他没想到的是,小慧在公社当干部的叔叔不能容忍自己的侄女嫁给地主家的孩子,竟然也没有成功。这对他是又一次的狠狠打击。应该说,黄金种在找对象这个问题上已经是脚踏实地了,他是知道自己是谁的,他想找的人在当时都是条件比较低的。比如他后来确定的追求目标王全灵。王全灵母亲的前夫是当过保长的地主,土地改革时被枪毙了,那时她母亲肚子里已经怀着王全灵。“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王全灵出生在雇农成分的家庭,贫下中农们还是把她和其他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放在一起,列为可教育好的子女。黄金种向王全灵递眼神儿,写了一首顺口溜诗说她是村里的一枝花,买发卡送给她。王全灵对他也有好感,事情正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当队长想让王全灵给他的外甥当老婆王全灵不愿意时,队长就组织村里的基干民兵批斗他们,把黄金种打得满脸是血,躺倒在地;批斗王全灵故意吹灭了灯,男民兵趁机在她身上乱摸一气,甚至还有人暴打她的继父。于此,王全灵只有嫁给队长的外甥为妻。
文学不能让人绝望,月光仍然在安慰,小说想让人物继续冲突,寻找出路。杜老庄让黄金种伤透了心,他对杜老庄彻底绝望了,他只有逃离。能逃到哪里去呢?在那个人们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时期,是没有一块真正被遗落的空地的。人们紧张地关注每一个人,谁都无处可逃。第一次,他被当成流窜犯抓起来,五花大绑地送回原籍。第二次他隐姓埋名隐瞒成分,给队长当干儿子,想给队长当上门女婿,被队长在公社广播站当编辑的侄子调查出了身份,被抓回了村里。人生无常也有常。黄金种第三次出逃之后,林彪死了,毛主席死了,好几个大领导都死了,唐山还发生了大地震。接着,北京有四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被抓起来了,国家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前所划的成分都取消了,什么地主富农,帽子都扔到太平洋里去了,人人的身份都一样了,都是共和国公民的身份。黄金种终于可以不担心再有人来抓他回去了,他也可以自力更生地在异地谋取最简单的存在方式了。他在这个地方靠卖烧饼维持生计,他千辛万苦地劳作,他想着有一天能衣锦荣归到杜老庄。等他攒够了一万块钱,七八年已经过去了。
我出生在安徽中部的农村,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风起云涌。从我一开始记事,我就生活在《遍地月光》的故事背景之中,对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及当时的社会价值、社会风气都非常熟悉。虽然那个极端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但时间并不能突然割裂,它是绵延不绝的。像时间一样,任何事情都不是突然发生,也不会突然消失,它们都在前因后果之中。极端时代的极端事情也是我们的文化充分酝酿发酵的结果,即使现在已经在形式上将它消灭了,但它的气味甚至内在的东西还在,还很有生命力,我们不应该忘记,更不能掉以轻心,它们还在这个社会上起着作用,干扰着社会公平,影响着社会的健康,影响着每一个的生活方式。
我常常思考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个问题。说真的,我更倾向于后者。在前几年,我听过庆邦老师的一个讲座,他跟我们讲他写某一个小说时的想法,他说到了人性中普遍的恶。应该说,在文革时期,人性中普遍的恶得到了最好的气候,在这片墒情已经十分良好的土地上迅速地生长,迅速地开放,生机勃勃,形成气势,一发而不可收。
庆邦老师用一片月光拂去所有的遮蔽,将这些存在于人性最深处的东西放在光亮之中。他在自序中说,“月光是普遍的,也是平等的。月光对任何人都不偏不倚,你看见了月亮,月亮也看见了你,你就得到了一份月光。人类渴望平等,平等从来就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人类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凡是有人类的地方,就同时存在着三六九等的等级差别。”《遍地月光》用文学的方式忽略了这些不平等,给在最低洼处的事物以足够的观照,体现出文学中的人性意义。
月光这个意象被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用了无数次了。月亮、月光都是美好的意象,在叙述爱情、亲情、友情的文字中反复出现,它们代替人们说出了团圆、思念及身临的某个美妙的意境。我至今还能完整地背出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多么恰到好处的心情解救,多么美妙的片断生活。月光的指向也如其发散的光芒一样,几乎照临了所有的角度、所有的地方。在这篇小说中,庆邦老师让月光反复出现,既是背景,也是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个意念,像一条线索一样把所有情节串接起来,推动着故事向前进展。
比如在某个晚上,吃过晚饭之后,队里的基干民兵们集合在队部门前学唱革命歌曲。他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男民兵风华正茂,女民兵英姿飒爽。月亮从东边升起来,很快跃过屋脊,挂上了树梢。“月亮一出来就很大,很圆,很亮,恐怕比最大的镜子都大。他们面朝东,正好对着月亮。他们想对着月亮把自己的身影照一照,没照到身影,月光把他们的脸变成一张张小月亮。”这是多么美好而美妙的情景啊!但这里面也有不美好的,人学唱歌须有资格,除了年轻,更主要的是,家庭成分要好,政治上可靠。夜晚是那样宁静,空气是那样透明,对歌声的传播效果很好。金种银种不能参加唱歌,所有地富反坏右家的子女都不能参加唱歌。这时候的黄金种也在月光下,正在地里削红薯片子,在一块长木板上嵌上锋利的刀片,刀片往上张开一点儿,在木板上推动红薯滑行到刀口里,一片片薄薄的红薯片子就削出来了。他的技术的确很高。一块碓头样的红薯,到了他手下,嚓嚓嚓就没有了,纷纷变成了薄片。由于他削的速度快,刀口下面的红薯片子不是落下来的,是蹿出来的,飞出来的。红薯片子恰像展开的翅膀的一翼,驾着空气,噌噌噌飞出好远。削好的红薯片子被弟弟银种运送到地里摊开晾晒,“月光是白的,红薯片子也是白的,月光和红薯片子交相映辉,那块地里白花花的。金种偶尔往那边的地里望一眼,几乎产生了错觉,差点儿以为月光是阳光,阳光照到那块地里,那块地里就亮;云彩遮住了这块地,这块地就暗。”是月光,让他在最难挨的时候心里能够发散、想象,把一段时间打发了。
比如又一个晚上,另外一个村子放电影。在那个年代,文化生活几乎没有,能看上一场电影当然是一件好事。不仅如此,电影一般都是在晚上放,光亮已经弱了,人们的活动在模糊的情形下进行,隐藏在人性里面的东西可以放出来活动一下。于是,电影场内外就发生了很多异常的故事。小说中,月亮果然升起来了,照出了麦秸垛的轮廓。人们在来来回回,那一对男女偷偷的情事正好与月光错过,仿佛真的被隐藏了起来。
月光似乎在为每一个有情的人创造机会。金种看上了王全灵后,他想尽快出手,把王全灵追到。在这个晚上,他把自己收拾了一下,就出门去找王全灵。这时候,月亮还没出来,星星很稠密。一帮男孩子在队部门前的空地上玩打仗。他在暗地里等待。月亮也是一个悬念,在故事中高高悬挂,和我们一起等待着一个答案。
月光给出了金种的希望。金种把卡子送给王全灵之后,他仰脸往天上看了看,月亮适时出现。这是一个戏场,“天上有大半块月亮,还有一些稀疏的星光。在月光和星空下面,才是灯,才是歌舞,才是乐器的演奏,才是人间的戏台。在戏台下面的暗影里,才是男女老少。”人间多少事,尽在月光下。
月光把小说中众多情节都关照到了,月光始终与黄金种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王全灵拒绝了他,他绝望了。在这个后半夜,月亮落下去了,黄金种开始了他第一次逃离。黄金种很快被送了回来后,他因和叔叔打架,他出门后叔叔从里面顶上门不让他进屋。这也是在晚上,他不由得抬头,他看到月亮很细,天很黑,他不知往哪里走。在很细的月亮下,他突然意识到,家有门他却进不得,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在第二次出逃被抓回来后的当夜,黄金种借着桌角磨断捆他的绳子,扁着头,扁着肚子,从窗户上面的空当里爬出来,又跑了。“是夜,月亮正圆,遍地都是月光,如雪。”黄金种的出走都是从夜晚开始的,他小心翼翼,他心里装满了委屈却不敢流出一滴眼泪,他听信了传说,鬼们的同情心都很强,也喜爱管闲事,他们若看见谁在夜间哭泣、流泪,就会显出很关心的样子,纷纷围过去进行安慰。行文至此,我们的认识也被强调,鬼尚有同情、善良之举,那个时候根正苗红出身良好且处在正常位置人却没有,不能不让人心寒身冷。
尽管月光并不能如阳光一样清晰地照彻,但我们仍然能看到事物部分面貌,进而感觉到事物的本质方面。长篇小说不在于篇幅的长短,而是对人物命运的揭示,是对普遍的社会规律的揭示,是对所有人的人生的本质揭示。月光之下,的确有因不能看清而误解的部分,像小说中王全灵谈到黄金种时说:“成分不好不就是毛病嘛,成分不好就是最大的毛病。有一俊遮百丑的,也有一丑遮百俊的。成分好了,啥丑都不算丑,成分不好,再俊也是白搭。”这显然是对社会的误读。但我们还是睁着双眼,借助一片月光,看着他们的来龙去脉。即使这是一个悲剧,我们看到了扭曲,看到反人性的令人恐惧的一幕又一幕,它们使我们警醒。在黄金种带孙秀文回到村子时,原来的会计杜建国下结论说:“人光靠成分好不行,成分好只管一小段儿,过了这一段儿,就不灵了。归根结底,人还得聪明,有志气,有才能。有了才能,人才能吃得开。一时吃不开,总有一天会吃开。”这是普遍的价值,是存在的根本规律。
月光悲悯,月亮在关怀,所以天也不应绝人之路。小说在结尾让寡妇孙秀文对黄金种说:“我知道你的心了,回去咱们一块儿过。过两年咱们再回来。咱们带着孩子回来,啊!”这算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了吧。我觉得这是普遍的价值最终起了作用,不管人之初是善是恶,但人最终都是要向善,向协调方向发展,否则社会就无法运行。这应该成为所有人的信仰。像这个夜晚,我们处在暗处,甚至我们自身都是一块暗,但月亮在头上高悬,它用普遍的光芒将我们一一照亮。我们要仰望它,像信仰一样,让我们的内心亮堂、坚强起来。
江 耶:本名蒋华刚,安徽定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协理事。曾在《诗刊》《中国作家》《星星》《诗选刊》《清明》《作品》《阳光》《广西文学》等报刊以及文学民刊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曾获安徽省文学奖、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阳光文学奖、《诗刊》年度提名奖等多种奖项,有作品入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天在远方弯下腰来》(作家出版社)、诗集《大地苍茫》(青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