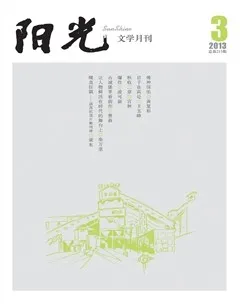爆炸
2013-12-29凌可新
张树生想不起来了,老婆到底是什么时候话突然多起来的。以前老婆很少说话,平常日子,除了上班,就是回家,管孩子,洗衣做饭,然后看电视,吃零食。到了睡觉的时间就睡觉。老公搂着,睡;老公不搂着,也睡。回头想想,张树生没觉得老婆给他带过什么麻烦,也就年轻时候跟婆婆怄过几回气,不愿意他多寄钱给父母。但他把眼睛一瞪之后,也就愿意了。
后来到了年龄,就内退下来,成了典型的家庭主妇。那年老婆其实才四十五岁。但当地有关部门就是这样规定的,国有企业女工,一律四十五岁内退,一刀切。工资待遇比上班少一百左右,十年后,五十五岁再办理正式退休手续。
老婆是前年内退的。那时她也还是像过去那样,不愿意说话,张树生下班回来,有时候闲着没事,怕老婆内退了,一时心里有想法,郁闷,想跟她交流交流,沟通沟通,劝慰劝慰。老婆也不愿意搭理他,嘴里只嗯嗯啊啊,纯粹像是应付差事。过后张树生也就不放在心里了。再说他在部门担任中层干部,忙,事儿多,有时候还要被上面的领导挖苦或者直接指着鼻子骂,心情也不是天天都好。就放任了,得过且过了。
张树生与老婆生有一女,大学毕业刚考上研不久,在北京。张树生高兴,说女儿争气,到底进京了。当年张树生也上过大学,只不过是本地区的大专。后来有几次,明明可以提拔他了,但总是被学历给卡住了。有些跟他状况相同的,则偷偷买回来张假文凭,大本、研究生的随意,竟也顺利提拔。但张树生胆子小,不敢。所以直到现在,他档案里的学历还是大专。这个成了他升迁的绊脚石,搬不掉了。女儿考了北京的研,算是对他的回报吧!
去年老婆的话还是少,今年开始,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张树生想了想,是没有。年假女儿回来,老婆也只跟女儿嘀嘀咕咕,说些他听不清楚也听不懂的话。跟他,就少得可怜了。其实张树生也不是个爱说话的人。说多了容易词不达意。当然似乎也只有被人灌醉了后,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一个中层干部,权力微小,公家的酒桌能上的机会并不多。张树生给人的印象还不错。有一回市长来调研,也对他表示过好感,说这个同志工作态度蛮端正,而且有理想有觉悟。张树生兴奋了好一阵子,以为市长想要提拔自己了,但后来什么后续的动作也没有。他一想,定是那天市长喝酒喝得高兴,或者碰到个称心女孩,随口一说而已。也就无所谓了。
应该是女儿开学回北京之后,老婆的话突然多起来的吧?老婆四十七岁了,因为天天在一起,她的容貌在他眼里还没有什么变化。但肯定也变得有些老了。有个歌唱的就是慢慢变老。张树生刮胡子时,照到过自己的脸,发现自己似乎要比老婆年轻,再一想可不是嘛,老婆二十三那年他二十一。他们认识了。然后过了一年,他们结婚了。老婆二十四,他二十二。他二十三岁那年有了女儿,女儿去年二十一考了研,那他张树生今年应该是四十五岁了。因为很少参加公家的宴会,肚子里的油水不多,身材保持得还紧凑,脸皮也光滑。单位二十来岁的女孩,有的干脆就叫他张哥。而她们见到他老婆,则纷纷叫阿姨。
记得有一回张树生和老婆出去逛街,正好碰到几个单位的女孩,这些没长脑子的叫过这边的张哥,转脸就去叫那边的阿姨。等女孩们离开,张树生听见老婆哼了一声又一声,去看老婆的脸,竟然像是刚刚被歹人谋害过一样,血色全无。问老婆怎么了这是,老婆说,你们单位怎么尽招回些鸡呀?你们局长是老鸨吗?张树生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她们是怎么得罪了老婆。还是老婆自己说,你是哥我是阿姨,她妈的逼是咋个排的辈儿?
张树生恍然,到单位告诫那些女孩,日后万万不可再叫他哥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春节前,应该跟老婆爱说话了没什么关系吧?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老婆突然爱说话了呢?要么也不是突然的,是慢慢的,是渐变?
张树生想不起来了。他之所以想,是因为老婆爱说话也没事,说正常的正经的都行。他张树生也愿意听,甚至愿意参与。因为人上了年纪,是需要语言方面的交流,年轻时节话可以不说,一个眼神递过去就成了,然后是肉体语言和肢体语言,是肉和肉的拼搏。人上了年纪,肉体的拼搏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剩下的是大片大片的空间。夜长梦多。如果有美好的语言的交流,把这片空间填补起来,生活应该还是相当美好的。
但老婆说的不是这些个。不是。老婆说的,更多更多的是他张树生没有想到过的,不愿意听的,甚至是非常反感的话。这些话成了爱说话的老婆的语言的最主流。张树生曾经请教过专家,专家说这是语言暴力。如此,则就应该是张树生的老婆在向他施展语言的暴力了。
张树生的老婆姓夏,叫夏春花。这个名字不错。仿佛很有几分诗意在里面荡漾。张树生一看见就喜欢上了。尽管等结了婚冷静下来,再作分析的时候,发现老婆的名字的用字其实是非常矛盾的。既然姓了夏了,再叫春花,可以的吗?春花春天生,夏天的时候还有春花吗?不过考虑到夏春花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岳父大人是山乡农民,认识的字总共也不过上百,水平不高,春花自己也只初中毕业,也就不计较了,谅解了。觉得名字就是个记号嘛,叫什么都可以的。
张树生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本想考个大本,但发挥不好,只能上大专。当年农村的孩子能考上个大专也很好的。所以他风光了几年,毕业了分配去县城,也都是叫他大学生。在大学,曾有个同学喜欢他,但因为毕业后需要分回各自的县城,没法协调。再加上他有点儿嫌对方脸上的雀斑过多,还有粉刺也不少,就淡下来。毕业了也不联系了。
第二年夏天,有个女孩来他单位办事,表情很腼腆,见了他不敢抬头。一抬头脸蛋是红红的,眉眼也是顺顺的。当时张树生心里哗啦了一声,像是被这脸蛋给融化了。他追问对方姓名,对方不说,只忸怩着把一条粗大的辫子扯在手里反复揉搓。他吓唬她说,你要是不说,我就不给你办事。结果他当天傍晚就跑到她上班的工厂,说是要请她吃饭。而她竟然什么也没问,就默默地跟着去了。
从认识到现在,有二十四五年了吧?老婆一直都是沉默寡言的,在她那里,似乎语言比金钱还重要。甚至两个做爱时,她都不肯使用语言,只紧紧咬着枕巾,最多啊啊几声了事。反过来,女儿是非常喜欢说话的。女儿是他俩手心里的宝。他们共同把女儿抚养长大成材。现在也应该放松放松,多想想自己的生活了。张树生都想过了,以后多争取些时间来陪陪老婆。
可是有一天,张树生下班回家,却发现老婆没做饭,而是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看见他进门,老婆反倒把汹汹的气势卸了下来,只那么空白着表情说,你越来越年轻了。
这是句没头没脑的话。张树生很奇怪,人人都是越来越老,自己怎么会越来越年轻了?难道自己是倒着活的?他看着老婆。一个人,脸上不管有什么表情,总归是有表情。若是什么表情也没有,就相当怪诞了。表情可以空白出来吗?如果不可以,老婆现在是什么表情?张树生说,你怎么了这是?
老婆说,春天越来越远了。她的眼光落在他的脸上,但浮浅得厉害,转瞬即逝。张树生说,你想要表达什么?老婆说,人生是不是越来越美好?张树生说,是啊是啊,党的政策那么好,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呢。老婆突然笑起来,说,张树生,你是不是决定要跟我离婚了啊?
这应该才是老婆想要说出来的一句话吧?前面的一切只不过是铺垫吧?但那些铺垫铺垫得有道理吗?合理吗?张树生学过哲学和主义,他回头想想,再咀嚼咀嚼,似乎也不无关联。但现在不是考虑哲学的问题,主义也且丢一边去,而是老婆提出了问题,她说他张树生决定要跟她夏春花离婚了。注意几点,一是决定,二是离婚,三是他张树生。
张树生有几分蒙。眼神也有点儿散乱。他几次都想看清楚夏春花的脸部表情,但几次都对不准焦距。他只好收回目光,让它们散落到地上,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有什么证据吗?如今是证据时代,没有证据的事情,少扯淡。说完这些话,张树生才有了底气,再看老婆时,焦距自然就准确了。
这回老婆似乎是蒙了。她肯定没想到张树生张嘴就跟她要证据。证据她有吗?证据是什么?包括哪些?她知道吗?她问张树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张树生说,证据啊。有证据再说话。好不好?没证据的话,收拾饭吧。我有点儿饿了。老婆的目光落到地上,小声说,我还没做呢。她跟张树生说,今天上午有个声音老在我耳边跟我说,你老公要跟你离婚了,你老公要跟你离婚了……说了不止一百遍。这算不算证据?张树生笑起来,你得把那个人揪过来,让他再跟我说,跟我们说。我还得落实了他的身份……老婆四处张望,我……我没见到过他啊?张树生说,那你不知道他是谁吗?老婆目光散开来,我不知道……
张树生突然恼怒起来,说,你就因为耳朵坏了,幻听了,就说我要离婚,就不做饭了?有你这样的人吗?
看见张树生恼怒,老婆也理直气壮起来,哪个耳朵坏了?你说!明明我是听到了嘛。清清楚楚跟我说的,一本正经。这能差了?再说,就算是没听到,你越来越年轻了,你天天刮胡子,天天照镜子,天天看自己的脸,是不是越看越觉得我配不过你啊?我是比你老两岁。可当初你咋就不嫌?现在看我老了,脸上起皱纹了,有沟坎了,不会浪了,被人叫成阿姨了,你这个哥哥就不稀罕我了是不是?你说张树生你说是不是?
老婆说的话一气呵成,如同长江之水,浩浩荡荡,连篇累牍,哗哗啦啦。毫无拖泥带水,连张树生都忍不住怔了怔。这是他第一次听见老婆夏春花一口气说出来如此多句的话来,而且流畅,而且具有杀伤力。仿佛这个女人突然脱胎换骨了,或者是魔鬼附体了。他定定地看她。是,他是有些不认得她了,她不是原来的那个夏春花了。不是外表不是,而是内里。内里知道吗?就是相同的一条麻袋,原先装了一麻袋麦子,如今则装了一麻袋玉米。
虽然都是粮食,但玉米不是麦子,麦子同样也不是玉米。
张树生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他把手里拎的皮包丢一边去,大口喘气。他有些窒息。甚至都动手抓扯衣服的领子了。老婆没有移动自己,只把角度转变了一下,这样,她还是直接面对着张树生,而且因为她站着,占尽了高度的优势。她冷笑一声,说,张树生,你哑巴了吧?没话可说了吧?傻瓜了吧?没想到让我揭了老底了吧?哈哈……她笑了两声,脸色突然变得恶毒,她说,告诉你张树生,想离婚,做梦吧你!门儿都没有!
然后她就到另外一张沙发上坐下来,周身都无比轻松的样子。
张树生缓了一会儿,到底是做中层领导的,手下也有一些个人员天天管理着,不会被自己的老婆这么容易就干倒了。否则他在单位也早就倒了。所以慢慢他就从容了,说,到底你还是听了一个声音说的。这个我知道,这在疾病学上叫幻听,属于精神病的一种。你应该去看门诊。他认真地说,你病了。
老婆一向害怕人说她病了。谁说她都生谁的气。张树生一说,她的脸色紧张起来,我没病。你才病了呢。她说,你不病,你咋么想起了要跟我离婚?好好的日子不过,离婚?哼哼。你是不是想先把我弄病了,再跟我离?最好说我得了神经病(其实指的是精神病),叫医生弄绳子捆绑了我去,像乡下捆猪一样,关起来,你在家里跟相好的,哥哥妹妹的,花天酒地?
现在是中午,因为下午还要继续上班,张树生不能跟老婆纠缠下去,就起身,把皮包抓回手里,你省省心吧。这么闹有意思吗?他说,我得走了。随便出去吃儿点东西。你也不能饿着肚子。好不好?出了门,发现老婆并没有跟出来纠缠,就松了一口气,想,老婆这是怎么了?要不是带她去看大夫?
下午没事,张树生上网查了一下,可能与更年期有关。他回想了好久,也没发现老婆到更年期了。因为她的月例还照例,也正常。老婆这方面不避讳他。如果是更年期就不一样了。不是更年期综合症,那会是什么?是不是有些人闲着没事,跟老婆嚼舌头,故意挑拨离间他们?老婆现在没事可做,闲极无聊,有可能就听从了呢。反正也没事不是?她说的那些话,光靠她自己想,她想得出来?幕后有人。张树生断定幕后有人。
可这人是谁,真正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一时还未知。张树生决定想法找出这个幕后主使者,把她(他)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让其原形毕露。
晚上下班回家,张树生在门外站了几分钟,屋里似乎一切都正常,开门,老婆在厨房做饭。他丢了皮包过去看,老婆冲他一笑。笑得也正常。张树生刚想松一口气,老婆说,没去会你相好的,直接就来家了?是不是回来看看我饿没饿死啊?
张树生给噎着了,他扶着门,对老婆说,我要有相好的,出门就让车撞死了。好不好?老婆干脆说,不好。要撞也得撞死你相好的。张树生说,好好好,有的话,就把我们一起撞死。这下你满意了吧?
老婆把手里的饭铲子嘭地一丢,跳将起来,伸手指着张树生的鼻子说,好哇张树生,你好狠毒啊!你比毒蛇还狠毒啊你!张树生盯着近在眼前的老婆的手指,委屈地说,我怎么狠毒了?我都咒我叫车撞了,你还不愿意啊?老婆说,你咒你咋么啦?了不起了?咒自己都咒这么狠毒,更加说明了你的狠毒!张树生暗暗吐了口气,想,看来老婆还是对他好的。不愿意他让车给撞了。
但转眼老婆就说,你自己叫车撞了倒罢了,你跑那边孤独去,一个人做了鬼,流浪去。吃不上饭,衣服破了没人补,你就后悔了。可你呢,狠毒啊,自己过去,还要带着相好的过去。你们都过去了,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马上在那边结婚?发请帖?举办豪华的婚礼?然后生儿育女?是不是?
张树生本来已经松懈下来了,已经转身往客厅去,要坐下来看电视了。他都在追问自己,是不是黑夜里冷落了老婆,才使她这样的,他都已经决心今天晚上好好地用力地奋力地给老婆以快乐了。这才眨了半下眼,老婆竟又放炮一样地造了上来。他一时说不过她,只好退缩,你不要蛮横好不好?明明我根本就没有相好的,更没有跟你离婚的打算,你这不是坑人吗?
他严肃起来,别的也用不着多说了,拿证据。他把手伸出去,人不要说话,让证据说话。如今是证据时代。哪个是我相好的,你拖拉了她过来,哪个要跟你离婚,你把他写好的离婚申请书拿过来。告诉你夏春花,我张树生工作这么多年,比你难缠的人见识多了。你难缠不是吗?证据啊?拿不出来就是诬陷,是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而且,法院也不管你诬陷诽谤的是不是一家人,只要有证据,一样判你的罪。
老婆的气焰就这么消失了。她一定是没有证据的。张树生也不怕她有证据。本来,明明他什么也没有。相好的没有(这让他心里多少有点儿悲哀和悲凉。一个堂堂的男人,难道真的可以没有哪怕一个相好的吗),跟老婆离婚的念头也没有。再说了,就算是有过,那也只是念头而已。念头不会成为证据吧?所以说,张树生不害怕,丝毫也不害怕。只要老婆还讲道理,怕什么?
害怕的应该是老婆,是夏春花女士。
果然是这样的。晚饭之前夏春花再也没说过多余的话,而且晚饭做得比往日丰盛,而且有肉有鱼,还有一瓶喝了一半的干红。看这架势,老婆是要缴械投降了,是要给他赔礼道歉了。张树生觉得自己的水平还行啊,对付一个人还是很有把握的啊。看看,连气势汹汹的老婆都软了,酒倒上了,鱼和肉端上了,笑脸……噢,就差一张笑脸了。这样的水平,就是再上一个台阶也是没问题的。不说连神仙都是人做的嘛。
老婆把一张脸送上来,说,你牛,要证据。要得我没辙了。我且敬你一杯酒,就当我今天犯了邪了,叫恶鬼附身了。喝了这酒,就是你没相好。张树生很干脆,没有就是没有。怕个甚,喝。就喝了。老婆赶紧又倒了一杯,还是那么说。张树生酒量浅。到底头脑昏沉起来,再看老婆,是一张迷人的笑脸,而且年轻了不止十岁。他就叫了声亲亲。后来就睡了,睡死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张树生看见老婆坐在床边冲他冷笑。本来天气好,暖洋洋的春天,但老婆一笑,张树生浑身都发冷。他忍不住哆嗦了一下,说,你怎么了你?老婆继续冷笑,张树生,你不是跟老娘要证据吗?老娘有了。她摇晃着手里的一支笔式样的东西,这就是证据。现在看你还咋么往下赖,咋么往下编!哼哼哈哈落老娘手里,老娘这回叫你死得很难看。
老婆夏春花的证据是这样的,事先,她到一家电器商店购买了一支录音笔,让店老板手把手教她如何使用,然后回家,想法把张树生灌醉了酒,然后往外套话。都说酒后吐真言,不怕他不上套。结果真如所愿,张树生招了。断断续续地把心灵向夏春花敞开了。
老婆异常得意,把录音播放给张树生听。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老婆:醒醒,你喝多了。
张树生:我没醉。我是谁,还能喝醉了?你没看见我们局长,就是于大脑袋,鸡巴样,一喝酒就往桌子底下钻。也不知他是怎么当上局长的。
老婆说:你好年轻好英俊哎。你这样年轻英俊的男人,咋么甘心守着你那丑老婆?要是换了我,恶心都恶心死了也。
张树生(拉住老婆的手):妹妹哎,哥哥我苦啊。我那熊鸡巴老婆,对我不好啊,折磨我啊,坑爹啊她……(呜咽)你以为我甘心吗?我早就想把她像甩一泡鼻涕那样甩了啊兄弟……
老婆:你决定跟她离婚了吗?
张树生:离。不离是王八蛋。
老婆:那你写了离婚申请书了吗?
张树生:写那个,你出去放个屁工夫,我就写出来了。我是谁,当年差一点儿就成了作家……
老婆:那你相好的是哪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张树生:相好的……嘻嘻,我相好的……她是……她叫……
老婆(口气突然紧张起来):她……她叫什么?你说……啊……
张树生:她叫……叫……(发出响亮的鼾声)
老婆得意地晃着手,说,坦白吧交代吧张树生。坦白了还能从宽,交代了还能考虑放你一马。要是抗拒呢,后果你知道的,从严,死了都没有葬身地场,随便找条狗拖出去啃了算了。
本来张树生是非常紧张的。但老婆播放过后,他突然轻松下来。而且,他看看墙上的月份牌,是周六,不用上班,就更加放松了,本来坐起来了,干脆又躺了回去,躺得舒展,四肢摆放成一个大字。然后他问老婆,夏春花,你不是说你认识字吗?不止初中水平吗?比大专还大专吗?那你瞅瞅,我现在摆的是个什么字?
老婆很吃惊张树生的态度。这是正常的吗?她把证据弄出来了,还让他的两只耳朵都听到了,也让他的脑袋想过了。开始他那么紧张,提心吊胆了都。可一听完咋么就放松了呢?无所谓了呢?是不是把他吓傻瓜了?听说人吓傻瓜了,表现就不正常了,该哭的时候笑,该笑的时候哭。现在,明明他张树生应该跳起来,举手投降,痛哭流涕,哀求她放掉他,他再也不敢了。可是……可是他却让她猜他摆出来的字。这正常吗?他……真的傻瓜了吗?
她就看张树生。看着不像。人傻瓜了,表情上是能看出来的。伪装得再厉害的傻瓜,也能让人看出来是傻瓜。张树生现在并不像是傻瓜啊。他那么放松,自然而然,一副游手好闲的泼皮样子。难道、难道是她的语气出了问题?回头想想他们的对话,除了离婚申请书还没写出来,除了他相好的名字没说出来,关于离婚,关于相好的,他都承认了啊。这个赖不掉了吧?
突然夏春花明白了。她从床边跳起来,指着张树生说,你死猪不怕开水烫!我识破你了。张树生懒洋洋地说,我没死。我怕烫,怕得很呢。夏春花疑惑,那你这是……张树生说,先猜字吧。这个多简单多容易啊。猜对了我就告诉你我相好的叫什么名字。夏春花狂喜,说话算数。张树生认真地说,我,张树生,党员、国家干部,大学毕业,没买过假文凭,没投过机。说话当然算数。
夏春花哈了声,马上说,大。是个大。
张树生看着老婆,慢慢笑起来,你再说一遍。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尽管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新鲜,古老,古老得都长了毛出来了。
夏春花坚持,张树生,你甭想引导我走歪门邪道,把我送进泥坑里去。这个字我闭着眼都认得。大。就是大。
张树生摇头,有的时候是个大字。但摆这个的得是个女人。现在摆字的是我,张树生,标准的男人。男人摆出来,就一定不是大了。老婆看了一回,再看一回,还是改不了口,就是个大。张树生哈哈大笑,把手指向自己的裆间,说,这里是不是有一点儿?一个点儿?男人有一个点儿,女人没有。明白了吗?
老婆的脸红了一下,张树生你流氓。张树生说,两口子之间,没这个词儿。再流氓也正常。老婆说,那你坑人。张树生笑,你连爹都坑了,我坑人怎么了?况且我也没坑,男人,那个地方都有个东西长着。而我的这个点呢,非常显眼是不是?你怎么就视而不见呢?
老婆颓然跌到床边的一把椅子里面。但她看见了手里的录音笔,眼睛又亮起来,老娘输了一回,大不了不问你相好的名字了。可这证据还握在手里呢。不信治不了你。
张树生说,醒醒吧老婆,你那叫什么证据?你拿出来,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把我灌醉了酒,然后一句一句套我的话。人在不清醒的时候说的话,是不可能成为证据的。你没事时可以找个律师问问。噢对了,你妹夫的弟弟就是律师不是?你问问他,看看是不是?
老婆沮丧着,很久不吱声。但当张树生起来,站到地上后,她还是坚强无比地说,不算就不算,可你心里就是时时刻刻想着要跟我离婚。
老婆夏春花及时调整了策略。她不再提证据的事了。因为她真的坚信张树生的内心深处是一定想要跟她离婚的。理由是,换了她是张树生,她也会有这种念头。而一有了这种念头,就会出去发展相好的了。现在到处都在说,当官的个个有相好,大官有一批,十几个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中官也有一批,几个到十几个。再小一点儿的官呢,比如他张树生这般大小的呢?起码也得有一个两个的吧?否则当官有什么意思呢?
看他张树生天天去上班,得意得很,也幸福得很。脸色那么好,情绪那么高,说没相好的在外边养着,别说她不信,连外人都不信。大伙儿都不信的事情,凭什么叫她一个人信?
这是老婆夏春花的心理吧?有时候张树生猜测,有时候揣摩。将心比心,他相信老婆是这么个心理。那么,满足了她?亦即,出去找个相好的?这才是让张树生为难的事情哩。
平心说,他张树生要是想找个相好的,不是不可能。比他官职低的,比他长相差的,都有相好的了。他会没人要?况且,这二十来年里,冲他抛媚眼的也不止三个五个,有的甚至都直白地跟他那么说,更甚至把手都放到他身上了。可是张树生胆子小,生来就胆子小,他尤其害怕对方是在设陷阱,要把他陷进去。或者毁了他的前程,或者牵住了他的牛鼻子,或者搅乱了他的家庭。这些都是他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掉的。所以都到四十五岁了,都中层了,他还是个除了老婆的身子,再也没沾过女性的男人。在如今的社会上,张树生应该算是恐龙级别的男人吧?要么是骨灰级别的?
所以面对老婆夏春花一波一波的攻势,张树生很是委屈,眼泪时时刻刻都准备跌出眼眶。真的哎,换了别人,她不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一心一意的老公,如今有吗?根本就没有的。他都不计较两个人身份地位的差别了,她还想要干什么?难道把他定位成一个想要离婚的男人,她夏春花脸上光彩吗?
张树生还是无法把握老婆的心理。照理说,他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几年,彼此都很了解了。以前他也以为自己了解夏春花,以为像了解自己的身体一样了解她。但现在看来不是的。他不了解她。至少不完全了解她。
归咎于更年期的临近?张树生不知道。但他苦恼是真的。老婆是不再纠结于证据了。他跟她要,她顾左右而言他,其实岂止是言他,简直……简直她是在赤裸裸恫吓他。她改变后的策略就是这个。张树生回家,吃饭,饭做得好好的,该放盐放盐,该放味精放味精,鱼也有肉也有。想喝口酒,随便。反正酒瓶子在桌子上,酒杯也在。吃饭的时候老婆脸上也没别的,正常。吃完饭,把残汤剩饭撤下,把碗筷洗了,桌面抹干净了,妥当了。老婆就笑眯眯地凑过来,坐到张树生对面。她离他很近,脸对着脸,眼睛对着眼睛。然后老婆说话了。因为事先喝了水,老婆的嗓子也很光润很流畅。
老婆说,离婚是每一个成功男人向往的事情。不成功的男人同样也向往,喜新厌旧,有了新人忘了旧人。把新人当宝贝,把旧人当抹布。把相好的当蛋糕,把老婆当狗屎。是吧张树生张科长?
张树生看着老婆。
老婆说,不要以为我没有证据,你外面就没有相好的。不要以为你外面没有相好的,你心里就不想着跟我离婚。你想,做梦都想。当年你说你就喜欢我的红脸蛋,就喜欢我的大辫子,这话不说了。你成功了,当科长了,往下还要当局长吧?局长当了还要当县长吧?老婆得换换了吧?是不是张局长?再不换就来不及了吧?是不是张县长?
张树生把眼睛闭上,不看她了。老婆表情轻松着,说,这么跟你说吧。离婚,我能离。离了你,我能饿死不能?不能。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搂着个小妖精快活。你不是天天得上班吗?好,你上你的班,我呢,内退了,没事做了,清闲了,正好。我在家把刀法练习好了,把手腕练习硬了,再多买几把钢刀,长的、短的,尖的、扁的。反正是买,买了干什么?跟你说了也没关系。等你上班走了,我就敲门,小妖精一开门,我就进去,把她用绳子一捆,哈哈,老娘就有事做了。老娘心硬得很呢。手腕也硬,刀子就更不用说了。捆了你心肝小妖精,把她身上的衣服统统剥了,精光精光往桌子上一放,刀子一排。你不是稀罕小妖精的樱桃小嘴吗?好说,老娘就把它割下来。你不是爱看小妖精的眼睛吗?老娘就用尖刀一剜,哈哈血淋淋放一边。鼻子也从根儿上一刀,两只耳朵上不是戴着你给买的金耳环吗?老娘一刀一个一刀一个……小妖精的脸抹平了,再往下走,下面是什么,哈哈奶子。小妖精鼓鼓的奶子不是叫你发狂吗,用宽刀一切一个一切一个……再往下面呢?是……嘿嘿,老娘刀子钝一把再换一把,放心,老娘会让你那小妖精死得爽快点儿。然后老娘把她的肉煮一锅,香喷喷留给你回来下酒……
张树生眼睛睁大了。老婆夏春花语言的流畅和里面闪烁的文学色彩让他无比惊讶。那血腥气和杀气,更让他胆战心惊。他感到自己在老婆的讲述中不停地哆嗦。但老婆滔滔不绝的样子,似乎是很得意,很享受。他说,天哪……天哪……你……你怎么可能……
老婆哧地一笑,老娘说到就做得到。只要你能离婚,只要你能娶回个小妖精来。她满面笑容地说,咋么样张树生?娶个小妖精回来试试?这会儿我也就说说而已。等到了那一天,再叫你瞧老娘我的手段。
张树生头疼。老婆一席话会让他头疼半天。黑夜里一闭上眼睛,眼前竟就真有个血淋淋的小妖精横陈着。瞅瞅是单位的某个女孩,再瞅,又陌生。惨,惨不忍睹。张树生不敢闭眼,连灯都不敢关上。老婆倒自在,说够了,往床上一躺,鼾声瞬间如雷。张树生只好到沙发上卧着。可在那里,灯一关,照样是血淋淋的场面等着他。
夜里休息不好,白天就容易出错。出了错老婆承担不了,倒霉的还是他张树生。老婆这种策略展开后,他都让局长骂过三回了。其中一回局长都骂到了他的娘。这是奇耻大辱啊!但原因细纠起来,还是在老婆夏春花身上。
娘挨了骂那天回家,张树生冲老婆举手,说,我投降了。好不好?日后你想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再吓唬我了。老婆冷笑说,行啊。投降了得表示表示吧?张树生问她怎么个表示法,老婆说,容易,告诉我你相好的叫什么就行了。张树生傻瓜了,喃喃说,这不是无中生有嘛。我上哪儿找这么个人出来啊?老婆说,你心里就有。张树生扪心自问一通,摇头,真没有啊。
老婆说,没有不是吗?你听我说。
她说,我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算盘。你怕我害你那小妖精,一定是仔细嘱咐她了,看见我要躲远一点儿,我叫门万万不能给开,要时时刻刻防备我。是不是?你也不用说不是。我这回就先放过小妖精。你娶个小妖精,不是还要生个儿子吗?好啊,我冲你儿子去。这个想防也防不了吧?你们的儿子哼哼……他得长吧?三岁得上幼儿园吧?在家里动不了手,我可以到幼儿园啊?到了那里,瞅准了哪个是狗日的张树生的儿子,一把抄过来,从怀里掏出尖刀一把,哈哈,你猜结果是咋么个样?我这手艺早就练成了,杀人不过一刀。
老婆说得从容。张树生只好再次投降,说,我都交代了吧。我是有个相好的,叫……他说出来一个名字。但马上就被老婆识破了。因为这个名字太假,竟然会跟一个老婆经常在电视里看见的女孩重名。不过张树生一口咬定就是她,老婆一时也没了主意。
没了主意就不说了。几天无事。但张树生有事了。工作失误,局长很恼火,叫他且把手里的工作交给别人打理,自己回家缓几天。局长说,工资就不扣你了。好好平静平静,找找原因,把问题解决了,轻装上阵,回来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
其实原因还用得着找吗?明摆着在那里。老婆夏春花如果不极度骚扰他,他能这样吗?这回来休整,不用上班,天天面对老婆,张树生就想用个办法把她的气焰完全消灭掉了。只是怎么想也没办法。有一天突然想到,要想在精神上消灭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他忘记了是哪个伟大的人物说的,但这一定是名言了。是名言就是真理,就是哲学。因而他一时很振奋。决定遵从伟人的话来做。
张树生买回来一些毒药,又买回来几把尖刀,还有一根绳子。他把这些摆放在眼前,掂量着用什么更合手。首先毒药方便,下进饭菜里即可。但万一自己不小心也吃了呢?那就两败俱伤了。还是用刀子吧。老婆都已经把过程告诉他了,先捆了对方的手脚,往桌子上一放,再操起刀子,想怎么动手就怎么动手。要眼是眼要耳朵是耳朵。唯一不足处是,动刀子要流血的。而血又很不容易处理干净。所以张树生在这一点上犹豫起来。
但很快他就不犹豫了。时间紧迫,容不得他再犹豫。因为老婆那边已经霍霍磨刀了。老婆夏春花要杀的可是他最最亲爱的爱人和最最宝贵的儿子啊。万一那边抢先动手了,他张树生就彻底完蛋了。
他可不能完。
于是张树生决定趁着茫茫夜色,马上动手。
起码他得让狗日的夏春花闭嘴!
凌可新:1963年10月出生于山东蓬莱。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毕业。中国作协会员。已发表文学作品约500万字,有几十部中短篇小说被《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并收入各种文选。已出版长篇小说《梦的门》,中短篇小说集《老白的枪》《醉纸》《避邪》《最初的地方》等四部。短篇小说《老白的枪》入围首届鲁迅文学奖,并入选“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排行榜”。短篇小说《雪境》获山东省作家协会首届“齐鲁文学奖”。短篇小说《星期天的鱼》入选《小说选刊》杂志社《2011中国小说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