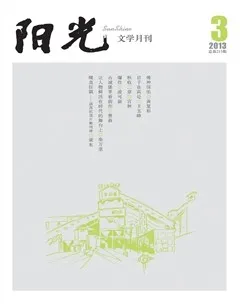秋收二章
2013-12-29宫林
柴火垛
谁还在乎柴火?
除了电饭锅,村里不少人家还用上了液化气。关二娘却不稀罕这现代化。她怕电,不识字的人怕给电老虎吃了。那年管电的文华在杆上被电击,俩脚心朝外喷火,远远能闻见焦糊的肉味,吓坏了她,叫她六十八岁得了心脏病,一发作喘不上来气,不是文华的脚心喷火,而是她的喉咙短了路。
液化气?见不得那装气的罐罐,大的小的,模样一样,活脱脱童年记忆中飞机撂下的炸弹啊!前年刘新才盖楼挖地基,还挖出来一对儿,远没有气罐大,可她咋就觉得有恁大呢?那时她坐在父亲的箩筐里,仰头一看落下的“罐罐”,好奇,一声爆响,震倒了父亲,不远处还有一堆模糊的血肉,在哇哇的哭叫。炸弹可真大,响声击得耳朵吱吱叫了好几天……
她最在乎柴火。没几根黑发的人了,仄仄歪歪,没根似的,依旧大包小包往家搬。搬的可不是大豆、玉米、芝麻,而是人家丢弃的豆秸、玉米秆、芝麻秆。是柴火。
大儿子得闲时,会用机动四轮给她拉上一车,卸在门外,由她一点儿点儿移进院子里,垛成柴垛。可这秋收季节,得闲是少有的。人人累得腰酸背疼,得闲就想躺到床上眯一会儿,养养神。
大儿子说她:“这路上过车多,又摊了厚的豆秧子,不方便。你待着,得闲了我一车顶你背十天的。”
她不管,说干着活儿心不急,背着柴火心不急。不是空耍嘴皮子。她样子真是不急,一趟一趟,慢腾腾的,如同驭着壳子的蜗牛。
村中有十几个如她大小的老人,身子坏的,多已拄了拐棍,吭吭唉唉,串串门唠唠嗑还行,下不了地了。身子好的,拎了竹篮,或者夹个化肥袋子,到收过的田地里捡捡豆子。豆子两元一斤,有点儿土尘人家照收。这几天收豆人的电喇叭不再吆喊,而是唱,常香玉、马金凤、唐喜成的,一段比一段蜇耳朵。仿佛不是唱戏,而是招人过来发奖金的。
儿媳说她:“你去拾点豆子,孬好能换几包方便面吧。你揽巴这些弄啥?哪年缺过你烧的?”
“不缺,哪年都不缺。”她说,“不吃方便面不急,见柴火扔着不捡急。”
“拾豆子不比弄这省力?”
“我眼花,手懒,瞅不清,又提不稳。”
倒是柴火好拾。政府不叫烧秸秆,天天有宣传车在村道上来回驰奔。各家的秸秆一时顾不上拉回村,全都扔在地头上、河沟边,谁想要是谁的。等人家忙完果实,犁地种麦时,会用大车小车拉回村里,垛进村口的树园里。虽是一家一家的分开垛,也没几人去烧地锅了,垛上就没人管了。二娘真缺了烧,去那里背,随便哪一垛,也不会有人长短什么。但她不去那儿背。这老太太犟执得很哩。年轻时也不怪啊,怎么老了就怪了,有点儿傻啦?活脱脱受罪的命。
除去烧火原始,苦点儿,单身的她生活还算滋润。
三个孩子,大儿子不出村,与人家合伙建房,大钱挣不了,每天五六十块没跑的。大媳在乡蒜片厂拣蒜片,每天四十块。他们的孩子在部队。二儿吧,公家干部,与二媳一样,吃皇粮的。不断回来看她,高钙奶粉、茶、蜂蜜,搬回一箱又一箱。老三是闺女,嫁的邻村,男人是窑主,有钱,农闲时能一天三趟的过来瞧她,电动摩托斗里没少过礼品……这老婆儿吃不短喝不短,穿的住的,啥都不缺了。怎就见柴迷,见柴亲呢?
“我是烧的。”她说,“我喜欢烧锅。”
闺女不喜欢,儿子也不喜欢,怕烟呛。闺女很少在她这儿吃饭,就是受不了烟薰。晌午来了,卸下东西,抛下几句暖心暖肺的话,跨上车呜一声走了。
二儿子更甭提,回家来从不进灶屋。
她问:“烟味咋啦?”
他说:“不咋,就是有点儿受不了。还有点儿酸。”
烟味竟然有点儿酸,她可第一次听到,还从来没闻出过。她开他玩笑,说老二,柴火里可没有醋,没有橘子皮,它们烧着,又不会发酵发过了头,咋会酸呢?你的鼻子有问题吧。别说炊烟,我看见你闻见香烟味,也都直抽鼻。
是他安排二儿子回家让烟的。他不吸,身上总不带烟。回村来与人说话,哪曾想到让烟的事。她说,老二呀,你公家人员,把人家让你的烟一根根收拾着,回来让给老少爷们多 好。他哦了一声,拍拍头,明白了。再回村,逢人便让烟,笑吟吟的。人家皆夸他当官没架子。他落得一街的好名声,叫她这当娘的心里熨帖。
平日里,她喜欢到村口闲站。这儿有几间趴趴屋,里面住了几个没人疼呵的老人,聚在一块有斗嘴皮子的,有斗棋牌的,在快乐中迎送着日月的升落。她跟他们说说话,笑一笑,一上午一下午就过去了。即使不说笑,也觉得这儿亲切。
那些人说她不会享福,端着金碗去要饭。放着三个好去处不去,独独守着旧宅,一个人单挑着过,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怄气吗?你说大儿家不称心,闺女家盖的是楼,称心吧。他两家嫌冷清,二儿子家在城里,出门是熙熙攘攘的街道,热闹吧。这仨地方,瞎着眼伸手摸一个,也总比你一人住老宅强吧。人家是没人疼呵,是寡妇蹬男人——没夫(福)。你是不知道享福,你叫人眼热得心里痒痒哇!
她总笑,不是不会,是享不了那个福。大儿闺女家住不惯,二儿家呢,是小区,半夜里还有小车进进出出,不是车笛声,而是那别人听不到的突突声,总能叫她醒过来。醒过来,再难入睡,又不好到客厅里开电视,怕影响别人睡觉。又不识字,看不懂书。只能在床上翻烙饼子,真是受不了。难怪,今春在那儿住了半个月回来,倒是捂白了,却瘦了几斤肉。最后实在住不了,叫闺女去接她。她叫闺女捏捏脸,说都瘦松了,闺女还打趣说,拿钱难买老来瘦啊!
是闺女与二儿合计着弄她进城的。二儿单位老干部全面体检,他给闺女打电话,弄老娘随老干部一同检查检查。头上肚里脚下,凉凉热热查一遍,最大毛病是白内障。以前只觉眼力不好,叫孩子们弄些眼药点点,如今才知是白内障在作祟。医生说现在不能手术,等白内障熟了以后才能做,先养着吧。孙子笑了,说奶,等于养条鱼,养大了再逮住,再开刀。
医生不让她烧地锅,那种烟最伤眼。
二儿也说别回老家了,这儿没有烟,有一点儿,抽油烟机也吸跑了。
不中!不中!
闻不见炊烟,总是觉不出饭时来了,吃饭不香。住在高楼上,上下都坐电梯,身子发飘,像地震,踏实不下来呀。
还是烧地锅好。用手将各种秆草捋顺溜,塞进锅膛里,看着青的烟飞,红的火扬,听着噼噼剥剥的火烧声,听着锅水的沸滚声,没有盛饭,就想吃,吃起来能不香?
二儿给她副茶色眼镜,叫她烧锅时戴上,保护眼睛。答应倒好,就是一回没戴过。心想那跟拉磨驴戴上暗眼罩有啥区别?别自找陋曲,遭人笑话了。快八十的人了,乐和一天是一天,再活还能如何,人又不是乌龟。这是村口那几个老家伙的话,不好听,却有理分呀!
他们的儿女不孝,有的出外打工,好房空闲着,却不叫他们住。逢年过节,也不看望他们。但他们活得倒不失滋味,虽是得过且过,钻头不顾腚,也不失一种豁达。比起他们,自己成了天上人。人老了,儿孙们待见,比啥都强。
那个电工文华的爹也在这儿。文华被电打得脚底冒火,竟然没死,成了瘫子。他女人走了,按说村中的好房该叫老爹住,但他却没有。他摇着轮椅,每天到集上卖小件商品,路过这趴趴屋,竟然不跟老爹说一句话,更甭提给点儿礼品了。他爹不生气,每天乐哈哈的。说人与人都一样,谁都一天二十四个钟头。自然有人反驳他,你是冰块夹在腚沟里——屁化(话)。你的二十四钟头怎能跟关二娘的一个样?
“咋不一样?”他说,“如今她出来背柴火,我也背。她烧地锅,我也是。”眼睛鼓突着,与人抬扛。
还真有理分,别说他,趴趴屋里的所有主人都在背柴火,都烧着地锅。只不过,有的人这两天不背,急着去地里拾豆子捡玉米,先抓能换钱的东西。等人家犁了地,他们自然忙着去找柴火背。背的少了,冬春不够烧,便会偷偷到树园里弄,那儿柴垛多。人家不满,也只能瞪几眼,不会报送派出所。
关二娘从不到那里抓柴,人家的东西她不要,年轻时就这副骨脉,老了更不干那丢人勾当。当然,她从来未遇到过缺烧的境况。麦收时她背麦子秸,秋收时背秋粮秆,再过些时,树叶落了,她去扫树叶。反正,她院里除了个大柴垛,没什么打眼的。
老头子死后,孩子们分家的分家,出外的出外,她似乎只守着个柴垛过日子。
这柴垛是哪年坐的根,她自己也说不清。反正到了春天缩小,到了初冬又增大了。从未消失过。
正因如此,被狡猾的黄鼠狼钻了空子。它天天偷吃邻居的鸡。拉吃鸡时鸡会惨叫,狗便去追,哪能追得上,大雪封山,别的动物寻不到食,黄鼠狼却很滋润。
新任村治保主任王小山侦察兵出身,一下查出了黄鼠狼的根据地是二娘的柴火垛。鉴于多家失鸡,怀疑垛中不只藏一个。他找二娘商量,要把这窝家伙一网打尽,给村民的家禽一个安宁的生存空间。二娘当然同意。王小山说,为了确保一网打尽,在柴垛周围插上网,再一把火点了柴垛。二娘马上摇头,不中不中,俺自打见了文华脚心喷火,再也见不得火了。主任笑了,你天天烧锅,还不见火吗?她说,火跟火不同呀!这叫啥火呀?是你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吧。王小山冒了汗,惹不起这老太太,又得逮黄鼠狼,只得再想办法。
后来虽没烧垛,却用网围了,将垛挖开。一下子发现了不少的各色鸡毛。还捉到了四只黄鼠狼,两大两小。
黄鼠狼凄厉的叫声让她心悸了好一会儿,赶紧将衣襟里的速效救心丸搕出几粒,压在了舌根下。她在想,那俩大的,是对夫妇吧,俩小的定是它们的孩子了。王小山他们将它们提到毛笔厂里卖了,晚上在桥头饭馆喝了老长时间的酒。而那些柴中的鸡毛,叫瘫子推轮椅过来捡去,据说扎了不少只鸡毛掸子,系在轮椅后面在集上卖。只是那些鸡蛋壳没用处,叫她看了难受。
不知怎的,她有点儿可怜起那些黄鼠狼来。对着散落的鸡蛋壳说,你们为啥在这儿作窝,咋不到树园里去,那里的柴垛多,好隐藏啊!
王小山见她不悦,忙串和几人,将扒散的柴垛重新垛起来。又安慰她说,如果柴火不够,树园里有俺一垛,只管背去;反正俺用的是电锅,放柴垛也没用处,烧了它,总比叫黄鼠狼穴了窝作恶强吧。
关二娘大喝一声:“王小山,再提黄鼠狼,小心我拐棍。”
王小山等人灰溜溜出来,低声议论,这老婆儿咋的啦?有点儿反常。
她到村口,问那些男人,这树园里几十个柴垛,为啥没有黄鼠狼窝?它们也是,偏就躲到俺家的垛里。
瘫子爹用手指指正嗑南瓜子的聋子,还不是他的功劳?他喂了几个鹅几个扁嘴子,天天从河坑里上来,跑到柴垛那儿闲卧,觅闲食,屙得到处都是鹅屎鸭粪的。黄鼠狼喜欢鸡,却独独怕鹅,它的脚一踩到鹅屎就烂爪子。
她明白了,真是一物降一物。黄鼠狼的爪子踩不得鹅屎啊。她在乡间待了七八十年,竟然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她只晓得它的毛尾值钱,是毛笔厂的抢手货,没听过这个。她心里乐了一下,先前的郁闷淡了一下。
瘫子爹又说,亏得王小山捉了它们,不然,它们在你柴垛里整天偷鸡吃,还不修成精怪。到那时,它们昧人作祟,咱就奈何不得了。
她说,你别吓人了,毛笔厂刘壮,只要俺家老二一回来,便来家里喝酒,他说捉到黄鼠狼,拔掉一些尾巴上的毛,再放掉,来年再逮再拔。哪像王小山恁狠心,捉住就摔死了。
瘫子爹说,刘壮捉的全是小的,十年八载成不了啥气候,你柴垛里那俩大的,眼珠子都半红,快成精了。也就怪了,它们在你柴垛里,你天天拽柴烧,看不见它们,也该闻得见臊气吧?
她摇摇头,真的不晓得。连它们的半红眼都没敢看,只听到了凄叫。那一刻她可怜它们,毕竟也是活泼喇喇的生命呀!
如今想来,即便那俩大的该死,那俩小的,还不会偷鸡,毕竟是无辜的,该拔了尾毛,放掉呀。这个王小山也真够狠心的。再一想,这小子还真有点儿本事,干了半年治保主任,还真给村里办了件好事,这满街十几盏路灯,就是他到乡里争取来的,所以一直取名为“治安灯”。有了这个,小偷小摸的事果真少了。
很自然地想起当初王小山扒完柴垛留下的一句话:“大娘,到秋收时,我给你拉柴火,给你垛垛,保证还你个更大更高的柴垛。”
她在瘫子爹的轧井边放下柴包,洗了手脸,喘了几口气,说:“我得叫王小山给我拉柴垛垛去。”
扁嘴子牙
大秋忙天,太阳在原野里龇牙咧嘴,挥着热辣辣的光鞭,不但抽打着流汗的脊背,还抽打得焦芝麻炸豆,四处蹿。秃蚱子忙得边叫边蹦,机器忙得冒着黑烟乱叫。人呢,杀完芝麻去割豆,忙得蛋子像摇铃一般,在裤裆里咯啷咯啷地响。
没想到,村里竟然出来两个闲人,吵唾沫嚷嚷,一个还抱了扁嘴子。
铁柱说:“真的假不了,扁嘴子不会说话,自有行家给公道。”
说完想从二毛手里夺扁嘴子,二毛不让,扭着身子,护着。
二毛说:“你说是你的,为啥会跑到俺窝里?”
铁柱说:“老扁嘴与新扁嘴不同,人家摸摸牙就晓了。”
二毛说:“哪龟孙昧的哪龟孙知道。”
铁柱说:“先别说扎耳朵的,摸摸牙就晓了。”
高个子的铁柱也涨红了脸,掏出一根烟,没有火,干脆从二毛口中摘下半截烟,引上,将半截烟又还过去。说:“又不是没前科。”
这话二毛像没听到,对他说,你引了我的火,总该给我一支烟吧。铁柱说,等摸完扁嘴子牙再给你。二毛没听见“前科”,村口歇息的几个老人却听得一清二楚。待他俩稍稍远点儿,互相对对眼,嗯,是有前科呀!陈芝麻烂糠谷抖搂了出来。瘫子爹指指二毛瘦小的背影,说怪不得喜欢扁嘴子,有点儿仿,扁嘴子死了,嘴都是硬的。那一年挨巴饼子的事忘了吧。
有一年村西医生刘玉生女人从娘家逮回只长毛兔,刚养三天不见了。谁弄去了呢?刘玉生想起半后晌二毛来给女人打针时看到的事,叫女人去他家寻寻。女人果真寻到了。在他家院角的一个破柳条筐里卧着吃青草哩。她想抱走,二毛不认,说已经喂了半年了,一次兔毛没剪,咋会成了你们的?
赶上玉生女人也是个喜欢直插杆子拧到底的主儿。什么不说,蹬车去了娘家,问他们给的长毛兔,有没有记号,他们指着旁边正觅食的兔子,说都有记号,公的在左耳后涂了红色,母的在右耳后涂了绿色,只有指甲盖大小,外人不会注意的。这叫做“男左女右,红男绿女”,防的就是与别家的兔子掺合了不好认。
吃了定心丸的她回村,拉了男人二次造访二毛家。问二毛家的兔子可有啥记号没有。那二毛偷兔子,只是顺手牵羊。当时兔子在诊所外边的路边啃草,被他抱住了,弄回来刚喂了一会儿,哪里晓得什么记号?只得吞吞吐吐说没有。玉生女人掂起兔子耳朵,叫他看,这不是指甲大的绿印印吗?她将兔子递给玉生,挥手扇过去一个大耳饼子。又嫌不过瘾不解气,脱掉鞋子兜头盖脸打将过去。打得二毛满院躲闪,连说眼花了,搞错了。幸亏玉生心软,拉了女人回了家,才算平息。
如今他又昧了铁柱的扁嘴子,铁柱那身坯,不揍他个稀巴烂才怪呢。但人家铁柱没动手。两家毕竟是隔了坑的邻居。两家的扁嘴子共同在一个坑里游玩觅食,一起比赛呱呱的声音高低,一起比赛扎猛子捉鱼,友谊着呢。铁柱与二毛平时关系也不错,二人共同给人家盖房子,属同一个建房队。铁柱不想为一只鸭子撕破了脸,别说这,就是只北京烤鸭才值多少钱?但他女人不干,非得争这口气不行,因为她去要了两回,二毛都不认账,把住不给她。她恼了,别说是只活扁嘴,就是根鸭毛,他二毛都休想得到。
铁柱当过兵,在部队里干过炊事班长,杀过不少也煮过不少扁嘴子。他晓得今年的鸭子与去年鸭子尽管个头颜色、神情相似,但它们的牙不一样。两岁的鸭子已经基本没了牙,吃东西磨秃了。一年的鸭子会有。集市里有鸡鸭行,里面的经纪人用手一摸,便会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他说:“二毛,走吧,去鸭行里。我破半天工夫,叫芝麻豆子再炸出去几斤,我也休息休息喘口气。”
二毛说:“正合我意,真的假不了。这官司奉陪到底。”
铁柱说:“你就癞蛤蟆趴在热鏊子上,鼓着肚子撑吧。有你泄气的时候。”
在村口的桥头,碰上治保主任王小山开着电动车过来。他跟铁柱当兵时是战友,自然会问他俩为什么争吵。铁柱指指二毛怀中的鸭子,嗯嗯两声。王小山几年前酒后揍过二毛一顿,打断了二毛一根肋巴骨。二毛平时便怯他,看见他就觉得肋部发痛,总想用手揉揉。哪想到他一揉肋骨,怀中的扁嘴子一下子跳到了地上,呱呱叫着想逃走,逃到水坑里觅食吃。
王小山一哈腰,动作敏捷,右手抓到了鸭脖子,左手将扇着翅膀的鸭子提拎起来。
“你们为了这玩意儿,想给我到乡里丢人,是不是?我可刚从那里回来。刚开的会,乡里干部多分下了村,提防点烧秸秆。你们现在上访都未必找到人。瞧瞧哪个不忙,就你们闲了吧。”
他说这鸭子先归他,叫铁柱和二毛给他拉玉米秆去,晚上再解决这只鸭子的问题。他的鼻子朝二人猛地扬了两下,说你们谁不愿意去,就证明谁心虚了,这鸭子便归另一人。说完骑车回家,将鸭子关进了院子里。
俩人谁都没争议,只得回家拿了木杈,去王小山的河滩地里装玉米秆。王小山的女人正在那儿装,一个四轮车的车斗快装满了。但她不会开车。王小山这三人来了以后,她抿抿额上的汗,说嗓子燥得不行,得回家喝水去。王小山拉住她咬了咬耳朵。她朝铁柱二毛诡秘一笑,说你们好好干啊,我去给你们做宴席去。
剩下了三个男人。王小山给他们发了烟,全点上。说为了你们的财产拥有权,大忙的天,奔往乡里,证明你们还真具有了公民意识,但这事太小了点儿吧。
铁柱说:“吃能让,穿能让,理不能让。”
二毛说:“是谁的就是谁的,丁是丁,卯是卯,一捏两瓣。”
王小山便笑了。半天不再说话。铁柱与二毛干活时不住的看看他,等他说些什么呢。二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手上摆弄着哗哗作响的玉米秆,心里却忘不掉那只鸭子。
车斗装满时,王小山又给他们两支烟,点上。他吐出烟,烟雾随微微的风散去了。他叫铁柱开车,自己和二毛坐进车斗里,屁股下是光光叶叶的玉米秆。他们将玉米秆卸在了村头树园里。
活并不多,也就两车。这时的天色尚早。王小山去河里洗澡,铁柱与二毛也跟着去。三条光光的男人身子几乎一起下了水,砸起了老高的水花。水里的青蛙在叫,与地里机器的叫声互为衬托,此起彼伏。都在忙,只有河道里三个光腚男人悠闲。落日把河水染得红彤彤的。
回到村子,卸下玉米秆,王小山抓二人进家喝酒。
王小山用一次性塑料杯子盛酒,一瓶白酒,刚好三杯。二毛看见桌上有两个猪蹄,一盘卤肉,一只烤鸭,口水泛起,二目放光,就想抓一块送嘴里。王小山和铁柱都晓得他的德性,二人有意似的,慢悠悠地吸上烟,并不急着端酒。按普通的规矩,不喝酒不许夹菜吃。而二毛注意力没在酒上,盯的是桌上喷香的肉。
院子里水池边有几棵竹子。那只引起争议的鸭子在水池里突嘟了半天,这会儿累了,卧在竹根处歇息,一动不动的。
“这扁嘴子倒像你家的。”铁柱指指竹根,对王小山说,“在我家时却一刻都不停下,叫个不停。”
“咋会在你家?那是俺的。”二毛不同意,“在俺家也是恁老实。”
王小山摆摆手,叫他们别再争吵。他端起酒杯,在桌面上蹾了两下,轻呵一声,告诉二人,他平时客人不少,可本村人来这喝酒的不多。言下之意,铁柱和二毛比村里其他人光贵一些。
这时二毛才发觉面前有一满杯白酒,连连摆手,声称自己喝不了恁多。铁柱轻蔑的一笑,朝王小山使了个眼色,说盖房子上楼板时你可是喝过的。二毛说那只是小半杯,还是你们硬灌的。周围的村子规矩差不多,盖房上梁时,现在全是上楼板了,主家要管一顿酒席。人家都喝酒,只有他二毛大筷大筷地夹肉吃,言称自己不会喝酒。他贪婪的吃相以及吧唧吧唧作响的嘴巴叫人家生厌。光吃菜不喝酒,这明显的便宜不能叫他赚得这么痛快。自然,几个人一递眼色,逼他喝酒。的确没有量,一喝就醉。鉴于他平时手脚不稳,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便有人高喊“量小非君子”的话,激激他。
王小山发了话,今天在他家,不喝酒,别说猪蹄烤鸭,连个鸡巴毛休想吃到。话虽粗,听起来觉出仨人的关系近了不少,。
二毛仍说,我喝不了恁多。
王小山端了酒杯主动跟他俩碰了一下,然后说这杯酒三气喝完,讲究的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日本鬼子是三光政策,咱们是三大纪律,三气过后尽开颜。他一气下去,喝下三分之一,然后捏起筷子夹了块卤肉,在口中吧唧吧唧嚼起来。铁柱斜睨了二毛一眼,端起酒杯往嘴边一靠,唧啾一声,下去的比王小山的还多点儿,捏筷子时,有意将两根击打了两下,算是提醒正在发愁的二毛吧,也夹块卤肉在口里嚼,声音比王小山的还大。
二毛馋得光想吃肉,但这是治保主任家宴,比不得人家的上梁宴,那是大锅饭,能鱼目混珠,占些便宜,喝吧,还真是喝不了恁多,真恨自个的胃,你吃菜够一份,盛酒咋就脓包了呢。铁柱递他一支烟,说先打打劲,一口下去弄半杯,不太辣的。二毛笑笑,端着的酒杯有些抖,酒出了几星,王小山说,这酒可是闺女孝敬的,价钱比小磨香油贵,别抛洒了,铺张浪费是极大犯罪。
二毛说:“你两个是战友,合伙欺我不能喝。”
铁柱说:“当兵时俺俩八竿子打不着,他是侦察连,我是炊事班。”
王小山说:“你连一杯酒都对付不了,以后谁还跟你玩儿呀。酒肉朋友酒肉朋友嘛。”
二毛趁他们发笑时,冷不防将酒倒进了铁柱的杯里。等铁柱用手挡时,他的杯子已满了。铁柱说,你啥熊货,叫我替喝,你女人咋不叫我替你日呀。二毛涎笑着,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你不就能多喝二两猫尿吗?刚才村长说了,这可比小磨香油贵,你赚大啦。
“咹,咹。我可不是村长啊!”王小山打断他。
“那也差不多。”二毛说,“支书不在家,村长不在家,村里全靠你了。”
村委班子因为支书与村长打架,互相告状,等于是瘫痪了。能负责任的就剩王小山和会计了。上面通知开会,都是王小山去。需要开个介绍信什么的,人们便去找会计。会计呢,是王小山的连襟,老实巴脚的,自然与王小山穿的是连裆裤子。所以,如今村里人都明白,王小山干一把手,是赶早赶晚的事。况且,他有群众威信。前几年他在城里卖家电,已经挣了不少钱,只因家中老母瘫在床上,他才回来的。他有心叫她进城,但她去了一次,再不去了。说城里人太多,吵得睡不着,又说城里没有月亮。王小山的俩哥都在家,每家都有几个小孩,老太太喜欢热闹。每天摇着轮椅四处转转,与人拉拉话,比城里舒泰。王小山的家电商店只得交给闺女,自己与女人回来了。这年头孝顺的人少了,也就感人,就有威信。他回来晚了,要是早了,就能当村长。他的治保主任是增补的,原先的那个得了偏瘫,一走三晃,自身都难保,哪顾上村里的治保啊!
“再说我可罚你。”王小山指指酒杯,“先喝一气。”
铁柱要把酒给他倒回去。二毛将酒杯端在空中躲闪,说我连沾嘴都没有,叫你替,高看你了。说着低头喝了一口酒,咽下去,嘴巴嗍着,眼睛挤着,痛苦万状。赶紧夹块肉在口中咀嚼起来,没怎吧唧就咽了,喉节一动,马上又夹了一块,衔上。
看见他衔肉的滑稽相,铁柱指指王小山,夹起一粒花生米抛在空中,一伸头,用牙衔住了。他问王小山这一招还会不会。这是他们当兵时玩的,也不知谁说这个游戏可以训练定力和身体协调能力,于是营房里不少人比赛这个。有一次王小山没衔好,花生米吸进了气管里,差点儿送进军区医院里。经他一提醒,王小山夹了一粒往空中一抛,一伸头,还真衔到了。他推推二毛,说你弄一下试试。二毛抛了两下,都衔不住,说你俩以前练过,别合伙欺我。王小山说,我俩要想欺负你,还用得着合伙吗?二毛瞅瞅他们,没再言语。
等打第二瓶酒时,二毛用手捂住空杯,说什么都不叫倒酒,只叫头晕。王小山硬夺过杯子,倒上半杯,说你说的不算数,喝酒不晕,喝个龟孙,这一回照顾你。他将自己和铁柱的倒满了。
他俩喝下半杯时,二毛也在王小山的训斥中喝下一半。他的脸和脖子已经通红,眼前也发了虚。
王小山发话了:“你俩眼里要是有我,这只扁嘴子归我了。这样,你们中肯定有一个人吃亏。但是,我桌上的这只烤鸭比那个活的可贵多了。你们因为它,闹到乡里,我这年把的先进算是白当了。人家会挖挤我说,你还是治保先进,却连个鸭子的事都捏不烂。我可顶不住,我是个要面子的人。这鸭子归我,你们有没有异议?反正我是侦察兵出身,破这个事易如反掌。但我不想破,大家不要为了小事伤和气。”
二毛看看铁柱,铁柱正专心啃一块猪蹄子,像没听见一般。
王小山举起酒杯,说你们不发言,等于默认了,咱们干了这杯酒。二毛只好端起来,与他们一碰,一饮而尽。
送走了他们,王小山在村街上逛了逛。夜色已深,村里并不安静。站在村街上,能清楚地听到有人家正开着玉米脱粒机,那机器的声音磕磕绊绊,嘶嘶啦啦,并不悦耳。
宫林:本名张功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18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