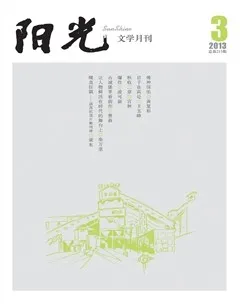黑煤
2013-12-29刘亮
一
客车摇摇晃晃跑着,双塔矿到了,下来几个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乘客,又上来几个人。接着,客车浑身抖了抖,摇摇晃晃起来。黑色的轮胎动了,带起一大片灰褐色的尘土,呜呜地开过去,扬起的尘土飘荡在了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
下车的人中有一位年轻人,他身穿滑溜溜蓝色的T恤,迈着青春跳跃的步子,给人以轻松愉悦的好感。他迅速走到别人前面,叫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向着双塔矿的招待所驶去。前面一段路稍稍上坡,三轮摩托不慌不忙地嘟嘟爬着。空气中散发着杨树的味道,洁白而轻盈的浮云,像一块块漂白的大丝巾,在蓝天中铺散开,像有人牵了一个角在抖动着,热风时紧时缓掠过头顶,摇动着杨树叶刷刷作响,仿佛雨滴洒在上面的声音。三轮摩托继续喘着粗气跑,车斗的挂钩不知什么时候开了,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到了招待所,年轻人扫了一眼招待所脏兮兮的绿大门就失望了。
“这个破地方。”他焦躁不安地嘟囔着,“要在这里索然寡味地待上几天,还不如在办公室耗着呢。”
年轻人是上海德意惠公司的技术员,叫李俊杰,来双塔矿维修井下割煤机。
到了中午,综采队长王富强宴请。
下午两点,王富强安排中班班长赵金柱带着李俊杰下井,并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李技术员。赵金柱把安全帽拍得啪啪地响,说:“放心吧队长,俺保证像看大妮一样把李工照顾得好好的。”
李俊杰没明白“看大妮”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从赵金柱有些粗鲁的哈哈大笑中猜透这句话不是什么好话。随即队长王富强就给他消除了尴尬,训了赵金柱几句,让他注意点儿自己的言语。又说李工是从大城市来的,听不惯你们的流氓话。赵金柱则哈哈笑着拍起了李俊杰的肩膀,有点儿道歉的意思,李俊杰感到他的拍拍打打很不舒服。
“李工,那就辛苦你了。”王富强站在罐笼口笑呵呵地挥手告别。
“队长,李工不辛苦。”矿工小个子接过了话,“下面有好多好多大妮呢。哈哈哈……俺们走了。”
“你说话注点儿意!”
“没事队长,李工又不是小姑娘哩。”
“你这小子!金柱,看着他们几个,别让他们胡乱喷粪了。”
“放心队长。”赵金柱说,“有我呢,俺们走了啊。”
一行人下到四百米的井下,再走到工作面还得一小时。
李俊杰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队伍中间,四周黑漆漆的,靴子声呱哒呱哒的,巷道里的凉风灵巧地顺着领口钻进夹袄里,似有千万条小蛇在身上爬,再配上头顶上橘黄色的矿灯,让李俊杰想到了恐怖片《夜行路》里的情景。赵金柱他们很熟悉走这种路,十个人犹如旧时占山为王的草寇,松松垮垮、摇摇晃晃、嘻嘻哈哈地边说边走,话题总是离不开女人——令李俊杰很不舒服的是:矿工们谈论女人时,说得非常简单直接和赤裸裸的,就在刚才,后面的小个子问那个胖子:你昨晚干了几次?你老婆给你炒羊鞭了吗?你老婆的奶子垂得咋样了?昨晚搞啥动作了?胖子没有一点儿拘谨和打哏,顺顺溜溜就把这些说给了小个子,接着胖子再反问小个子同样的问题。俩人有说有笑,嘻嘻哈哈的,全不把美好、神圣、缠绵的性爱说得委婉动听一些。就连年龄最大的老宋头(赵金柱说他干到年底就退休了),说这事时一点儿不亚于几个年轻矿工,他扯着嗓子回答小个子的问题:俺呀,不行啦,还是你们青年人厉害,一晚上三五次的,俺顶多两次。昨晚就没完成任务,一次也没弄,喝完酒直接就爬床上去啦。他的话音刚落,大伙呼呼哈哈笑起来,李俊杰没忍住,也抿嘴笑了。
“快到了。”赵金柱突然喊了一嗓子,声音上下跳跃着回荡在巷道里,有的声被巷道壁弹回来,撞在矿工们的身上,“哎呀,他奶奶的,这个破靴子忒难受了。”
“班长,回家让嫂子给你揉揉脚呗。”小个子笑嘻嘻地说。
“小个子,”胖子插了话,“还是让班长的脚,放你老婆的大腚上蹭蹭最好了。”
“俺老婆的腚不管用”,小个子反唇相讥,“还是放你老婆的大奶子上管用,是不是老宋?你见过他老婆吧,奶子真大,这么大这么大的。狗日的胖子,你老婆的奶子是不是让你揉起来的?”
“滚蛋!那东西能揉起来……”
“好了好了。”赵金柱打断了胖子的话,“李工在这里,你两个熊人说话注点儿意。”
“班长,”小个子点点头,像个小乌龟,“俺们就是随便弄两句,也没说啥,哈哈哈……李工不会在意的。”
离工作面还有五十米,李俊杰就听到割煤机的声音不对,刺刺啦啦的,像两张砂纸相互摩擦的声音。前面的灯光跳跃着一闪一闪,煤粉味轻飘飘地上浮下沉,人影像根枕木似的投下粗壮壮的影子。到了跟前,赵金柱和上个班班长边打趣边交接班,对方浑身通黑,牙齿和眼睛却闪着亮晶晶的白光,那人边说话,边瞟着李俊杰。
赵金柱说:“你瞅啥老周?下来个大妮,帮咱们修割煤机的。怎么样,今天前进了几米?”
“不到三米,龟孙子不听话哩。”
“有法啦,”赵金柱咋咋呼呼地说,“上海来的李工马上就会收拾它……对了老周,回家和嫂子干事时悠着点儿呀。”
“没事,不够还有弟妹在上面等着我呢。”
“哎呦,你个老流氓!”
“弟妹说不定就喜欢俺这样的老流氓,是不是金柱?俺们走了。”
“老周,上去给嫂子带个好,就说俺金柱在下面想着她呢,哈哈哈……”
对方十来个人像鬼影似的踢踢踏踏往回走,巷道里回旋着雷鸣般的哈哈声。赵金柱又骂了声老周,接着分了活。李俊杰蹲在割煤机跟前,把手电筒掏出,照了照ET-23轴承和ET-28轴承,其他人蹲旁边瞅着。李俊杰示意赵金柱停机,他侧耳听了听,接着让赵金柱再开机,他继续蹲地上照着。
“听清了。”李俊杰大声说,“ET-23轴承处的五号螺栓磨透了,我得换个新的。还有……开机法不对,把水压控制在一兆帕,前进二档位置,别用一档了。”
“俺们都是用一档,进度快哩。”小个子说。
“一档适合三十毫米煤层,你们这里超过四十五毫米了。”
“这回事呀,”赵金柱拍了下膝盖站起身,“他奶奶的俺们光图快了,这德国家伙还挺讲究哩,是不是老宋?以前用苏联的就没这么娇惯,咋使唤都行,这个还得讲究讲究哩。”
“和小媳妇似的要慢慢搞才行。”小个子嘿嘿笑着说。
“还是咱们李工厉害。”胖子说,“马到就能成功,俺们还想着多歇几天哩,结果这么快就找到法子啦,哈哈哈,班长,是不是?”
“是你个屁!光歇着能多挣钱吗?小子,想想你的下面吧……”
“啥下面,班长?”小个子饶有兴趣地伸过头,眼睛兴奋地眨巴起来。
“歇着就挣钱少,挣钱少老婆子就生气,老婆子生气你下面就受委屈了,这个不懂吗?”
“俺懂啦,懂啦。班长,俺还是愿意多挣钱。”
李俊杰再也忍不住了,扑哧笑出声,他正卸着螺栓的手也停住,手则一个劲地晃悠。因为第一次听到这些稀奇古怪且带着很浓色彩的俚语而有些兴奋和不好意思,他把笑红的脸扭过去,重新掂了掂螺丝刀。
“看见了吗?”赵金柱故作严肃样指着手下人说,“李工让你们捣乱得干不下去啦,现在都闭嘴,谁也不许再提裤裆里的事啦。”
“班长,是你先提的哩。”小个子轻飘飘抛出一句。
“是吗?我先提的就我先提的,你们就不要再添油加醋了,到此为止哩。”
“班长,啥动静?你听听?”小个子的耳朵灵巧地抖了两下。
“让你们别吱声嘛!”
“你听听班长?真的。”
“啥?他奶奶的。”
赵金柱吼完,警惕地侧耳听听,又蹲下,随即站起,拍了下液压支架,慢慢地朝后退,朝后退,接着,头顶的煤层开始往下掉煤块、矸石,哗啦啦一块,两块,五块,赵金柱的脸色由黑变青,嘴唇哆哆嗦嗦,手臂朝后张起,他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快跑,快跑,塌方啦!”
小个子张着嘴呆在原地,赵金柱一把抓起他扔到了液压架后面,接着抓李俊杰,推老宋、胖子,都扔到了煤洞深处。随即,哗啦啦一阵巨响,矸石、煤块如暴雨般砸下来,乒乒乓乓的,砸在干活的工具和液压支架上,犹如愤怒的人找不到对手而把怨气撒在工具上,铁锹柄立刻变成了五节。接着,烟雾迅速地升腾,包围,扩散开,瞬间,灰尘就把九采的整个工作面灌得满满当当的。
“朝里去,朝里去,戴上口罩。小个子,你他奶奶的可要趴好了!”
“班长,俺看不见了。”
“他奶奶的稳住,戴上急救器,俺们一会儿过来救你。”
“班长——”
“别说话了。趴好!”
大伙儿到了煤洞深处,有两个液压支架完好无损地坚守着岗位,赵金柱欣慰地靠在柱子上,心怦怦狂跳,汗水顺着耳朵尖啪嗒啪嗒往下砸。他又把矿灯拧灭,握着李俊杰的手,生怕他逃走似的。接着,他让胖子、老宋、大军们把矿灯拧灭,只留了三个。李俊杰被这突如其来、疾风骤雨般的塌方吓得眼睛乱眨,呼吸急促,全身哆嗦。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白净净的脸庞已经和煤灰没了两样。
“甭怕李工,有俺赵金柱在,你放心好了。”
李俊杰已经说不出话,傻呆呆地点了点头。
“班长,咱们……现在,咋办哩?”胖子结结巴巴地说,造成一个个浑浊的跳跃声。
“等灰尘散去后,先把小个子救回来。”
“咱们没事吧,班长?”大军颤着声问。
“能有他奶奶的啥事!”
大家不吱声了,时间仿佛静止了,人也静止了,大家看着大片大片的灰尘慢慢地往下降落,形成灰蒙蒙的烟雾覆在了地面上、支架上、开关柜上、人身上,有根水管被砸断了,喷出的水柱把那片的灰尘冲刷得袅袅升腾起了亮晶晶的水汽,在矿灯的照射下,形成了五颜六色的彩带。而此时,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傻愣愣的,像两块灰乎乎的石块,一动不动。
李俊杰想到最多的是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他从电视上看到过矿难——而自己却硬生生置身其中了。对于现在的处境,他没一点儿思想准备——到底塌方的程度如何?液压支架能撑多久?上面的人什么时候能到达这里?他心里乱得和麻绳一样。
二
一个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化矿井发生塌方事件,犹如一个体面人无来由地被人暴打了一顿。矿长刘坤感到愤怒和不解。不到半小时,他就把大小头头们招到了一起,开了一个简短的会:决定由生产矿长和综采队队长王富强带领矿山救护队开赴现场,其他各个部门都要竭力配合。半小时后,井口就聚集了五十名救援人员和十多辆救护车,嘈杂声此起彼伏,罐笼发出急迫的吱嘎声,滚轮飞速旋转着。为了安全起见,王富强先带十五名救护队员下去摸情况。矿长刘坤坐镇井口,听着各路来的消息。一小时后,集团公司张庆国局长和安监处长到了,人群自动分开一条缝。
“哪个采区?”张庆国急匆匆地问。
“局长,九采。”
“下面有多少人?”
“十个,加上李工十一个。”
“哪个李工?”
“上海来维修割煤机的技术员。”
“哎呀,咋就这么巧哩……”
有人把图纸拿过来,挂在墙上,矿长刘坤指点着九采的位置,矿总工在一旁小心翼翼讲解着,听得张庆国的眉头皱起来,仿佛瞬间长在了一起。
“九采去年不是评了个尖刀班吗?”
“被困住的,就是。”矿长刘坤小声回答。
“……”
刘坤把名单递给局长张庆国,张庆国抖抖纸,看起来。屋外突然传来尖厉的警笛声。
“是保卫处的王处长。”秘书说。
“让他们把警笛关上。”
地面上的人正稳步地救援着,赵金柱们已经开始自救了:他率领其他矿工正救小个子——他被倾斜的支架柱子别住了脚。
“班长,俺的脚没事吧?”
“班长,俺不会残废了吧?”
赵金柱没说话,和老宋猫着腰查看现场:发现是巷道末端连着工作面段塌方了,塌方处把工作面通向巷道的路堵死,外面什么情况不知道,反正这段路是堵上了。老宋说,幸亏是巷道末段,要是工作面塌了,咱们全得活生生埋底下。俩人又猫腰看看几个液压支架,基本完好,转回身去救小个子。先是胖子顶了几下液压柱,没反应,接着又上去两个人,还是不行。
“班长,俺的脚不会断吧?”
“现在啥感觉?”
“麻,麻哩。”
“麻没事,别他奶奶的钻心疼就行。老宋,你去那边看着顶板,有动静赶紧喊。”
这会儿李俊杰还处于巨大的惊恐之中,他看着矿工们手扒肩扛在救小个子,仿佛一群老鼠在救一只被老鼠夹夹住的小老鼠。小个子哎呦呦地叫唤着,更加重了李俊杰的恐惧,他觉得自己的思维和身体已经断成了两截,大脑时而清醒时而空白,像现实又像做了一个冗长的噩梦——他中午吃下去的饭瞬间就化为了乌有,身上有种轻飘飘的,软绵绵的,犹如长途跋涉的水中人的感觉。
众人前后左右忙了半天,液压柱子纹丝未动,气得赵金柱连骂带叫,加上小个子哼哼叽叽的,弄得赵金柱的火气更旺。他恶狠狠地盯着液压柱,仿佛身前站的是他一个不共戴天的仇家。
“班长,得把液压架子上面的支头加固一下才行哩。”憨头憨脑的胖子突然献上一计。
“对对对,对呀。他奶奶的,大军,你爬上去!”
“好。帮我照着矿灯。”
“大军,把安全帽戴正,防止掉矸石啦!”赵金柱瞪着眼又喊,“胖子,把扳手递给他。”
这个法不行,大军把支头螺栓上紧后,支架还是倾斜,小个子仍旧哼哼叽叽的。老宋跑过来,提醒了赵金柱,说让李俊杰过来帮忙,他是技术员。又说,咱们这么使蛮力起不到一点儿实际作用,还是把液压支架重新冲上压——把支头摆正才可以。赵金柱点点头,示意胖子过去叫李俊杰。
“上这边来,李工。快点儿,帮帮忙。”
李俊杰呆滞地看了胖子一眼,慢慢移动着身子,仿佛在蹚着水走。
“咋弄,李工?”赵金柱急切地问。
李俊杰呆呆地站着,手如抽风的鸡爪子似的一个劲颤抖,一分钟,两分钟,他憋了半天也没吐出一个字,嘴唇继续抖动着,喉结迟疑地跳动着,脸上的虚汗也流成了线,赵金柱等不下去了,突然,他抡起胳膊捶了李俊杰一下,把周围的人吓呆了。
“他奶奶的李工,你倒是想个法哩,快救救小个子!”
“班长哩……”大军大声劝解。
老宋跑过来,拦腰抱住了赵金柱。
“李工,你快点儿想法子吧。”老宋可怜巴巴地说,“俺们就会使这些东西,可是不会修它们呀。你赶快,赶快,晚了小个子的脚再保不住了咋办!”
李俊杰如梦方醒,噢噢答应着,灵魂仿佛突然归了位。他眉头颤抖着开始查看液压泵,冲压器,压力表。胖子在一旁打着亮。李俊杰把液压数据重新输入,归了正常位,启动,调压,液压支架缓缓动了,支头抬起,柱子立正,托起了损坏的防护网,赵金柱眼疾手快,一下把小个子提起来。
“班长,哎呦呦,没事没事。谢谢李工啦,哈哈哈,俺的脚出来啦。”
“胖子,把他抱过去。”赵金柱把小个子塞到了胖子怀里。
众人一起往煤洞子里跑,胖子把小个子放下,老宋赶紧把他的靴子脱下来,小个子嘿嘿笑着说没事没事,俺的脚又不疼了。
老宋看完,给赵金柱说:“班长,幸亏小个子人矮脚也小,基本没压着。要不然麻烦就大了。”
小个子站起身走了两步,踢踢腿,跺了跺脚。他看见李俊杰低头喃喃自语着,反过来劝起他:“李工哩,谢谢你啦,哈哈哈,别担心。毕竟咱们这是大矿,不是小煤窑,上面的人比咱们还着急呢。”
说话间,队长王富强带着救护队已经来到了九采巷道口,巷子长有两百米,他们走到一半多的地方走不动了,王富强开始和上面指挥部通话,告诉现场情况。局长张庆国知道后,和总工、安监处长商量一下,拟了个救援方案,让救护大队周队长带着后援队伍下去。
秘书进来,悄悄告诉局长张庆国:省、市电视台,《齐鲁报》《济州青年报》《蔚山工人报》的记者们想要采访您。张庆国略一停顿,点点头,接着把安监处长叫到跟前,如此这般嘱咐了一遍,让他去接待记者。
三
地面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时,井下的赵金柱们开始吃晚饭了。他先是把饭和水收集在一块儿,让老宋和大军保管,到吃饭时统一分配。大家心悦诚服地听着班长安排,而李俊杰又恢复了木讷,任由赵金柱指挥着,自己已没有一点儿主意。他现在满脑子都是上海:那里的父母,公寓,街道,大楼,公司,人群,女朋友,超市,地铁,公园,酒吧,场景犹如剪影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突然又感慨起命运来:昨天还在上海的客隆商场和女朋友购物,今天一落千丈就困在了黑糊糊的井下,让他不禁想起电影里的穿越、时空隧道之类的事。
众人吃完饭,忧虑和担心又像小虫子悄不声息爬上每个人的脸,大家闷不作声。过了一小会儿,赵金柱突然一拍巴掌,喊起老宋,让跟着他去巡查。俩人小心翼翼转了一圈,发现工作面问题不大,液压支架挺好,关键是出去的路堵死了。俩人回来,把情况说给其他人,小个子先发言:“班长,咱们挖吧,和外面的人来个里应外合咋样?”
“挖?咱们的工具咋行?”胖子说。
“不行也得行呀,是不是班长?总不能等死吧。”
“我同意小个子的想法。”老宋说,“最好把人分好组,轮流着来。”
“我看可行,俩人一组吧。”赵金柱点头说,“其他人休息,保持体力,胖子和大军先上。”
俩人领了命,扛着铁锹摇晃着去了。小个子因为没事,加上恐惧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轻,竟和老宋开起了玩笑。赵金柱则闭目养神,其他人也大都歇着。李俊杰坐了一会儿,觉得腰酸背疼的,就去了割煤机那儿。拧开矿灯,借着橘黄色的灯光,他重新把磨细的螺栓卸下来,找到工具包,换上一个新的,把水压调到一兆帕,档位拧到二档。李俊杰叮叮当当弄着,小个子傻乎乎看着他,像看着一件骇人的稀奇事,他推推赵金柱:“班长,那小子是不是疯了,现在还有精神头鼓捣割煤机哩。”
其实赵金柱听见了,只是没去管他,他故意惊奇地问:“是嘛?把他叫过来吧,好省点儿力气,也省点儿电。”
“别弄了,李工,班长叫你过来哩。”
“那小子是不是吓疯了?”老宋嘿嘿笑着说。
“别瞎说。咱们几个人,越是这个时刻越得拧成一股绳才行,不能像树枝子那样分杈、长叶了。”
“是这个理,是这个理。”
赵金柱瞥了他一眼,突然指指头顶,意思上面的人在干嘛呢。
这会儿,救护队周队长带领第二批救援人员和综采队长王富强会合了,俩人查看完,商量一下,觉得一边挖掘一边做支架才行,防止挖掘时再次塌方。周队长是复员军人,脾气刚烈暴躁,说话斩钉截铁,他吼叫着把队伍分成若干组,叫人歇工具不歇。王富强和指挥部喊着话,让人送木板和大梁下来,做临时支架用。局长张庆国安排矿长刘坤从木厂抽几个骨干一块儿随着木材下井。刘坤犹犹豫豫地说:“木工都没下过井哩。”
张庆国急了,扬起手狠狠挥了一下。矿总工急中生智,说让掘进队的赵班长带他的人下去,那人年轻时干过木工。有人就去喊正在休班的赵班长了。
安监处长进来,把采访情况向局长张庆国汇报,说怎样怎样回答的记者。
张庆国说:“采访的事先搁一边吧,你现在联系矿接待中心的刘主任,把记者们的吃饭、住宿全部安排到矿外宾招待所,用最好档次接待,我有空再去看他们。记住,啥话也不要跟记者多说了。”
安监处长应声出去。
这个时候刚过八点,井口依旧人头攒动,保卫人员站了一圈又一圈,拉起的警戒线一会儿掀起一会儿放下,来来往往的各种车像乌龟似的慢慢爬行着,巨大的探照灯打在人们身上,投下了一片片粗大模糊的影子。秘书端着快餐盘进了指挥部,张庆国扫了一眼,没有动筷子的意思。矿长刘坤和几名副矿长劝他吃点儿,实际在场人员一个也不敢吃,都在等着局长开吃,他们才敢动筷子。
无奈,张庆国点了下手,示意晚餐开始。矿总工吃着吃着,住了嘴,凑张庆国跟前耳语几声,张庆国哦了一下,拍拍手说:“小马呢,小马呢?”
秘书从外面跑着进来。
“赶快,赶快,给食堂管理员打电话,让他们马上蒸肉包子,要牛肉馅的,给井下救援队送下去,快点儿!”
秘书小马去打电话。
这个时候,王富强他们正热火朝天挖着巷道,前面十来米好挖,基本没堵透,三拨人挖下去,路就通了。再往里走不行,有很多足球大的石块,铁锹用不上了,得挨个人手传递着搬出去,一会巷道就站成一个大长溜。
王富强看着长蛇阵,忧心忡忡地跟救护队周队长说:“关键咱们怎么能把风送进去,给他们通点儿气……也不知里面的氧气还能撑多久。”
周队长点点头说:“是这个理,王队,这儿离工作面有多远?”
“大概……有三十米的样子吧。”
“咱们先通个管子咋样?”周队长问,“从这里穿过去,到时把风管子接上?”
“也是。对对对,我给局长汇报下,不知这个法子管用不管用,咱们试试吧。”
送饭工把包子送下来了,顷刻间,浓浓的肉香味灌满了黑黝黝的巷道,队员们早已饿得双腿发颤,两眼眯缝起来,都停了手。
周队长骂了一嗓子:“快搬,快搬,吃饭也得他奶奶的轮流,想想里面的兄弟和他们的老婆们,快点儿快点儿!说你呢王金元,再往前凑就把你的鼻子拧下来!好,一二三组先吃,麻利点儿,四五六组等会儿,谁吃慢了他奶奶的就多搬三块哩!”
队员们踉跄着挤过去,抓起包子就往嘴里塞,包子皮被印上了一道道黑色的粗手印,他们连同肉馅、面皮咽下了肚,牙和眼睛却闪着亮晶晶的光。
王富强过来,把汇报结果和周队长说:局长同意是同意了,关键咱们咋个往里捅管子?
“没好法,先用大锤砸吧,看看咋样?”
“好,我去找大锤。赵班长,找几个有劲的人过来。”
直径十毫米的铁管子砸了八九下就弯了,王富强看看管头,觉得管子太细,就让掘进赵班长找来直径三十五毫米的,当砸进去一个胳膊深时就听着里面砰砰的响。王富强知道是碰到里面矸石了,让人把管子抽出来。众人开始挖时,一名队员嘟囔着说:“王队,里面还有多少块石块咱们看不见,就这么光砸,效果不一定好使哩。”
“你他奶奶的不砸咋就知道效果?”周队长听见了,立马嗷嚎起来,“甭废话了小子,快干活!”
“周队,他说的有些道理。”王富强说,“不过也没好法,咱们先砸试试吧。”
砸了一会儿,管子不动了,再使劲,外端都砸得起褶皱了管子还是不往里走。王富强让队员停下,他摸着热热的、伤痕累累的管头,一个劲地摇头。掘进赵班长突然想起一招,说在管子那头安个钻头,咱们手动着往里钻,兴许那样好进些。王富强和救护周队长交换了下意见,周队长也觉得这个法比憨砸管用,就派一个人跟着赵班长去找电焊和钻头了。
四
地面过一天,井下相当于过三天,赵金柱他们深知这个道理,可李俊杰并不知道,他正无精打采地唉声叹气。小个子过来和他开了几句玩笑,看样子效果不佳,李俊杰仍愁眉不展的——这是他第一次在四百米的井下睡觉,也是他最不想睡觉的地方。他靠在煤堆上胡乱思忖着,脑子又飞回到了上海。突然他低沉、软绵地哭起来。老宋紧挨着他,拍拍他肩膀,谁知赵金柱却火冒三丈,腾地站起身,指着李俊杰破口大骂:“哭啥子,就知道他奶奶的哭,打起精神来!听见了吗?全都他奶奶的打起精神来睡觉!”
老宋说了几句漂亮话,想缓和下沉闷的气氛,谁知李俊杰哭得更狠了,小个子和胖子也过来劝他,让他放宽心,明天咱们就能出去。李俊杰呆滞的目光仿佛凝固了,什么话也讲不出,身子往后一挺,又躺在煤堆上。赵金柱火气没减,继续骂着:“他奶奶的这么大的矿,还救不出咱们这几个屌人吗?啥事放宽心了,都赶紧睡他奶奶的熊觉去!”
大伙儿不作声了,闭上眼,心情沉重地各想心事。李俊杰还在婴儿般抽咽着。
巷道那头的王富强他们并没停歇,继续对付着铁管子:众人像拧螺丝似的轮流转动把手,看样管子焊上钻头比没有钻头强,现在已经钻进了五六米。
王富强看看表,快夜里三点了,跟周队长说:“让队员轮流歇歇吧,我给调度打个电话,让他们再送一张图纸下来。”
周队长一梗脖子:“歇啥歇?打仗的时候命都不要了,还能歇?不歇,熊东西们使点儿劲,到十米了才能停手。”
王富强说:“还是歇歇,就五分钟吧。”
突然,正拧把手的两名队员哗啦一声跪在地上。有人把他们拉起来,周队长刚要发火,一名队员喊了一嗓子:“队长,钻头断了!”
王富强跑过去,示意大伙往外拔管子。好不容易拧进去的管子,现在拔也很费事,大伙喊着号子拔着。
“我操他八辈子祖宗的……狗日的钻头,气死我了!”周队长恶狠狠骂着。
局长张庆国一激灵抬起头,吓得秘书,安监处长和矿长刘坤直起了身子。
“啥情况了?”
“局长,刚才王富强要了一张图纸,说正在钻管子。你再趴会儿局长,天还早着呢。”矿长刘坤搭了话。
“现在几点了?”
“不到四点哩。”
“一会儿别忘了给食堂管理员打电话,让他们赶紧做饭,给救援队送下去。”
“好,俺这就打电话。”
夏天的夜很短,早上五点多天边就开始发白,一会儿红晕泛上来了,天空浮现出了一大片网状的白云,都镶着亮闪闪的红边。值班民警表情严肃又有些木然地守候着警界线,一辆辆救护车一字排开,司机趁这个空当在里面打着盹。矿长刘坤陪着张庆国在指挥部门口转了一圈,折回来,矿总工和安监处长还在刺眼的白炽灯下研究图纸。
“想出别的方案了吗?”张庆国点上烟问。
“还是想着能不能从十二号巷道挖过去……”总工说。
“那个巷道不是废了嘛。”矿长刘坤问。
“先找人进去测测瓦斯浓度,只要条件允许,咱们就从那里试试。”
“您看呢,局长?”刘坤仰着脸问。
“只要行,就抓紧时间弄吧。”
矿总工开始给调度室打电话,让派瓦斯员过去。
这时,局秘书进来了,身后跟着两个挎照相机的年轻人,他小声跟局长张庆国说,这是咱们局报社的记者,想趁这个空隙给您拍几张指挥现场的照片,想用在局报上。张庆国没吱声,秘书一挥手,俩人快速摁动了快门。矿长刘坤避到了边上,稍一等,他冲副矿长努努嘴。副矿长心领神会出去,一会儿也领着两个人进来,刘坤皮笑肉不笑地跟张庆国说了想法,想让自己矿的宣传科拍几张照片。张庆国听完,一脸得不痛快。秘书赶紧把刘坤拉到一旁,悄声说:“别添乱了,我让局报把照片传给你们不就行了。”
一个小时后,调度室打来电话,说是十二号巷道瓦斯超标。
张庆国气得点上烟,吧嗒两口说:“他奶奶超标了,还有啥方案吗?”
矿总工小心翼翼地说:“局长,要不从八号巷道挖过去咋样?就是有点儿远,有五十米哩。”
“还有其他方案吗?”
总工摇摇头。
“五十米就五十米,反正比坐这里干等着强。刘矿长,你抓紧找人挖吧。”
“王富强他们咋办?”
“两边同时进行呗。你现在任务就是麻利组织人,其他别管,快点儿!”
上面组织人时,赵金柱也在组织人,他正招呼大家吃早饭,说再苦再难也要填饱肚子才行。李俊杰一夜没睡着,眼皮耷拉着像有石子坠着。小个子又开起他的玩笑,赵金柱瞪了他一眼,让他麻利吃,还得干活。老宋蔫巴了,吃得慢条斯理,胖子却狼吞虎咽的吧嗒嘴,仿佛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样子——实际他们的饭已不多:昨天下井带的饭,基本是一顿的量,现在是第二顿,往后还不知道要吃几顿。赵金柱事先把饭定好了,说是每顿饭五个人只能吃一个馒头,喝一小口水。胖子吃完感觉和没吃差不多,摸着肚子嘟嘟囔囔。赵金柱也不理他,从腚下摸起安全帽去巡查了。
现在轮到小个子和李俊杰搭伙挖塌方的矸石,俩人无精打采地扒拉着,小个子的嘴并没闲着,一边挖一边问李俊杰:大上海是个啥样?繁华吗?大不大?李俊杰有气无力回答着。小个子铺垫完前边的话,突然话头一转,又问李俊杰,上海的女人咋样?那个时髦吗?啥都风骚吗?玩起来带不带劲呢?小个子的话刺激得李俊杰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小个子却兴头很浓,一个劲地催他答。李俊杰觉得男女之事应该温柔、细腻的属于两个人的私密,可小个子却不加掩饰地说出来,让他难以接受这种赤裸裸的直接。他闷头不吱声了。小个子却急迫得像看见自己心爱的女人裸光着身子而突然阳痿的壮汉,他扑哧一声坐在了矸石上,脸色因急迫也泛起了红晕。
“说呀李工,你那里的女人咋样?玩起来带劲吗?”
“李工,你说说呗!”
李俊杰被激怒了,掉头就走。
赵金柱看着这一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扯着嗓子问小个子:“你俩咋了?他奶奶的干点儿熊活咋还吵起来啦?”
“没吵架,班长。”小个子笑嘻嘻地说,“俺就是问问李工,上海的女人咋样,好玩吗?他就生气了。”
“你老问啥,净他奶奶的瞎操心。猴子,你去和小个子搭伙。”
胖子过去拍拍李俊杰的肩膀,让他消消气,说小个子就是喜欢嘴上图痛快,实际他连根鸡毛也没碰过,甭和他治气了。李俊杰泛红的脸颊渐渐消退,没说话,木讷地点点头。
五
记者们每天都聚集在井口或者指挥部门口想捕捉第一手新闻,尤其每次的罐笼响,记者们都像齐头并进的浪头往前涌,而随着罐笼门的打开,他们的失望就立即显现在了脸上:三天来,除了见到疲惫不堪的救援队上井,要么就是全副武装的瓦斯安监员下井,而被困矿工的影子一个也没见到。人们议论纷纷、胡乱猜疑起来,把矿工的生存几率预测到了百分之十。他们越这样议论,矿长刘坤的心悬得越厉害,局长张庆国的脸色也不好看,他让刘坤通知保卫科把警戒线拉大一些。
这个时候,有的矿工家属坐不住了,吵嚷着要局里给个说法,也有的要求解决子女就业问题的。刘坤不敢做主,跟张庆国汇报了,张庆国哼哼两声,没做指示。队长王富强听说后气得直跺脚,说这边正急急救援呢,有的家属竟在想这事,他奶奶的安的啥心呀!倒是班长赵金柱的老婆不错,没参与其中。刘坤抓住这个缺口,和赵金柱老婆商谈了一个小时,想让她劝劝其他家属,让她们别紧着找这事,给救援队一个机会。再说,煤矿到年底就是安全生产五周年了,谁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出事,保证会全力救援的。
井下的赵金柱他们正在收集工业水——虽说带的饭早已吃完,可割煤机的冷却水还滴答着,大家正喝水度日。小个子也不上蹿下跳找李俊杰聊上海女人了,左边紧挨着胖子,右边是李俊杰,三个人有气无力地躺在煤堆上。老宋弓着腰起来,赵金柱问他去哪儿?老宋指指肚子。赵金柱知道老宋想干嘛,摇了摇头,把接满水的安全帽拿开,换了一个。老宋转到割煤机旁,摸索着,把皮带上的精煤抓在手上搓起来。赵金柱好奇地瞅着,精煤在老宋的手里发出亮晶晶的蓝光,像鬼火,也像钻石在跳舞。老宋搓了一会儿,捏了一小撮,像吃炒熟的豆子似的慢慢咀嚼着,嘴里发出了咯吱咯吱的脆声,看得赵金柱傻了眼。他把安全帽固定好,挪到老宋跟前问:“哎呀呀,老宋哩,这个东西也能吃?”
“能吃能吃,好吃着哩。”
“有些瘆得慌,不会死人吧?”
“啥死人。煤是树变的,能死哪去,你说是不班长?”
胖子听见关于吃的话题,摇晃着抬起头。他顺着晶莹的蓝光望过去,煤粉确实闪呀闪的在发光。他推推小个子,小个子软绵绵地说了声:“别动别动,那边就是有个大妮,俺也没劲去玩了,还是你们去吧。”
胖子说啥大妮,是吃的。李俊杰也听见了,抬起头,小个子突然摇晃着坐起来。
赵金柱学着老宋的样子搓起粉煤,不过他挺有法,嚼完后就着冷却水送下去。大伙儿看着他俩吃,既惊讶又新奇,仿佛在荒漠中看见了一汪水。
“别看了。”赵金柱的嘴角淌着蓝色的煤汁说,“都麻利吃,跟俺俩学。这样,这样,喝点儿水,别他奶奶的直接吞就行。”
“班长,这个真能吃哩?”小个子说。
“班长……”大军喊。
“喊啥喊……还有你李工。快吃,不吃他奶奶的就活不了,快点儿。”
李俊杰皱着眉头,右手颤巍巍地捏了一把,搓起来。最后试了几下,也没敢把煤放进嘴里。看着他们几个,也是闭着眼皱着眉在嚼,他才小心翼翼地把一小撮放进嘴里。
过了一会儿,赵金柱把胖子的耳朵拧了一下,让他少吃点儿。又说这东西压饿,吃两口就等于吃三个馒头,小心撑死你个熊东西。赵金柱的话音刚落,巷道口哗啦一下,接着又两下,矸石和煤块落了不少。赵金柱猫着腰往里跑,大家愣下神,一看他正转移安全帽里的水,都明白了,跟着跑过去。
正在外头的王富强和救援队员也感觉到里面塌方了,吓得朝后撤了十来米。周队长没动,仿佛在和塌方较劲似的,还是直挺挺立着。王富强指挥两名队员把他拉回来。周队长气急败坏地挣扎着,嘴里还骂着他奶奶的干啥子!干啥子!王富强没去劝周队长,赶紧给指挥部汇报,说巷道又塌方了一次。得到的答复是先撤出来。周队长不愿意走,说是里面塌又不是外头塌,撤啥?得赶紧挖才行。
他们那天用的往里砸管子的方案已经不用了,因为里面的矸石太多,钻头根本钻不深,只能手动,又回到了原始方法,手搬铁锹挖的。因为这,王富强和周队长愁得不轻,说只能这样了,挖吧,只求他们能多撑几天。
听听里面没动静了,王富强把人带过来。他观察了,再有十来米就能挖到塌方处。周队长喊着号子,也吆喝着,咋呼着,加上气钻声,铁锹声,所有的声音搅合在了一起,在巷道里上下左右撞击着,传到了里面。首先是小个子听见了,他嘘嘘着,示意大伙别吱声。他趴在矸石墙上听着,突然兴奋地叫起来:“班长,外面有人,有人,有人哩!”
赵金柱过去听了听,隐约有动静,就拾起一块拳头大的矸石,照着矸石墙有节奏地砸起来。一会儿,他停下后,外面没有响应。赵金柱又砸了几下,听听,外面还是隐隐约约的嘈杂声,没有人回应他。小个子骂起来,说这帮子熊人光知道挖,也不竖起耳朵听听,都是一大群笨蛋。砸累了,大伙儿坐在矸石堆上休息。
中午饭吃的还是粉煤,然后砸墙,外面没一点儿反应,最后赵金柱和大军都泄气了。小个子也过来砸,老宋也砸,还有胖子,大家都砸了一遍,外面始终没有回应。大家垂头丧气地坐在一起,
突然,李俊杰像发疯的公牛似的,一跃而起,搬起一块头盔大的矸石猛砸了过去,矸石被弹回来,断成了三段,接着他又搬起一块,猛砸过去,哗啦一声,矸石墙掉下来一大片矸石。他不甘心,拾起脚下的矸石又猛扔了出去,矸石墙哗啦啦又掉下了一些。赵金柱吓坏了,上前把李俊杰抱住了。
“放开我!”李俊杰咆哮着像匹野马,使劲甩着膀子,力气仿佛重新回到了他身上,把小个子他们吓了一跳,大家像看怪物似的站起身,“我一定砸烂它,我就不信他们听不见。我们在里面,里面呀,你们听见了吗?快点儿,我们在这里呀……”
赵金柱一使眼色,大伙儿一拥而上把李俊杰摁在了地上。
“你们干什么,别拦着我,我要出去……”
“好了,别他奶奶的使蛮力了。”赵金柱咋呼一声。
“我就是想砸,想砸,使劲砸,让他们听见,我想出去,想出去……”
“知道你想出去。”小个子骑在他身上说,“我也想出去,大家都想出去,可也不能这么用蛮力,万一他奶奶的你把上面的顶板震下来了咋办?”
李俊杰不蹬腿了,也就过了三秒钟,他突然低沉地、抽噎似的哭了。赵金柱把他拽起来,拍着他的肩,像安慰孩子似的。
老宋仿佛被李俊杰的情绪感染了,不太甘心,在最后又砸了两下。突然一块顶板落了下来,老宋只是闷着哼了一声,接着啪嚓,木桩似的倒在了地上。
“老宋!老宋……”小个子边叫着边扒拉着。
赵金柱一下把小个子拨开,抱起老宋就朝煤洞跑。大家跟过去,到了里面,赵金柱放下老宋,他没有任何反应,鲜血像蚯蚓似的爬了下来,慢慢地,顺着眉梢,眼睛,鼻子,耳朵,爬满了他的整个脸,赵金柱用手给他擦着。
“老宋,俺是金柱呀。”
“老宋,老宋,俺是金柱……”
“俺是胖子,听见了吗老宋?”
“老宋,俺是大军……”
“他奶奶的老宋,你醒醒,醒醒,俺是小个子呀,你醒醒,睁开眼,你说……退休了找俺钓鱼的,你快睁眼呀。他奶奶的老宋,再不醒俺就日你老婆了。老宋,俺的老宋……你他奶奶的坚持坚持,一会儿咱们就能出去了。外面的人,王富强,刘坤,你们狗日的快点儿挖呀,老宋不行了,快点儿挖呀……”
“胖子,把小个子拽过来。”赵金柱哭着喊。
六
十一个安全帽现在是十个了,帽子里的水也越来越少。
大家软弱无力地一字排开躺在煤堆上,任思绪轻飘飘地游荡,又是一天过去了,胖子成了瘦子,小个子变成了小猴子,猴子成了一根麻秆,李俊杰也很虚弱,身子瘦成了虾米状,耷拉着头,眼睛时闭时睁的,生怕闭时间长了再睡过去——这是赵金柱教的,说现在只能打盹,不能他奶奶的睡大觉,还要相互提醒着。
现在,大家呼吸越来越沉,越来越困难,每喘一口气就像小孩拉风箱一样费劲。大家明白,在这里就是饿不死,时间长了也会憋死。之前赵金柱和大军、小个子他们几个分析:这里面的氧气可能是割煤机的冷却水带来的,现在水管里的水越来越少,滴滴答答的,说明冷却水管被第二次的塌方砸坏了。
大家继续仰面躺着,赵金柱小心抿了一口水,递给胖子,胖子传给大军,大军舔舔水给了猴子,小个子没接水,耳朵却抖擞起来,随即咳嗽一下,有气无力地、断断续续地说:“班长,俺听见,说话声了,他们可能打通了,像是咱队长……王富强的,破锣嗓子。”
小个子的话把赵金柱吓一跳,他赶紧听听,没声,又听听,还是没动静。他怀疑小个子出现幻觉了,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出现幻觉不是什么好事,不禁瞅了瞅正在“睡觉”的老宋,越看越心惊胆战的,随即寒气也劈头盖脸袭来,他抓住了小个子的手。
“班长,俺不是女的,你抓俺干啥哩?”
“别说话了。”
“班长,你咋啦?俺真听见动静了。”
“你个熊东西,别说话了行不行。”
“真的,是狗日的,咱队长王富强……”
“躺好,躺好了。”
“俺说的是真的……”
“知道了,你说的都是真的。”
“班长,俺现在……咋就这么想俺儿子……还有俺老婆了呢。”
“知道了,他奶奶的……你快歇着吧。”
“要是上去……俺一定要日她个……十次八次才过瘾呢……”
“好呀,你上去……就他奶奶使劲日吧,俺们可是困了……”
大家进入了睡眠状态。李俊杰也闭上眼,思绪接着上来,随即飞了起来,像根魔线,嗖嗖地飞向上海,飞向家里,飞向女朋友,飞向公交地铁,飞向拥挤不堪的超市,飞呀飞;自己的身子也跟着飞起来,掠过农田,河流,村庄,房屋,大桥,沿着铁路线,越过群山、大河,跟着魔线,身子轻飘飘地飞在半空中,耳边的风呼呼作响。
就在这个时候,矸石墙哗啦啦两声,轰然倒塌了,紧接着橘黄色的光线透过缭绕、呛人的煤尘射进来,人影晃起来,人头攒动的,矿灯闪闪的像是在跳舞。王富强大跨步进来,紧跟着是周队长和队员们,大家像猎狗一样拿眼扫射着黑糊糊的煤洞子。
“人呢?他奶奶的给我回一声!”
“在那儿,”一名队员喊起来,“周队,人在那里。”
“乖乖们,挺住呀!快!快!都抬出来。”周队长喊。
王富强则双手哆嗦着向地面指挥部报告。
没一会儿,井口处乱成一团了,对讲机和电话声此起彼伏,人群骚动起来,救护车一字排开,滚轮嗖嗖叫着,罐笼嘎吱嘎吱往上爬,被困矿工一个个的被蒙着双眼抬上了井。
就在前两天,老宋的老婆被从两百里外的农村接到矿上,不知道是因为激动的还是紧张的,期盼了三天,现在看到井下的矿工被抬上救护车时,她想自己的男人可能还活着,就控制不住了,突然冲过警戒线,跑向救护车。有人过来阻拦,人还没碰到她时,她却尖叫着、失魂地大叫了两声,一头栽到了地上。有人把她拽起,一块儿抬上了救护车。
局长张庆国看救护车走了,交代刘坤:让记者离医院远点儿,死人的事先别说,我回去想想法。随后坐轿车走了。
现在矿长刘坤开始指挥,处理现场,清理塌方,接待记者。
晚上他又把记者们召到一起,开了一个临时会,把大意说了说:总之,通过局领导,矿领导的正确指挥,全面协调,迅速圆满地把十名矿工解救了上来。对于老宋的死只字未提。有记者好奇,不是十一名矿工吗?现在怎么是十名矿工?刘坤说了缘由,正好有一名矿工那天休班,误以为全部下井了呢。
对于这个解释,记者们半信半疑。加上后来警界线扩大,他们靠不到近前,也没看清到底抬上来几个。还有一个原因,老宋老婆的突然昏倒,也被抬上救护车,让他们更难辨认到底抬上来几个人。
晚上,刘坤就被张庆国叫到局长办公室,在场还有几名副局长和安监处长。
刘坤瑟瑟发抖地站在办公桌前。
“看看你干的好事!”张庆国突然吼了一嗓子。
“局长……”
“你说,你们咋搞得塌方了?咋检查的?咋预防的?咋他娘的执行的!你说说,咋捣鼓的?咋给我保证安全生产五周年无死亡的?咋……”
刘坤低着头,一个字不敢往外吐,额头上的筋突突跳着。
“听好了,对外一定要咬定是十名矿工。老宋的事我正想着弄,明白了吗?”
刘坤点着头,还是不敢说话,喘气匀乎了一些。
“年终奖咋办?你们是不是不想要了?”
刘坤略微抬抬头,小心地朝上瞟了一眼。
“扣百分之二十。对了,那个上海人咋样了?”
“没大事,局长。他输点儿液就行。”
“好了就给他送点儿纪念品,派专车把他送回去。我一会儿再给他们的老总打个电话,让他们把嘴巴闭严点儿,毕竟咱们是他们的大客户。”
张庆国训完刘坤,还不解恨,又把一摞文件推到了地上,接着把脸转向几名副局长,说了自己的看法:还是按以前的做法,把老宋这个死亡名额卖给辛庄矿吧,把他的关系转过去。那里是镇上的小矿,一年死三五个人很正常,咱们这里可死不起。至于价格,和去年的一样,给他们二十万,就当是他们矿死的人。
几名副局长点头赞同着。随后,张庆国安排一名副局长去了辛庄矿。
刘亮:1975年出生。2008年开始写小说,鲁迅文学院第15届高研班学员。小说见于《山花》《阳光》《长江文艺》《作品》《山东文学》《黄河》《福建文学》《绿洲》等刊物。有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转载。中国煤矿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