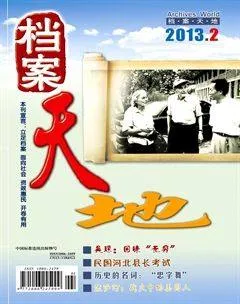照片感怀
2013-12-29杜青敏
作为一个有着多年档案情结的档案人,为家庭建立档案已经成为一种本能,然而在众多的家庭档案中,最受欢迎的当属照片档案,儿子每次翻阅都是眉笑颜开的,我却不尽然,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再看照片时的视角、心境往往与前不同,尤其是看到父母的照片时,不知不觉间会涌动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和莫名的感慨。
父母最早的合影,是1959年秋在县城唯一的一家照相馆拍的,22岁的父亲浓眉朗目,蓝色上衣的口袋中插着钢笔,脖子里围着白毛巾,十分精干。20岁的母亲端庄大方,身着红上衣,围淡青色纱巾,温柔恬静。新婚不久的两个年轻人身无片瓦(母亲原话,是说家里很穷,没有住房),但因为年轻,充满对新生活的向往,所以,依然青春勃发,神采飞扬。照片虽然是人工着色,但整个画面非常和谐自然。这张照片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美得近乎神圣。
我的照片档案里还珍藏着两幅全家福,一幅是黑白照,一幅是彩色照。每当我看到黑白照上母亲那紧抿的双唇,就想起了当时的情景。
1976年春,父亲的好友要调回原籍工作了,临走前送给我家一张3寸、半身的全家福作留念,大概父母也觉得全家照张相很有意义,于是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们姐妹打扮得整整齐齐跟父母去县城唯一的照相馆照相。照相馆里的人认识父亲,极力推荐5寸的全身照,父亲爱面子就答应了。母亲心想:3寸的全家福就挺好,在家都说好了的,怎么人家忽悠几句就改5寸了,这凭空多交的2元钱不知能办多少正事呢。心里不痛快,母亲便抿紧了双唇和父亲端坐前排,三姐妹站在身后,我因年幼无知,登了两个小凳站在姐姐中间依然笑得很灿烂。
同年7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边向全家喊:“地震了,地震了”,边急切地推我,不等我明白怎么回事,就飞快地把我背到院中,漆黑的夜里,大喇叭里惊悸的音乐一响,我的迷糊劲全消了,一家人全都站在院里不知所措,母亲蓦地转身冲向屋子,先后取出了草栅、被单等生活必需品,幼小的我躺在草栅上,数着星星,看着银河很快就睡去了。
事隔多年,一想起母亲在大地震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生命安危,往返土坯屋数次,去取一家人的急需用品,就感到很感动,一个连生命都不顾惜的母亲,怎么会对家人吝惜2元钱呢,还不是穷闹得。
当时父亲体弱多病,工资只有24元,每月还要给乡下的爷爷、大爷爷18元,母亲工资也只有28元,除去房租和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外,也要孝敬姥姥、姥爷,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为补贴家用,母亲带领我们捡过猪毛、剥过花生、缠过线子……母亲要当好这个穷家真的很不容易。
另一幅全家福是外甥12岁生日时照的,父母还是端坐前排,三姐妹站在身后,这一次母亲的眉宇舒展了,嘴角向上翘了,一家人喜笑颜开,其乐融融的。是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老人们都照顾了,儿女们也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下一代也都承欢膝下,济济一堂了,父母怎能不高兴呢。
但细细看去,父亲的头发、眉毛都已稀疏花白,一双大眼睛下面出现了大大的眼袋,脸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母亲的头发也已灰白,脸上虽然没有那么多皱纹,但背明显的驼了……看到这些,心里略过阵阵酸楚。
父母也曾青春年少,也曾有着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他们放弃了很多,牺牲了很多,如今我们风华正茂,他们却已风烛残年,摸挲着老照片,我顿悟了什么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光一去不复返。
我们阻挡不了时光的流逝,阻止不了生命的衰老,但父母的爱已像涓涓溪流,流淌在生命中、血液里,我们可以将它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时光啊你慢些走吧,让我们把尽可能多的关爱反馈给父母,虽然再多的爱也无法报答父母的恩情,但母子连心,再微小的爱他们也会感知,也会满足。
岁月无情,岁月有痕,照片档案提醒着我们那些真实的过往,刻骨铭心,挥之不去;岁月无情,人间有爱,让我们珍惜生活,珍爱亲情,愿普天下所有的父母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