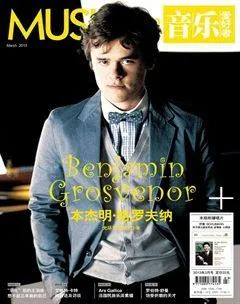“未完成”究竟“完成”了吗?
2013-12-29田立
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因为只有两个乐章,所以又名《“未完成”交响曲》。有人说,其实它已经完成了,有两点可以用来作证:一是虽然后人前仆后继地试图“完成”这部作品,但均以失败告终,这恐怕不单单是“才疏”的问题,可能它就不该有其他乐章,联想起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续写之事,于是断定“未完成”其实已经完成。二是从纯粹美学角度看,这部作品的意境是完整的,思想是完整的,因而美也是完整的,就像断臂的维纳斯一样,任何多余之笔都只能是续貂。
年轻的时候听别人,尤其是一些名家大师这样说,我也就全盘接受了,还陶醉其中,甚至煞有其事地给别人讲起了所谓“已完成”的理由。但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拿来”的审美就越令我不安,我越发不能认同这样的观点。如今已近知天命之年,我终于鼓足勇气放弃了当初不懂装懂而接受下来的所谓“高见”。
在我看来,这部“未完成”至少在乐思上的确是没有完成的。第一乐章一上来那个阴郁的主题就透出了焦虑、躁动、紧张和不安的情绪,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开头部分的阴沉主题,我们甚至可以说两者是何其的相似。尽管总有人喜欢说舒伯特晚期有向贝多芬靠拢的倾向,但从史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舒伯特在这个主题上借鉴了贝多芬,因为两个人在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上几乎一致,在其中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公开发表、公开演奏的情况下,借鉴显然无从谈起。但也正是这种创作时间上的一致,使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两个人在主体基调上的“巧合”,其实绝非巧合。
十九世纪初的欧洲社会正笼罩在迷蒙的气氛中,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星星之火到轰轰烈烈,经历了血雨腥风和奸人篡权以及初尝胜利果实后的脆弱、敏感、浮夸和彷徨,人们在黑暗中觅得曙光,又在曙光中重温昏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对社会变革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希望、失望、迷茫纠结在一起,不可能不表现出焦虑、不安、恐惧和阴霾的情绪。当这种情绪反映到音乐中来,就是我们听到的“贝九”和这部舒氏“未完成”的局促主题。在这个精神层面上,两位大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不是情趣和才华的巧合,而是时代精神的真实表现。
然而,贝多芬此时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的丰富经历、倔强性格和深刻思想使得晚年的他在热烈中添加了淡定,在冲动中增加了沉思。他终于明白社会的变迁不是一场热闹的革命就可以完成,也不是一个普罗米修斯所能拯救,而是要建立在广泛博爱、自由和平等思想基础上的社会觉悟所能开启。于是,他在《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中把各种思想的碰撞展现出来,并最终用席勒的《欢乐颂》将他的理想升华。这种升华不但总结了其一生的感悟与觉醒,在音乐层面上也“回答”了前面几个乐章的疑问乐句,这在自莫扎特之后的欧洲音乐创作中几乎是一种不变的范式。
舒伯特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并且比贝多芬还要急迫地进入到“思想碰撞阶段”——贝多芬是在第四乐章才进入的,而舒伯特在第一乐章就已经开始了。但与贝多芬不同的是,舒伯特的碰撞没有结论,第一乐章那个焦虑不安但相对柔和的主题不断地被一个粗暴的齐奏打断,就像“贝九”第四乐章中那些没有答案的主题被后来演化为欢乐颂的粗暴主题不断冲击一样,舒伯特似乎也要否定着什么。遗憾的是,打断之后,没有新的乐思站出来回答前面的疑问,反倒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疑问主题中,无法挣脱,由此在逻辑上需要后面的乐章解决问题。
可是到了第二乐章,舒伯特还是没有结论,尽管阴云翻卷之下常有田园般幽静的意境,但若以此作为结论似有逃避之嫌。不是说音乐作品不可以以阴霾的情绪作为结论,后来的柴科夫斯基在他的《悲怆交响曲》中就是以这种情绪作为整部作品的基调和主题的;问题在于当作品以阴霾作为结论时,音乐的逻辑是完整的,如果没有达成这样的逻辑结论的话,作品就会呈现出未完成的状态,因此我们说舒伯特的这部作品的确未完成是站得住脚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舒伯特没有“回答”前面的疑问,进而以和“贝九”一样的完成面貌面世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舒伯特一定是想这么做的,这不仅是范式,也是任何一位作曲家必想的。我们不妨从舒氏另一部同期创作的作品中寻找例证:完成于1824年的《F大调八重奏》(D803)的第一乐章开头也是一个长长的疑问乐句,同样的低沉、阴郁;但与“未完成”不同的是,舒氏在这部作品中对疑问进行了回答,虽然这回答有些混乱,一会儿是热情的冲动(有几分“贝七”的风采),一会儿是回归自然的亲和,一会儿又是对古典精美的复古,却始终不见像贝多芬那样的深刻与广阔。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一个大胆的设想:后来人之所以无法将这部舒氏遗作完成,恐非仅仅是才能所致,也可能是一旦以其原有逻辑继续写下去,要么是“贝九”的重复,要么就是继续回到舒氏的“混乱”。无论怎么写,也无法造就一部人们所期待的伟大作品。与其这样,还不如保持其原貌,至少在意境上还是舒氏的优美与飘逸。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如果单纯以某种意境之美来欣赏“未完成”,它的美是不容置疑的,就如同“问君能有几多愁”寥寥七个字所蕴含的浓郁情感和凄苦之美一样,虽未见其后作答,但此意境已浑然天成。不过,李煜的这句名句如果没有后面“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唱作答的话,恐怕我们也很难夸赞其意境之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