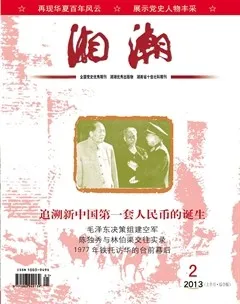你所不知道的金维映
2013-12-29张丽红

金维映是杰出的女革命家,也是李铁映的母亲,是中央红军走完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后到苏联养病,牺牲在战乱中。她漂亮、活泼、能干,对家人有情有义,对革命坚定不移,她枪法高超,喜爱唱歌,曾经是中央苏区众多农家女孩崇拜的偶像。
带动全家干革命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1904年出生在舟山群岛岱山岛高亭港一户贫穷人家。她的父亲金荣贵,祖籍山西,出生在浙江镇海县一个海边小村,长大成人后独自到舟山岱山岛谋生。因为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一家人不得不四处讨生活。
金维映6岁时,曾被送到宁波镇海叔叔家。8岁时,略通文字、为人真诚的父亲被人请到舟山定海公民招待所任账房先生并负责管理日常工作,全家从此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尽管家庭并不富裕,金荣贵仍然答应送女儿到舟山革命的摇篮——定海女小读书。
长大成人后的金维映身材修长,皮肤白净细腻,满头乌发,一双大眼睛会说话,是一位漂亮的女人。她从宁波竺洲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回到定海女小任教。她立志为教育事业而奋斗,曾将名字改为金志成。
1924年,金维映到上海大学看望同学,经介绍认识了瞿秋白、项英、杨之华等共产党人。与这些人的交往,使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她过去曾崇尚“教育救国”的思想,认为女子的解放在于接受教育达到自强自立。现在她认识到,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要彻底改变命运,必须进行革命。经历大革命洪流的洗礼,金维映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于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金维映秘密加入共产党后,积极参与国共合作,在舟山的定海城区等地开展工人运动、盐民运动,被誉为叱咤风云的“定海女将”。在她的影响下,全家人都成为革命者或者革命群众。由于金荣贵管理的公民招待所被特许夜间不查夜,因此从1926年起,中共宁波地委派到定海建党的一些领导人,经常住在那里。金荣贵总是想法设法保护他们,为他们守门望风。公民招待所成为党组织的秘密据点,工农运动的许多文件都放在金荣贵那里,由他保存。
金维映在岱山岛发动工人运动时,面对当时高亭镇上有些人心存顾虑不敢加入工会的情况,她首先动员自己的亲友入会,她的弟弟金水定也成为工会骨干。到岱山发动盐民运动时,她也是先找弟弟了解情况,经弟弟介绍认识可靠能干的盐民骨干。解放后金水定回忆,当时常常向姐姐汇报工作商量对策。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金维映离开定海。国民党反动派抓不到她,便到公民招待所抓捕了金荣贵。金维映的母亲和弟弟得到父亲被捕的消息,从岱山赶来。不料母子二人一进门,就被埋伏在公民招待所的敌人团团围住,全家人都被投进了监牢。后来,金维映的母亲先被保出,弟弟在关押一个多月后也被保出。被押往杭州的金荣贵死不开口,敌人见榨不出什么油水,才将他释放回定海。
家人虽然全部释放出来,但此时定海已没有他们的安身之处,他们的住处已被查封,所有东西被洗劫一空。因为金荣贵的革命行为,老板不得不解雇金荣贵,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只好迁回镇海老家。
金荣贵一家人在镇海安定后,日夜为转移到外地的金维映担忧。不久,就打听到金维映在宁波被捕了。闻讯,金维映父母心急如焚,倾家荡产打造一尊金佛送人,终于将她保释出来。金维映出狱后,被家人接回镇海老家。
自从女儿参加革命后,金荣贵也接触了革命道理,他知道,只有共产党才是穷人的救星。所以得知金维映要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时,尽管金荣贵很是不舍,但仍然亲自送女儿出门。
1930年在上海工作期间,金维映把弟弟金水定叫到上海做联络工作,经常安排他骑自行车去送文件,听革命道理。为了工作,金维映又把母亲叫到上海住机关,除了为大家煮饭烧茶外,还看门放哨。母亲虽没有文化却足智多谋,办事机敏果敢,她知道女儿从事的是要杀头的工作,仍义无返顾地走进女儿的工作圈子,直接为革命做贡献。
英姿飒爽女书记
1931年金维映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即被任命为中共于都县委书记,她和李坚真成为中央苏区仅有的两位女县委书记。在当时,县委书记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不但要求政治水平高,工作知识面广,而且工作量极大,党、政、军、工、农、商、学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靠县委书记运筹帷幄,对县委书记的综合素质要求是很高的。中央把金维映放在这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上,是对她的高度信任和充分肯定。
金维映没有辜负中央的重托,不只妇女工作、扩红等擅长的工作做得好,支前、反“围剿”等传统的男人工作也丝毫不落人后。虽然条件艰苦,工作繁重,但金维映总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干净利落。她经常穿着钟爱的列宁装,戴着八角帽,扎着腰带,打着绑腿,英姿飒爽,成为苏区一道美丽的风景。
于都虽然是苏区县,但许多村还是白色,经常发生赤白之间拉锯式的游击战。严酷的战争环境需要领导干部具备过硬的军事本领,金维映努力提高自己的军事作战能力,练习纵马飞驰和百步穿杨的枪法。每天早晨,她早早起来,骑一匹枣红色马,在乡间小路上练骑、跑操。
乡民曾多次看到金维映迎着朝阳,腰里挂着盒子枪,威风凛凛地策马飞驰。每当她骑马跑过来时,许多早起干农活的村民都会驻足观看。跑过之后,她就开始练枪法。她练枪的地方很特别。离她住处100多米的地方有两棵参天大樟树,每棵有三四人合抱那么粗,她在树上用石灰画了个圆圈当靶子。有时她骑在马上打枪,难度很大,因为骑马时颠得厉害,很难瞄准。有时不骑马,站在那里练习瞄准射击。经过勤学苦练,她的枪法很好,曾带头活捉过岭背区的反动武装分子。四乡八方都纷纷称赞她是巾帼女杰。
1932年5月,金维映率领新编独立团奔赴赣县江口,直接参加第四次反“围剿”。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反击国民党正规部队的战斗,场面很大,战斗也很激烈。她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火线与敌人展开英勇的战斗。子弹呼啸着在她的耳边飞过,炮弹在不远处炸响,不时有战士负伤、牺牲。
警卫员一次次拉着金维映,要求她下火线,她抖抖压在身上的土块,摆摆手生气地说:“不要多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不打前阵谁打前阵!”此时,她不只是花木兰式的女战士,还是统率几千人的女指挥官。经过四天三夜的激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轮番进攻。
在中央苏区任县委书记期间,金维映虽然工作顺利,个人生活方面却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和邓小平结为夫妇后,尽管两人聚少离多,分别在不同的苏区县工作,但两个人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一有时间就会相互探望。
1933年,邓小平在江西反“罗明路线”中受到无情打击。作为邓小平的夫人,金维映的压力非常大。后来,他们离婚了。同年秋冬,金维映调入中央组织部工作,任组织科长。在朝夕相处中,她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互生好感。1934年,金维映和李维汉结婚,婚后不久即匆匆动身参加长征。1936年,金维映在陕北生下唯一的儿子李铁映。
亮丽歌声永相随
金维映从小喜欢唱歌,她出生的高亭港里舟船云集,每当这些船出海时,起篷号子总会传到她的耳朵里,这就是她最初的音乐教育。作为海的女儿,她天生爱唱海岛的歌,学会了许多海岛歌谣。参加革命工作后,她又学会唱客家山歌和其他革命歌曲。对她而言,唱歌不仅是她的个人爱好,抒发个人情感,也成为她做群众工作的有力武器。
在岱山岛发动盐民斗争时,金维映秘密走村串户,下盐田,上滩头,每到一个地方就把盐民集中起来。有时,她和盐民们以筷击碗,唱起一首《盐民苦》的歌谣:“一根扁担挑勿弯,两只脚底磨沙滩。一年三百六十日,祖祖辈辈挑盐担。起早摸黑出门槛,十里沙滩走往返。阿拉穷人无靠山,挑来挑去是烂泥山。苦卤苦水苦扁担,苦屋苦路苦海滩。行行呒没介个苦,两行苦水拌苦饭。”
唱着唱着,盐民的妻子在一旁抽泣起来,金维映的眼睛也湿了。她趁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盐民的觉悟,唤起盐民的斗志。很快就成立了岱山盐民总协会,统一领导全岱山的盐民运动。
在上海开展妇女工作时,金维映走门串户拜访女工,为了拉近和女工的距离,启发女工对女人地位的思考,她和大家一起唱《女工苦》的歌:“踏进工厂门,自由被剥尽。老板心太狠,我们像犯人。黑心领班女工头,凶暴又残忍。做工稍不慎,打骂重罚甚至赶出门。”通过唱歌,金维映很快和女工们打成了一片,为做好妇女工作、成功筹划丝厂女工罢工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中央苏区时,金维映很快被山味浓厚、清脆悦耳的客家山歌深深吸引,每到闲时总会情不自禁地唱上几首,工作中也常教妇女们用山歌来鼓励劝说人。女人们在夜里做军鞋支前,金维映也和她们坐在一起做鞋,边做边唱:“千针万线一颗心,双双军鞋送红军,脚穿军鞋上前线,彻底消灭反动军。朝织鞋,暮织鞋,织鞋不为上街卖,送与前方战士们,冲锋杀敌多轻快。”工作闲暇之时,金维映还喜欢教儿童团的孩子们唱歌。
长征过草地时,非常艰苦,但金维映和她的战友都很乐观,只要有休息的时间,就想办法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唱歌或是讲故事。轮到金维映时,她先是讲自己的家乡舟山,描述大海,接着就唱起撑篷调,那激昂的歌声再一次鼓起大家的勇气和希望:“一片风篷啰一股啰风,二片风篷啰二股啰风,啥人会撑倒风篷,扭转乾坤是英雄 。”
寻寻觅觅半世纪
为了革命工作,金维映曾数度改名换姓,从舟山转战到上海、江西、陕北、苏联,与家乡亲人生离死别,天各一方。在她的家乡、在她的亲人中,大家一度只知“金爱卿”,却不知“金维映”即“金爱卿”。为此,她的家乡、她的亲人苦苦寻找了她几十年。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金维映被迫离开定海,从此再未踏上家乡的土地。1931年她离开上海,奔赴中央苏区,离家乡和亲人越来越远,此生再未相见。离开上海前夕,金维映的弟弟曾到上海,想请她回家乡参加他的婚礼。她仔细问了家中的情况,特别问了婚礼的准备情况,哽咽着对弟弟说:“我要到一个新地方去工作,你的婚礼阿姐不能参加了,我准备了20元钱给你办婚事。以后我会常常来信,也会给家里寄钱用的。只是,你要担起照顾父母的担子了。”
金维映奔赴中央苏区后,难忘父母养育之情,经常给家里写信,在自己的生活极端困苦的日子里,不忘辗转着往家寄钱寄旧衣。开始长征后,她彻底和家乡断绝联系。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局势相对稳定,金维映和家人恢复联系,每个月给父亲写一封信。1938年春金维映到苏联后,音讯再次中断。
1941年底,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飞机轰炸莫斯科时,金维映牺牲。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包括她的丈夫李维汉都不了解她的确切籍贯,更无从谈起与她的家乡和亲人联系。解放后,李维汉几次请浙江的同志帮助查找,看金维映家里还有什么人,都没有查到。
与此同时,金维映的家人也一直在寻觅她的下落。金维映离开家乡后,父亲金荣贵非常想念女儿,他的脑海里总留着女儿最后一次离他而去的情景。1938年,金荣贵逝世,弥留之际还在念着他的女儿,再三嘱咐儿子金水定一定要找到姐姐。
宁波解放的时候,金水定带着妻儿走上街头,穿梭在如潮的人流中,他们在一队队过往的解放军中,寻找着亲人的身影。可是脚站肿了,眼睛望穿了,仍然没有见到金维映的影子。姐姐没有回来,让金水定牵肠挂肚一生。后来,他向《人民日报》写信,向康克清写信,都没有得到消息,寻觅不到姐姐的下落。
尽管母亲远赴苏联时李铁映才两岁,也许幼小的李铁映心中并没有母亲的印象,但长大成人后的李铁映仍然无比想念母亲。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寻找线索,几度奔赴金维映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踏遍了江西老区的山山水水,在莫斯科郊外的这块埋葬着母亲的大地呼唤:母亲,你在哪里?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经过多年的寻觅,李铁映得知母亲是舟山人。1983年,他曾亲自到过舟山,看过母亲出生的小屋和读书的小学,亲属下落也有些线索,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1987年李铁映再次到浙江出差,吩咐秘书去宁波各处仔细查查,看家里有没有人?强调要有可靠的证据。经过实地调查,确认金维映的父母早已过世,弟弟金水定四处漂泊躲藏,后来到了镇海。得知舅舅还在人世,李铁映立即赶到镇海,见到舅舅,失散多年的金维映姐弟才得以另一种方式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