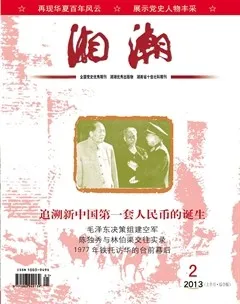女八路赵建华的青春苦旅
2013-12-29李伶



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战士责任重,女兵路更艰。她们的付出尤其令人震撼。这里要记载的就是昔日的女八路赵建华的青春苦旅。
善良稚嫩,二八女勉强定终身
1939年,赵建华在延安荣军学校二大队担任文化教员。大队政委胡子明看上了她,但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爱恋,就将组织上的暗中撮合和盘托出,说是上级将她“分配”给他了,问她何时举行婚礼?
会有这样的事?她找了好朋友了解真相,摸清了组织上的真正意图:
延安男女比例18:1,军婚成了大问题,虽说有“258团(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才能成婚的规定,但伤残红军军官仍然在自由恋爱中失去了竞争力。为给他们创造条件,荣军学校领导特地向上级要来了一批女教员、女医生,先在领导层里初拟了一份“鸳鸯谱”。把赵建华安排在胡子明属下当教员,就是想促成这桩婚事。
赵建华为难了:刚刚入党,不能违背组织上的意愿。出于善良的愿望,16岁的赵建华勉强定了终身。人们开玩笑,说她是“分配的媳妇”。
尽管她在婚后生活中“努力改造思想,培养无产阶级感情”,但仍然无以弥补情感之欠缺。于是,她鼓起勇气向荣军学校领导提出了离婚请求,尽管已有身孕。
荣军学校政治部主任陈振亚说:“现在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党中央已经决定,我们6个残废(当时称残疾人为“残废”)人马上去苏联治病。你也跟去,有个照应呀!至于生孩子,在那儿生也一样,人家是社会主义,条件比延安好!”
“家属里就去我一个?”
“凡有家属的都去,我们思齐她妈也去,把思齐也带去,还有谢江廷家属,都跟去!这下你放心了吧?”
听说张文秋一家也去苏联,赵建华打消了顾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赵建华和另外两名年轻的媳妇,外加两名勤务兵,各牵一匹马,驮着6名伤残军人,不紧不慢地向西而去。领队的便是陈振亚。
思齐姑娘像只快乐的百灵鸟飞前跑后,有时还拽着马尾巴跟随而行。
艰苦跋涉到兰州。一等两个月,一架小型苏联运输机将他们秘密载至迪化(今乌鲁木齐),适遇希特勒向苏军猖狂进攻,一场恶战席卷整个欧洲,也影响着亚洲的战事。苏联军队自顾不暇,一时再无可能像以前那样大批接待中国的来客。苏联去不成了,他们只得在边城迪化听天由命地等待时机。
事出意外。一天,陈振亚不幸捐躯。此时,还想离婚的赵建华只得去找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
陈潭秋在新疆化名为徐杰,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谙政治,识风云,也颇通情爱。他听了赵建华的一番含泪申诉后,唤起了这位兄长的同情和理解:“小鬼呀!我理解你,但我这个办事处不解决离婚问题,回延安再说吧!眼下,苏联去不成,延安也回不去。难呐!好在你把孩子生下了。想学习,好嘛,你去迪化女中念书吧,毛泽民的爱人朱旦华在那儿任教务主任,我负责介绍。”
她不再提离婚了,并及早地给儿子民平断了奶,背着书包去迪化女中上学了。人们风趣地称她“中学生妈妈”。她听了嫣然一笑,仍然早出晚归忙学业。幸好她貌美而年轻,不知底细的人谁也看不出她当妈妈的“资历”。
铁窗岁月,吞下黄连吐出蜜
密布的阴云翻开了恐怖的日历,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早就料到的事件发生了:深夜,一群士兵端着枪,把驻迪化的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连同家属小孩统统“保护”起来,分批押上汽车,拉到迪化城北山坡上的八户梁软禁。
1943年2月7日夜,警察又来捕人了,瘸子也不放过。他们拽着胡子明朝外拖,赵建华母狮般地扑上去,拉着自己的丈夫不让走:“他打鬼子丢了一条腿,要人照顾呐,打鬼子也有罪?把我也抓去吧!”
她的话有理有力。警察扭转头来,放慢了脚步。
她的儿子民平两岁多了,吓得直哭,“爸爸”、“妈妈”,哭喊不止。
不知是泪水触动了警察的恻隐之心,还是事先就是这样的安排,警察改口道:“那好,一块儿进去!”
赵建华在丈夫耳边轻声嘀咕:“大难临头,我不会扔下你,要设法关在一起!”
分配监号了,小个子警察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胡子明的名字。赵建华主动站出来,毋庸置疑地搀扶着丈夫走进了指定的监号。然后,就去搬铺盖,提衣箱。
警察看看这个漂亮而伶俐的媳妇,望望那个老实巴交而又断腿发臭的胡子明,似乎想说什么。
众人连忙上来求情:“这么个残废,还有孩子,成全成全吧!”
“那就暂时住一起吧!”
盛世才为政,阴险狡猾,处处讲新招,连监狱前边都冠以“模范”、“仁慈”之类的美词。轮到赵建华过堂了,她被“请”到警方办公室,让座、倒水,客气地走完过场,便问“暴动”之事。
赵建华哈哈大笑道:“真可笑,大批共产党来新疆,这是盛督办一片盛情请来的,四菜一汤招待我们。我陪丈夫去苏联看病逗留迪化,也是盛督办允准的,怎么成了搞暴动反对他?你们也不想想,凭着这批秀才、残废,还有家属小孩,能搞暴动吗?”
审讯的警察见她答得天衣无缝,便以关心的口气说:“不谈那个,谈谈你自己吧!”那警察贼眉鼠眼地盯着面前这位美丽的少妇,似很惋惜地说:“好一朵鲜花插在屎粪堆上呀!”话到这里,他的语气立刻缓和下来,“我们听说啦,你是分配的媳妇,跟那瘸子是勉强夫妻,早就想离婚,共产党不允许,是不是?”
“警官说到哪里去了?我们明明是夫妻关系,怎么扯到党的关系上了?你们的夫人跟你们不也是这样吗?人嘛,总得讲些道义。我们一直是恩爱夫妻,偏有人爱搬鬼话,说我们如何如何,要是那样,我们怎么会有孩子?要是那样,我怎么不借机逃脱?警官可不要听信那些风言风语。”
这番话,噎得警察无以答对。
赵建华在监狱里十月怀胎,第二个孩子平安出生了,是个女孩,叫什么呢?
屋檐下春燕呢喃,不觉叫人心寒,燕子呀,天大地大任你飞,为什么偏到这苦海无边的监狱里筑巢呢?莫不是陪伴囚徒度寂寞?这苦命娃就叫“狱燕”吧,愿你长上翅膀,早日飞出牢笼,飞向延安!
奋起自救,创造奇迹泣鬼神
1944年春,卡车顶着西北风在迪化街道上奔驰,车上载着刚走出牢房的赵建华等12人,12人的基本情况是:两名“分配”给伤残红军的媳妇各自领着两个孩子,加上5位伤残红军,占了车上人数的一大半。
那个连眼睛也睁不开的老妪年龄最大,是我党农民运动的先驱苏兆征烈士的遗孀王瑶友。人们敬重她,老老少少都亲昵地称她苏妈妈。她从苏联治病归来,卡在迪化坐了大牢。
那位年轻的妇女叫晓云,又称肖云,东北抗日民主联军被打散,她越境入苏,在异国的饥寒和辗转煎熬中,她带着女儿秀灵入新疆返回祖国,闯进了盛世才的牢笼。
那对纯粹东北口音的老两口,谁也叫不出他们的姓名,都习惯地称他们爷爷、奶奶。东三省失陷,他俩奔命新疆,适遇中共某领导人添子胖胖,“奶奶”便成了他家保姆,“爷爷”则靠一把胡琴混吃街头饭。后来革命需要,胖胖的父母一个去苏联,一个回内地,扔下胖胖无人抚养。“爷爷”、“奶奶”伸出友爱的手,拯救了一条危如坠崖的幼小生命。善良给他俩招来了祸患,共产党遇难,相依为命的爷爷、奶奶和孙子也成了要犯,一同入狱,坐了4年大牢。
12人被安置在迪化贫民安残所的一座大屋子,与先期到达的另外5位伤残红军会合,组成了一个17人的大家庭。这个大屋子里几十张单人床杂乱无章地挤在一侧,床上的铺盖肮脏不堪,像垃圾堆里捡来的。屋里空气格外污浊,霉烂味、汗臭味实在令人作呕。
双目失明的谢江廷一阵破口大骂,4个瘸子愤怒地敲打着拐杖,这才迫使安残所所长发了慈悲,分给这个17 口之家的“共党户”两间住房:男一间,女一间。
赵建华和另外两名年轻的媳妇成了17口之家的“贤内助”。
下午4点钟,贫民安残所开饭了,每人两个又黑又硬、霉味熏鼻的高粱面窝窝。孩子们饿得扛不住了,拿起来就咬,吃着吃着,从里面拣出一条蛆来,民平和狱燕不想吃了,偎依着赵建华,怯生生地说:“妈,咱们回去吧!”
“回哪儿去呀?警察把咱们从监狱赶出来啦,从今往后,这儿就是咱们的家,记好了,全家17口!”赵建华半含泣声地安慰她的孩子。
苏妈妈抚摸着饿得又黄又瘦的孩子们,心疼地说:“我这把老骨头了,饿死不要紧,这些孩子要活下去,将来靠他们支撑天下!想个办法吧,我箱子里还有几件衣服,从苏联带回来的,拿去卖掉吧!”在她的带动下,各人都捐出了稍微值钱的衣物。
曾在红军里当过财务科长的罗云章豁然开朗地说:“我们不能坐吃山空。将这些衣服变卖成本钱,摆个香烟摊,活水长流不好吗?”
迪化西大桥上出现了奇迹:5个一等伤残红军军人摆起了香烟摊。他们之中,一个双目失明,一个双腿截肢,其余3人皆缺一条腿,5个人合起来只有8只眼睛5条腿。
来来去去,一幅何等动人的场景:失去双腿的罗云章背着一箱纸烟,双目失明的谢江廷发挥双腿俱全的优势,背着罗云章,像传说中瞎子背瘫子那样,一个指路,一个迈步,走在最前边。其余3人夹着木板或板凳,各掖一根拐棍朝前支撑。
他们赚钱了,除了改善“共党户”的伙食,还有了积余,怎么花?搭救难友去!他们买了400多斤熟肉和上千斤炒面,雇了两辆牛车,把心意送进了牢房。
狱中200多位难友及其家属,是从多种渠道汇集新疆的,相互间本不太熟悉,这下子要一一写出他们的名字,而且多数都用化名,5位伤残红军拍空了脑袋也没拍齐。赵建华召集几个孩子及他们的妈妈、奶奶们回忆伙伴们的姓名。孩子们真聪明,不但想出了名字,还在思齐、邵华姐姐的炒面里塞进发卡。后来又把加工成熟菜的几百斤灰灰菜送进了牢房。
监狱里的同志接到慰问品后,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狱中党的负责人马明方(后任中共东北局第三书记)代表全体同志传来书信致谢:“你们照顾好自己就很不容易,还为大家尽了这么大的力,我代表狱中同志谢谢你们。不要再送东西来了,这里再苦也能熬下去,最要紧的是加紧向家里联系……”
摆脱困厄,断线的风筝找回了家
有一天,赵建华在迪化的省立第一医院意外地遇见了迪化女中的3位女同学。惊喜邂逅,各道现状,3张笑脸就像朝霞里的3朵鲜花,双手拢成一个小型话筒:“告诉你,我们要去解放区!”
那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叫张玉贞,她抱起狱燕,轻轻地对赵建华说:“这些日子,天天盼你们来接头,今天总算盼着了。国共两党正在重庆会谈,周恩来为营救你们出狱,等着你们的消息,特别是牢里人的名单。赶快写出来,明天中午,你到西大桥东头的趣兴酒店等我!”
像阔别多年的游子,忍着千辛万苦在给慈母写信:
党中央、毛主席:
我们是赴苏治病而被卡在迪化的5名残废军人。冤狱4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惨遭杀害;乔国桢、关茂林狱中病故;徐梦秋、潘同、刘希平等15人叛变,其余100多名好同志仍关在第二、第四监狱始终坚持斗争,争取回延安。
名单附后。
信的正文写好后,5人依资历签了名。
赵建华接过信和名单,叠了又叠,严严实实地缝在一双布鞋里。
接头的时间就要到了,赵建华穿着孔雀蓝大襟上衣,挎着篮子,装作挖野菜的样子,来到西大桥香烟摊前。摆摊人将拐杖立在摊位上,这是安全信号。她向身后担任保护的年轻媳妇晓云使了个眼色,便向趣兴酒店走去。
店里有几个男顾客正在埋头苦吃,并不关心周围的一切。肩负使命的那3位女同志,正在另一张酒桌上谈论着什么。领头的张玉贞化了妆,穿着入时的紧身旗袍,外加高跟皮鞋,一下子把这个天仙般的美女重心提高了一大截。她见赵建华来了,老远就打招呼:“大姐呀,我们等你老半天啦,过来坐呀!”
“二妹,你真的要回家去吗?”赵建华从容又含蓄地扯上了正题。
“对,我明天就动身!”张玉贞点点头,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芒。
“唉,这年头手头紧,没什么孝敬老人家,纳了这双鞋,你给俺娘带去,请她老人家放心。”赵建华特意指了指鞋中的要害部位。
“大姐手真巧,娘见了定会高兴的。”张玉贞接过布鞋,用食指在鞋子里做了个心领神会的小动作。
赵建华动情地说:“请告诉家里人,离家7年来,天天都盼着回去,可惜,身不由己呀!”
目击者谁也没曾想到,这场情真意切的姐妹话别,关联着近200人的生命呀!
这封信辗转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上,周恩来指示中央组织部调查情况。在摸清情况后,周恩来在国共会谈中直接与蒋介石交涉,指出其“释放政治犯不彻底,光迪化监狱就有一二百名政治犯至今在押”。这时,西北五省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将军亦向蒋进言,蒋才勉强同意放人。
张治中秘密召见了他的师娘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四监女囚),说他答应过周恩来,营救这批共产党员出狱。营救名单已开出来了,却没有安残所17名难友。
5个“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的伤残红军每天一封信,向新疆省政府要求回监狱,集体回延安。送信的任务自然落在了赵建华身上。她高跟鞋磨去了一大层,17名男女老少,终于回到了监狱。
囚笼打开了,约200名政治犯包括安残所的17名难友获得了人身自由。愿回延安的131名受难者分乘10辆美式带篷卡车,归心突突地离开了迪化,向延安进发。
经过火焰山时,因酷热缺水,狱燕再也没有醒来,赵建华伤心欲绝。
百子归来,延安一片沸腾。毛泽东面带笑容,在中央党校跟大人小孩一一握手。
当毛泽东和赵建华握手时,她很想说说心中的感受,但在这种场合,她仍然是那样柔顺,除了激动的泪花,别无流溢。
婚姻,宛如河蚌吃进了沙子,有的将沙子变成了珍珠,有的则把沙子吐了出来。赵建华与胡子明终于“沙蚌分离”了。他们的儿子民平被送进了朱德夫人康克清领导的延安保育院。她则打起背包,马不停蹄地奔向东北解放战场,成了白衣战士中的一位基层领导。其后,她与部队干部肖永汉结了婚。
后来,赵建华更名赵艺雯,一直在长沙市医疗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又添了4个孩子,外加炼狱归来的胡民平,共5个孩子,皆恩爱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