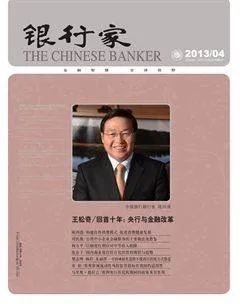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改变了什么
2013-12-29周莉萍
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最早可追溯到1892年纽约股票交易所清算中心的建立,发展于20世纪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盛行于20世纪后期。当前,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已经遍及全球各类证券交易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典型的中央对手方机构包括美国的CME清算公司(作为主要的中央对手方机制,为股票、固定收益证券、场外交易OTC衍生品和外汇交易服务)、欧盟的Eurex清算公司(一家盈利组织,为欧盟市场所有的证券交易提供中央对手方服务)、英国的LCH清算网有限责任公司(英国LCH清算网集团的子公司,为股票、商品、固定收益证券、衍生品和回购提供中央对手方服务)、加拿大CDS清算和存款服务有限公司(一家依托FINet清算平台运行的非盈利性组织,是加拿大CDS市场的主要中央对手方)等等。
次贷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各国监管当局对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的普遍关注。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提出,在2012年底之前实现标准化衍生产品都通过交易所或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并通过中央交易对手方来进行清算。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已经被视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
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到底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能否达到G20提出的降低系统性风险的要求?本文试图回答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以理清对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的全面认识。
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的核心要义
在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产生之前,较为流行的是传统的双边清算机制。即买卖双方成交后,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清算、逐笔全额交割。其中,第三方机构不承担交收担保义务,双方各自都需承担对手方风险。单项交易的信用风险很容易产生传染风险,引致系统性风险。由此,便出现了有可能规避传染风险的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
中央对手方的本质是以中央对手方为核心的多边清算机制。核心内容包括多边净额清算(multilateral netting)、合约更替(novation)和担保交收(guarantee)。核心功能是降低双边结算的对手方风险和传染风险,提供市场流动性,保证证券结算的顺利进行。
实施中央对手方机制实现双赢、多赢的前提条件是,清算的金融合约必须标准化、中央对手方机构具有充足的市场流动性。首先,标准化能增加交易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任何私人定制的个性化金融产品,都因交易规模不高而不宜实行中央对手方清算。其次,中央对手方充裕的流动性从何而来?当前,大部分中央对手方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是内部资金,包括清算会员的保证金和资本金、中央对手方自身备付的担保金和资本金。在某一个对手方出现违约时,首先动用的是该交易对手的保证金和追加保证金,其次是全体清算会员的保证金,再次是中央对手方的担保资金,最后是会员的资本金和中央对手方自身的资本金。在外部资金方面,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中央对手方机构直接注册为银行,如欧盟地区的German-based Eurex Clearing AG和France-based LCH.Clearnet SA。它们可以直接向中央银行拆借流动性,获得紧急流动性支持。也有部分欧盟国家的中央银行直接为中央对手方清算机构提供隔夜流动性支持,如瑞典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由于中央对手方清算的国际性,大部分国家的中央银行并不愿意为在本国注册的全球性中央对手方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可执行的跨境合作和国际协调是中央对手方机制完善的方向。
在风险分担方面,中央对手方承担信用风险,即合约顺利结算的风险,但不承担市场风险,即合约价格波动的风险。中央对手方是所有交易对手的担保方,除了要求对手方保持合理的经济资本以缓冲风险,其自身则通过保证金制度应对违约风险。保证金一般要求是最安全和最具流动性的抵押证券,不同的中央对手方机构对此要求不一,如北美的中央对手方对抵押品的要求普遍高于欧洲,只接受特定条件的抵押品。通过不断调整保证金要求,中央对手方得以囤积高质量的抵押品。一方面,抵押品可用来应对市场冲击;另一方面,中央对手方机构也可以再次盘活利用抵押品,并从中获利。
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
从市场自身发展角度来看,OTC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催生了对中央对手方机制的需求。全球OTC衍生品市场呈现继续扩张趋势,且系统重要性不断增加。在规模方面,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全球OTC衍生品名义总额达到639万亿美元,比2011年底下降1%。其中,利率合约和信用衍生品名义规模都持续下降,而外汇合约规模增加了5%。在结构方面,OTC衍生品市场的主要交易工具仍是利率衍生品。全球各国基本都已经实现利率市场化,规避利率风险是市场交易主体的长期需求。因此,OTC衍生品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紧密,系统重要性有增无减。
OTC衍生品市场具有典型的定制交易、个性化交易特征,标准化程度低,尤其是规模和范围较小的衍生品。据IMF统计,2009年之前,仅有45%的OTC利率衍生品由全球中央对手方机构——英国的LCH进行清算,其余大部分OTC衍生品仍是双边结算。OTC衍生品市场的双边交易结算容易产生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传染风险,而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能降低金融市场交易的负外部性、将其内部化,改变双边交易结算的弊端。从而能保持OTC市场的稳定,这也是G20极力推崇中央对手方机制的根本原因。
具体原因包括:第一,匿名交易,信息不对称,增加交易机会。第二,直接和实力强大的固定中央对手方交易,直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第三,将分散的信用风险集中于实力强大的中央对手方,降低了所有的对手方风险和传染风险。第四,净额结算,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提高资金分配效率。多边净额清算机制包含多个双边清算,并将双边清算的净额信息进行汇总,从而减少无效的交易次数和规模,以达到用较少的资金支撑最大规模的支付活动。这从整体上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交易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第五,完善交易信息,增加市场交易透明度。
从金融监管实践来看,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是一种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监管工具,在发达经济体倍受政府监管部门的青睐。OTC衍生品市场原本不在各国监管范畴之内,不涉及监管问题。但是,OTC衍生品市场相关产品如CDS,与受监管的证券交易以及实体经济紧密相关,其风险溢出效应终会波及场内市场。因此,次贷危机之后,各国当局更加关注如何降低OTC市场的传染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中央对手方机构主要受中央银行、证券监管和衍生品监管当局的监管。通过中央对手方保存的OTC衍生品清算价格和合约交易信息,监管者可以掌握第一手的市场信息,监测OTC市场的发展动向。由此,中央对手方机构也间接成为金融市场监管的工具。
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的局限性
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能直接减小双边交易的对手方风险,却未必能真正消除系统性风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该机制存在典型的“赢家诅咒(winner’s curse)”。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分散的信用风险集中于自身,虽降低了对手方风险和传染风险,但又滋生了新的风险。中央对手方管理信用风险的主要方式是吸收高质量的证券作为抵押品。问题是,任何所谓的高质量证券就是准货币,即能及时、以较高价格变现,其质量具有时效性。金融危机史证明,具有逆向选择倾向的金融市场容易突然面临流动性枯竭。匿名交易的中央对手方机制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骤然枯竭时,高质量的证券也会遭到非理性抛售,交易信心的丧失进一步降低证券交易价格。此时,中央对手方手中持有的大量优质证券并非高质量。
第二,标准化会削弱市场力量。标准化与个性化对立。一方面,中央对手方交易机制提高交易效率的前提是,与所有对手方进行的交易尽可能的标准化,从而降低个性化交易的成本。另一方面,标准化可以保证可控性和安全性,但会扼杀个性化市场需求与供给的活力,削弱市场内生的创新力量。
第三,信息不对称的负面效果。信息不对称在提高中央对手方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存在负面效果。一方面,保证金制度的引入,使得其交易对手只要有很小比例的抵押品就可以进行交易。中央对手方无法掌握其全部的资产负债状况,大部分没有能力交易的机构都被放入中央对手方交易体系。另一方面,国际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直接导致其进入门槛不断被降低。原本不可能成交的双边交易,由于匿名交易和低门槛而进入中央对手方交易。原本想通过标准化和其他机制设计提高交易对手质量,中央对手方机制最后的交易对手中却存在低质量机构。
第四,中央对手方也面临风险。中央对手方会面临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外部风险是,其对手方机构如果破产违约,中央对手方就面临违约风险。内部风险包括法律风险、管理风险、操作风险及机制设计所致的系统性风险。以管理风险为例,中央对手方机构一般都是某一大型金融集团或清算机构的分支机构。依托有实力的集团,中央对手方才能保持充裕的流动性和高效的清算。目前,据IMF统计,中央对手方机构一般都没有独立的董事会等决策机构,内部治理水平不高,存在隐患。以系统性风险为例,如果没有严格的保证金制度、抵押品管理制度和再抵押融资机制,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会导致无担保的信用创造,导致无追溯权的违约风险,最终成为系统性风险。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各国也出现过典型的中央对手方破产案例,包括1973年的法国Caisse de Liquidation清算所,1983年的马来西亚Kuala Lumpur商品清算所,1987年的香港期货交易所。另外,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也曾数次遭受重创,接近破产。2008年次贷危机中,LCH,CME和Eurex等国际中央对手方,也因其主要交易对手(如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的破产而面临措手不及的违约风险。
综上,即便是中央对手方,也面临多种风险,其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亟待加强。必须有完整的风险缓释机制和措施,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才能在提供有深度的流动性和便利的交易机制时,同时降低自身风险。才有可能优越于双边清算机制,使全球清算资金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增加社会福利。国际社会不仅提倡在OTC衍生品市场推广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也试图强化对该类机构本身的跨境协调和监管。
结论
次贷危机后,国际社会采取了多项监管措施缓解系统性风险,方式之一是增强金融基础设施吸收风险的能力。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已经被列入金融基础设施范畴,成为一种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监管平台和监测工具。当前,国际社会大力提倡在货币市场交易(如回购等)和场外衍生品交易(如期权、互换等)采用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以减少OTC市场上双边交易失败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降低风险传染所致的系统性风险。
从应对金融危机的短期视角来看,中央对手方能改变双边清算的不利影响,如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增加市场流动性;保存OTC市场合约信息,增加交易透明度,辅助实现监测功能;消除双边清算的对手方风险等等。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符合市场效率需求,有利于尽快摆脱金融危机,使OTC衍生品市场变得更加稳健。
但是,中央对手方交易机制存在典型的“赢家诅咒”效应。理论上的完美不能完全遮挡实践中的局限性。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必须有更加合理的抵押品管理机制、风险相互化机制、流动性支持机制和跨境合作机制等,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