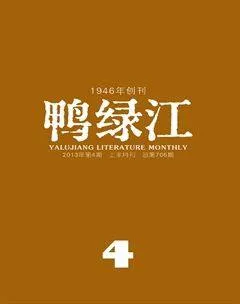熨帖着乡土生命的疼痛与温情
2013-12-29刘恩波
刘恩波,1968年出生,现居沈阳,供职于辽宁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辽宁作家协会特邀评论家,辽宁文学院客座教授。现主要致力于中外戏剧名家、史铁生和黑泽明研究,兼及现当代文艺作品、现象和思潮评论写作。
在城市里生活多年的习惯有时候很容易让人淡忘自己的来路,那浓郁的乡土气息、简单质朴的乡村风情、那乡原里忘我劳作的农民兄弟姐妹,还有土坯炕、草垛、喜鹊窝、房檐上结的冰棱,以及清晨抑或傍晚家家户户烟囱里冒出的炊烟,丝丝缕缕,伴随着晨曦落日,曾经飘散过我们记忆中恒久的惦念和牵挂。
然而,现在,时过境迁,故土和故乡都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也许不是心的有意疏忽冷漠才造成人与它们的难以弥合的空隙,实在地说,是历史文明正在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后工业化脚步乃至商业浪潮的席卷,无形中使得乡土社会日益面临瓦解消融,成为点缀着轰轰烈烈行驶着的都市欲望号街车的某处临时抛锚之所。
乡村的原始格局的改观随着一大批农民工的进城而日益变本加厉,乡村的劳动力资源在急剧萎缩,土地也仿佛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和弹性。“空巢家庭”、“留守儿童”现象的出现,一时间成为整个社会舆论热议的焦点。正如某些预感到精神危机存在的人类学家所言,“一个社会在面临外来的超级文明时,会有文化休克的现象。”如果说乡土社会遭遇到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巨大裹挟和洗礼,从而有可能变得奄奄一息走向衰落,要么通过某种适当的形式脱胎换骨重塑自我,大概都是它的悖论式的生命境遇的必经之路。
而艺术和文学对于古老乡村文明的写照、捕捉、定格和挽留又会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不平静的审美旅程呢?
文学艺术就其本质来说当然是务虚的,也只能作“无用之用”,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巨大差别及其由此带来的精神空缺,就如同作家余华在一篇文章里做过的对比性反差的描述:闭塞山村的孩子最大的梦想是能买到一双耐用的球鞋,而大都市的同龄人则可能已经乘坐波音747环球漫游了。梦的起点显然是经济基础——而文艺说到底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愿望的某些替代性满足,它能够为我们的想象力和经验世界提供心灵的疗伤和休憩之所,可以整合我们麻木痛苦的神经中枢,起到释放减压舒解的功能。
就此而言,艺术和文学与乡土文明的对话的确有赖于疏导精神痛楚和提供温情抚慰这两种直接关涉到人的肉身和心理的双向建构。
毋庸置疑,人与故土的分别和分离,人的返乡和回眸,人的茫然寻找和在失落中的守望,其实构成了人和乡村社会故土亲情的无法割舍的内在连结。
而面对浩瀚无边的文献典籍艺术影像,这里充其量只能择取本人感兴趣的若干作品,具体描绘一下它们带给阅读者的真切感染、疏导和升华。借以勾勒聚焦在现代化浪潮中那颠簸挣扎的乡土记忆、生命温度和心灵纠结。
1
很多年后才读到莫言的《白狗秋千架》。相见恨晚,心里却暗自庆幸毕竟没有错过它。在作家的创作系列里,这个短篇似乎轻微得不值一提。要不是霍建起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暖》获得了东京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它很可能仍然处于湮没或者长期无人问津的尴尬之地。其实,这是莫言很棒的作品,这里面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而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围绕着这块热土展开他丰沛激情野性的想象。
《白狗秋千架》是对撕裂的乡土人生经验的深度开掘,它磅礴凛然如同钝刀割肉的叙事笔触直接指向人物滴血的灵肉之间,仿佛在往那隐痛难消的伤口上继续撒着一层又一层的盐。小说写了一个游子返乡的故事,他当年的出走是为了谋求生机活路,实现命运的转折,十年过后,他成了学院的老师,身份地位再不是从前,然而他回乡的目的并非为了什么显摆和荣耀,却是为了弥足生命中致命的亏欠。为了那个当年叫暖的女孩。他们曾经相知默契,彼此间也曾泛起过爱的涟漪,不过一次意外的事故(他们带着那只有灵性的白狗一起荡秋千,不料中间绳索断开),暖从悠荡的秋千架上摔下来,结果一根槐针刺瞎了右眼。那瞬间的欢乐顿时成为人生莫大的残缺与遗憾。
暖的命运无疑是凄苦的,她先后爱上的两个人最终都没有接纳她,——当然也说不上背叛,“我”还有“蔡队长”,可以迷恋暖身体里洋溢的乡村淳朴天然的气息,但是无情的现实到底还是粉碎了他们那不彻底的爱恋。“蔡队长”来自城市,文革期间带领一群会吹拉弹唱的文艺兵下到农村搞文艺宣传,对于他,乡村说到底不过是人生转换中的一块踏板,一处别开生面的精神驿站,而那个让他动心的乡野土妞,只不过是弥补自己心理空缺的临时的“绿色菜肴”。当然他没有亵渎她,告别的时候只是抱着暖的头亲了一下,呻吟着说,“小妹妹,你真纯洁……”至于“我”,属于暖的暗恋者,那种朦胧的憧憬从来未曾真正挑明。如果沿着上述线索,你会觉得这是一篇带点失落怅惘之情的作品,怀旧的伤痕恐怕早已在乡村的月色和凉风里缓缓散去。然而不是这样的。莫言的残酷和高妙体现在他是把酸涩而美好的追忆与眼前极端令人心寒的生命事件叠加穿插到一起来展示人物精神的痛苦、茫然还有渴望超越的。暖在失去两位意中人之后,迫不得已嫁给一个哑巴,不久一胎生下三个儿子,从娘胎里出来也都是哑巴。暖死心塌地认了命,用无尽的劳作捍卫了乡土人生的尊严和价值。养活着四个哑巴还有自己瞎了一只眼的五口人的家。所幸还有那条叫“豆腐”的黑爪子白狗,风雨里伴随着暖的摸爬滚打的命。造化弄人,生涯惨淡,累遇穷途。不过,即便如此,在小说的尾声段落,莫言还是以他充满挑战性和感召力的笔调,让女主人公不可思议地实践着她对宿命的反抗与挣扎,“她压倒了一边高粱,辟出了一块空间,四周的高粱壁立着,如同屏风。看我进来,她从包袱里抽出黄布,展开在压倒的高粱上……”也许,这是莫言后来著名电影作品《红高粱》高粱地野合那场戏的“草稿”或者“初稿”,但是里面浸润的生命情调却大相径庭。实话实说,我觉得《白狗秋千架》最后的情感宣泄,其戏剧性动机已经不是什么“感性解放”所能承受得了的,暖用自己最深切动人的直白口吻宣称,“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我了。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却把无限的思考和遐想留给关心暖的人生故事的人。
莫言的小说其实说起来更像传统的戏剧,尤其是古希腊悲剧的底色,讲究极端冲突的作法,完全笼罩了《白狗秋千架》的布局谋篇。在某种程度上看,这篇作品显然写得过于张牙舞爪,将乡土生命悲怆幻灭的东西推到了艺术表现的极致。“哑巴”的情节设计,即使不是矫揉造作,恐怕也难逃刻意求奇的嫌疑。就如同余华在《活着》故事的整体创意里,有意识地把福贵的亲人一一写死,以此博得小说的传奇性,莫言的章法结构大概也承接了过于仰仗戏剧偶然性和巧合性的“死穴”,一家四个男性都是哑巴加上坏了一只眼睛的主心骨女人,生命的悲剧意味固然可以直击乡土社会宗法制人伦价值的废墟瓦砾,给人大厦将倾的疼痛感,危机感和无助感,另一方面,却也给我们一种天意刻薄弄人、命运就是这么蛮不讲理的荒诞乖戾气息。在莫言笔下,故土原乡仿佛都带着原罪的氛围和情调,人来到此处,无非是在惩罚的境遇里弥补与生俱来的过失。
不必讳言,《白狗秋千架》从思想立意上有意识疏离了五四以来的悲悯温情的传统文脉,它没有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于国民性的反思,这其实是从农民身上挖掘封建宗法体制的道德虚伪悲剧(我们不妨想想祥林嫂的命运),也匮乏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那类乡土人生赞美诗的笔致,更缺少沈从文《边城》一类的的浪漫风情。也许,从人物残缺病态的生命冲撞里可以找寻乡土社会某些方面的劣根性和不文明因袭,但是,却无法成为替都市文明进行实质性辩护的借口和心理补偿方式。就说那个知识分子返乡的动机还谈不到忏悔的深度价值,他只是觉得当初若不是跟倾心的女孩玩秋千的时候出了事故,那么他的心灵原本可以平静如砥波澜不兴。而现在他成了乡土人生悲剧实际上的旁观者,可以表示廉价的同情,但绝无力量和信心去帮助暖恢复那原初的健朗生机和淋漓活力。
说起来挺纠结的,文学和艺术一旦触摸到乡土文明的根须,就总是要以祭奠的仪式来展开它们自身的丰富想象的可能和实质性动机的,而且被祭奠者往往是女性或者老人。
多年前看今村昌平导演的影片《栖山节考》那白发暮年颤动微弱却又壮心不已的阿玲婆的形象,给人留下至深的印象。这是一部描绘人类本能和社会体制相交错冲突的作品。片中的山村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食物的紧缺匮乏,造成了当地人有个不成文却人人遵守的规矩,凡是活到七十岁的老人都要被送上栖山参拜山神,某种程度上是任其自生自灭。
正是在这种极端残酷的生态环境里,阿玲婆也同样面临着行将被风雪湮没的事实。她必须接受也只能接受。可她的命悬一线之际的生本能却还要在垂死关头完成几桩未了的心愿:替中年丧偶的大儿子续弦,让按照村规不许结婚的二儿子满足一次性的需求,帮助与邻家女孩偷情而使其怀孕的长孙设法逃脱乡村原始礼教的惩罚而不惜葬送女孩一家人的身家性命。
在这里人类的延续族群的生存需要竟然是以老者的无辜牺牲为手段,文明的转型因此成了一次挽歌式的放逐及其与死神邂逅的无奈冲撞。当阿玲婆的长子在影片高潮段落冒着寒风背着母亲来到栖山之巅,大雪纷纷飘落,曾几何时死去的先人的枯骨在乌鸦的声声啼叫里给人大限将至死到临头的威慑,然而,阿玲婆的内在情怀却是坦然放下的,是心满意足的,有着看穿命运谜底的坚毅和洒脱。她告别了儿子,固然带着几分依依惜别的情愫,但更多的竟是赴死的庄严肃穆和超脱。山神的信仰不绝如缕,一任阿玲婆躺倒在大山的怀抱里享受到自然生命的生死轮回和交替。
也许,无论中国的暖还是日本的阿玲婆,她们都把一颗心交给了乡土文明的最后礼仪,不管那是宿命的遵守,盲目的虔诚,还是挣扎之后的解脱。这两部精彩深刻直至让我们生发出无边艺术感叹和人生怀想的作品,代表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东方审美的极品神韵,彰显了启蒙理性的片面无奈,预示了理想家园的残缺与心灵终极处的骚动不安。
2
疼痛的东西其震动人灵魂的程度固然撕心裂肺,但是不可太久,否则,那种根深蒂固的痛楚就会变成压迫人生命整体张力的一种破坏性建构。乡土社会即使在高度扩张的当代文明版图里被无情地边缘化,乡音乡情即使遭遇到钢筋水泥丛林法则的无尽蚕食而变得气喘吁吁,然而,某些驻守在过去传统里的温情依然还会不失时机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命个体的血脉深处,从而流淌出乡土歌谣般的美丽舒缓的幽情。
如果说《白狗秋千架》是一次心灵的探险,那么由这篇令人坐立不安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暖》却是难得的精神驿站,没有了极端痛楚的两极化的故事情节营造,弱化了暖的从外部形体到心灵世界的悲剧性内涵,譬如改编者将暖从秋千架上摔下来之后的眼瞎变成了腿瘸,原作中三个哑巴儿子的极端形象在电影里置换成了一个健康的小女孩的人物造型。其他的人物身份、性格也相应熨帖吻合着新的艺术基调的构想,尽量往温情怀旧的主题上靠。
这当然是由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艺术发展的整体环境制约和影响到电影的精神容量和生命价值观,才使得《暖》的主题立意符合情感回归、人性关爱的时代主旋律。
影片的导演霍建起曾说,生活是无奈的但诚意十分重要;人在旅途中需要彼此理解与关怀,常怀忏悔或心存感激才能够心安理得。本着这种质朴坦诚的人文信仰,霍建起重拾沈从文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里所恪守皈依的乡土文学的生命追求和返璞归真的精神本色,在新的年代讴歌人性淳朴的共鸣和回归。
王德威曾经在北大的系列讲座里谈说过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人道主义传统。这是针对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和家国忧思文脉的另一种制衡和补充。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作家艺术家苦心孤诣地在大时代激流涌进的涛声中听取急管繁弦背后的浪漫优雅,将残酷急骤的社会变迁的动态观感转换为乡野牧歌式的静态审美情怀,从而在历史错杂的脚步声里留住了几许心灵的悠远、朴拙和宁静。
霍建起的《暖》在风景画面的处理和人物心理层次的把握中,很有一点沈从文《边城》之类作品暗流涌动的暖色调和抒情性,它改变了莫言原作里对命运悲剧的过度彰显和渲染,而让乡土诗意的成分加入进来,让人性中善意美好的因子变得清澈透明。
在这里城乡的差别依然存在,渴望出去的愿望在女主人公的心头还不时萦绕,譬如当她和井河(即莫言原作里的“我”,作者注)荡漾在秋千架上时,她问他看见了什么,井河回答得很老实,“我看见稻草堆的尖了”,而当井河反问她,她说“我看见北京了!我看见天安门了”!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对远方和梦想充满无尽期待和痴迷的女孩,现实的人生并没有按照她的愿望来设计,两度失恋加上一条残疾的腿,遏制了她放飞的心,因此她又开始本能地依恋起故乡的一切,包括那个哑巴男人。毕竟他们有了自己的骨肉——一个天真可爱懂事会开口说话的女孩,更何况在影片中哑巴的形象一改莫言作品里的野蛮失礼,而呈现出那种质朴憨厚的村民本色甚至还有点知心会意的体贴与温情。
影片《暖》实际上说已经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怀旧心理的单纯释放和捕捉。我们更应该将其视为中国乡土文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精神慰藉。尽管外在的经济文化的落差固然可以改变人们出走或者重返之际的复杂心态,但是,故乡的根系毕竟在每个人生命的深处藕断丝连。《暖》在画面场景中有意识地选取水牛、鸭群、草垛、春蚕、雨巷等物象,将故事本身的混融性构成,依贴着人性与故乡的密不可分的深层次背景,如同陈年佳酿一般会在观众的心里默默发酵涨潮。
用伤感和温情构架起来的《暖》在质地里有一种哀而不伤恪守中道的安详朴拙之美。它让我们看到高度物质化文明中某些已经被淡化忽视的精神气息,城里人和乡下人其实还可以坐在某个温暖的角落里重话桑麻,共叙世道沧桑,就如同电影尾声,井河做的那个深沉的承诺,“等你长大了,叔一定接你到城里读书。”这是跟暖的女儿倾诉的肺腑之言。在其间我们也仿佛听到了突飞猛进社会浪潮里还有人的温情暖意拒斥着冰冷的经济伦理,磨合着城乡的二元对峙。究其实质,是文明的某些敏感部位还依然需要故土诗意的看护,人性的卑微信仰中还少不了乡土精神底蕴的熨帖和支撑。
3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位叫阮义忠的台湾摄影家,近些年来他以“人与土地”的系列摄影作品日益受到人们的理解和关注。2011年年初,阮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首次执笔道出“人与土地”摄影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后来文字和摄影汇集成册,由中国华侨出版社于2012年2月出版发行。在我本人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品质有所质疑和顾虑重重之际,正是阮义忠的画面和声音令自己释然于怀,重新对乡土中国的定义与内涵发生切身的体味和眷恋。
故土情怀,故园情结、乡愁意识,毋庸置疑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永恒的主旋律,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那离乡游子的缱绻顾盼,遥想故园灯火的精神回想,还有那对土地乡野枯藤老树的脉脉牵系,都展示了人与精神来路和源泉的无法割舍的情感依傍。尽管随着古老乡土文明的逐渐衰落,近现代都市社会的强健崛起,商业体制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人们在当下疲惫不堪的生存危机和对物欲无穷尽的追求里,业已或者正在失去本真的心路。然而故乡和故土,毕竟还是以精神存在的方式继续召唤着艺术的寻找和造访,就像阮义忠的文字和画面带给我们的生生不已的迷醉与痴情。
也许,还是那句老话表达得异常传神贴切,“城市是人造的,乡村是神造的”,人的最初的天性,大体上裸露于乡野的自然律动中,而未曾被程式化的文明篡改矫正和剥离。正因如此,面对摄影师用那精准生动的瞬间抓拍到的场景,人物的特殊造型,细节里镌刻的丰富表情,你会跟着定格的记忆仿佛重返乡土童年的伊甸园。
在“澳花的三代同洗”的镜头捕捉里,我们会看到婆婆、媳妇还有孙子三代人来到溪水旁洗衣洗澡的情景,那是冬天的早晨,躲在云深不知处的某个乡间发生的充满生命情趣的瞬间,尤其是那位面对镜头赤身露体用手掌捂住整个面颊的小男孩,那原本自由自在地与大自然融化为一的默契,只是在遭遇到意外的被拍照的情况下,才显露了文明带给人的羞涩和赧然。在“告别童年”的画面里,“一处刚收割过的稻田中,一个小孩朝着日落的方向呐喊。这么小的乡下孩子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情绪?”作者不仅拍得好,话问得更是惹人牵动心肠。有人说,画是无声的诗。而在这作品里,那个凸显在空旷原野上与天空大地叫板的男孩,两只小手顽强地伸向空中,他在抗议吗?我们仿佛听到了他生命深处的轰鸣。至于被命名“兰屿的头发舞”的摄影作品,是摄影师对台东县兰屿乡土著居民原始歌舞的动态写真,几个达悟族女子用她们浑然忘我的肢体语言表达着生命的恣意奔放,在阳光底下尽性地甩动长长的头发,她们弯腰挺身甩头的动作“与近在咫尺的大海唱和、呼应”,显示出野性活力的美。那是罗素在描述希腊酒神精神时说的“用热情扫除审慎,以迷醉冲决理智的网罗”(原话大意如此)。
阮义忠的文字和摄影应该说是在人类面临空前的生产消费失控、盲目占用土地资源、严重的环境污染、人际关系日益冷漠疏离这样的无情现实面前而采取的重温乡土文明诗意的一次动人的深呼吸。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拍照时,最想留住的正是人性的美好: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
换而言之,如果继续漠视乡土中国的内在亲和力及其作为精神家园象征的感召力的话,则我们在现代或者后现代社会浪潮间的无尽挣扎求索迟早会沉陷其中难以迷途知返,起码那是一块值得人心暂且休憩安眠的临时驿站,抑或是时下物欲熏天的过度浮躁的时代综合症的一剂良药。
在阮义忠的画面和文字里,我们能由衷感觉到血缘与亲情依然犹在的传统脉息(如拍摄于宜兰县礁溪乡二龙村的家族留影,月亮高悬夜空之际,村子一处空场里大人小孩簇拥下喜笑颜开的瞬间定格,折射出几代同堂的中国式的乡情乡梦),会切身分享到乡野的孩子围拢一处玩儿翻筋斗游戏时的自在快慰(想一想今天城市里的儿童都变成了网络和虚拟空间的俘虏,我们的感概可能会更多些),而当读者的目光一旦锁定一位农民在群山环抱的玉米地里低头默祷的身姿,触摸到快门按下的须臾间北港的妈祖信徒虔诚跪拜的敬畏之态,甚或是为那辆老牛车载着眼神里散发着无边平宁喜悦的一家人慢慢远去的情景而动心,你都会为自己湮没的记忆里突然翻涌出的莫名颤抖而暗自吃惊——久违了,我们的乡土,我们的乡情和乡亲,久违了,大地苍天和人的原始默契与投缘……
责任编辑 宁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