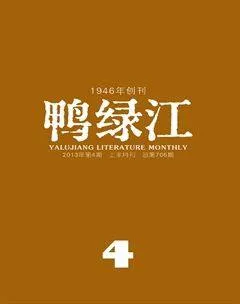梦里水乡
2013-12-29刘薇
刘薇,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主任医师。喜好文学、写作、绘画、摄影及音乐。1992年至今已发表八十余万字散文、诗歌、小说、健康科普文章及百余幅幽默漫画、卡通漫画、彩绘插图、人物漫像等绘画作品。参与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并绘制插图。小说《养我五日》获《新作家》创作奖。散文《风中老槐》《古都脉动》等获市级奖项。
烟雨同里
三月,春色正好,花香、鸟语、桃红、柳绿。
长途汽车停在小小的车站外,眼前是暴土扬长的街道和风驰电掣的汽车,但回首处的一座貌不惊人、名曰“三元”的长桥却将我带入了同里古镇。
初名“富土”,唐时更名“铜里”,宋时,叠叠折折,化为今日的“同里”。虽几易其名,但对固守传统、不为花花世界所动的同里人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古镇外面环绕的绿水千年不变,将岁月与红尘隔断,而一座座石桥又在过去与今朝、传奇和现实之间架起了回味的阶梯,于是,当我一步步走入古镇时,刹那间竟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虽然手中握着许多景点的联票,我并不急于前去游览,宁可贪婪地在这小街上漫步,细细品味这原汁原味的古旧与素雅。
天公作美,那日清晨彤云低压,微风习习,空气清新。大约因为不是周末,所以游人稀少。晨雾中的水乡格外俊秀——错了,那弥漫而朦胧着的不是雾,而是早起阿婆点燃的炊烟,是贪睡骄阳支起的纱幔,是寂寞访客眼中的乡愁。
走在岸上,蜿蜒的流水无时无刻不陪伴在我的身旁——水边伫立着睡眼惺忪的女人,她们的脸上挂着平和的笑容,或绾着袖管儿在刷洗着木桶,或蹲在石阶上揉搓着衣服,或探出身子在汲水,于是宁静的水面便泛起了阵阵涟漪……水上则屹立着名称不同的石桥,或曰“乌金”、或称“东溪”;它们的姿态也各异,或高高地拱起,或平平地横架……
岸边房屋粉墙斑驳,窗榭半开,青瓦结露,回廊曲折,无不透着浓浓的风情,我的目光却依旧被那一湾春水所吸引着。石板路上看不出风霜,舒缓的流水沉默无语,我却分明听见了古镇的声声梦呓,她仿佛在询问陌生的人为什么要惊醒沉睡中的孤女,在诉说积压在心头的忧伤和委屈;或者那是朗朗的书声,寄托着宋朝至清末的状元、进士、举人、秀才们的凌云壮志,仕途坎坷的无奈与辛酸……
渐渐的,行人多了一些,推着车子上班的、背着书包上学的,他们的脚步并不匆忙。支起油锅的、打开铺面的、做小生意的也很悠闲,虽然对身边的美景已熟视无睹,但那份从容和恬淡早已融入每个人的血液和心中。
不知不觉间来到同里有名的“三桥”。这是地处古镇中心成“T”字形的水道,聪慧的同里人依水建造了“品”字形的三座石桥——太平、吉利、长庆。此三桥建筑风格迥异,寄托并涵盖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希望和祝愿。相传,每逢家有新生的孩童、送嫁或迎娶、老人的寿辰,人们便会来“走三桥”,因为他们相信“走过太平桥,一年四季身体好;走过吉利桥,生意兴隆步步高;走过长庆桥,青春长驻永不老”。
在桥边的弄堂口抵不住诱惑买了一串即炸即卖、多汁多料、臭不可闻却香在满口的油炸臭豆腐。卖豆腐的老人不仅对我笑容可掬,还耐心地教给我“走三桥”的正确顺序,于是我便“不能免俗”地按老人所说的方式走过了三桥。三桥围拢的水面上一只扁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其实那船也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船舷上站立着五六只鸬鹚,旁边一面杏黄色的大旗上是招揽生意的“广告”,内容大抵是说几元就可以欣赏几只鸬鹚的捕鱼表演云云,虽然过了许久并没有游人光顾,但主人和鸬鹚一样还是悠哉游哉地等待着。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时间仿佛已经不存在了,只有这迷宫一样的水道和手中的地图是真实的。有时在临水的茶铺问路,有时在街边的小摊前挑选工艺品,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买或不买,你得到的总是详尽的指点和温暖的笑容,感动间天空飘下蒙蒙细雨,这雨中的水乡立时又展现出别样的温柔。
冰凉晶莹的雨点滴落在额头上。那雨滴太过细小,仿佛只是一团雾气在眼前升腾;那雨滴又太过羞涩,好像是新嫁女的思乡之泪慢慢滑落。细细看去,这雨竟是嫩嫩的淡绿色,否则水边的垂柳为何会染上了丝丝翠意?或许它又是浅浅的粉红色,于是点出了春花的娇艳和芬芳。侧耳听去,这雨也并非无声,它时而轻叩窗棂时而慢摇花叶,声声浅唱、句句低吟。足下的石板路潮湿却并不泥泞,身边的流水闪着点点微光,远处的石桥若隐若现,咫尺的老屋昏暗但充满温馨……一切在这雨的冲刷下变得愈发干净,一切也在这雨的渲染下愈加清秀。
已是中午时分,我坐在一家小餐馆里,宽敞的门外是同里的雨中即景,干净的屋内是同里人憨厚的笑脸。经济实惠的小菜配上清爽可口的茶水,就着春雨珍贵的和质朴的乡情,我竟有些微醺的感觉了。店主人已年过六旬,对许多事情都有一种超然的平静,他告诉我同里之所以直到现在还是这般安静,躲过多次朝代更迭的战乱,主要仰仗于早先艰难泥泞的土路和迷宫一样的水道;而文革中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暗藏机智的安排——退思园、嘉荫堂、崇本堂这些同里最好的古迹分别用于工人文化馆、幼儿园和公安局的办公场所,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如耕乐堂等处则无一例外被毁坏了……
午后,小雨依旧不急不徐地下着,我信步在退思园、嘉荫堂、崇本堂、耕乐堂之间,徜徉在雕梁画栋、奇石古树、长廊庭院之中。不知何时,雨已经停了,傍晚的天空如洗过般湛蓝,甚至还有几缕金色的阳光斜斜地射来。船娘穿着碎花篮袄,轻摇木船,载着游人,边歌边行进在雨后的春水中。
同里的弄堂中最具特色的是穿心弄。晴天走在穿心弄中,不见骄阳,只觉得狭长而深邃,足下的石条于落脚间会发出“铿锵”之声,于是近三百米的弄堂回声不断;雨天走在穿心弄里,则湿滑无比,雨滴打在石条上,伴着谨慎的脚步,更是别具风情。现在,我走在雨后的穿心弄中,既能聆听石条的声响又能体会行路的艰难,真可谓一举两得。
古镇的东南,在仿古的戏楼旁还有一处建筑风格鲜明的“明清街”,那里商家云集,从美味多汁的“状元蹄”、清香四溢的“闵饼”、细腻软糯的“青团”,到充满民俗特色的蔺草制品,再到精美的同里风景水墨画……可谓应有尽有。
从明清街出来时已是华灯初上、渔人晚归了,周围越发的安静,耳畔只有隐隐的水声。星光映在水面上,如同撒落了一池的碎银,黝黑的是桥的剪影,闪烁的是屋檐下的彩灯,这一切将这水道装点得更加美丽动人……
入夜,回味着那黛瓦素墙的民居,蜿蜒碧绿的流水,走进梦乡,走进温婉妩媚的水乡古镇。
繁华周庄
其实,启程之时就有人告诉我,江南古镇游一个就可以了,因为都“大同小异”,就像国人眼中的 “老外”全是高鼻大眼或“老外”眼中的国人都黑发圆脸一般。但真地细细观察下来,你一定会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甚至有大相径庭之感。
车子刚刚驶进周庄车站,就呼啦啦围上来一大群人。有的邀请你到他的餐厅去吃饭,有的在介绍自己的旅社;卖地图的,三轮车夫……晕头涨脑中我买了一份导游图并坐上了一辆三轮车,据说这车站离周庄古镇还颇有一段距离,况且五元的车资也还算合理。
三轮车装饰得挺红火,蹬车的是周庄老乡。他边掌控着车子边和我攀谈。当我问他周庄在他眼中如何时,他憨憨地一笑说,“天天看呢,也没觉着有什么哩。”我又问他周庄的开发带给他的是什么时,他坦率地告诉我,土地收了去以后,每年给他家三百元的口粮,凡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还有八十元的补助,“这不,我还能弄个三轮出租车呢。”我问他这三轮车上花花绿绿的广告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位大老板投资在古镇旁要再建一个“新周庄”……说话间来到一座新建的仿古长桥,地图上标明应该是“周庄大桥”,上坡的斜度使得他跳下车来努力推行,额头上已冒出了汗珠。下坡时重又坐在座位上的他扬着头、眯着眼,给我讲述起几十年前儿时的他花五分钱摆渡过河去镇里看戏的故事。“那时可没有这桥,来回都用船的。”说这话时那脸上满是憧憬和回味……车子终于停在仿古的高大牌楼前,我来到了号称“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
全功路与全福路成十字交叉,两边满是大大小小的商店、饭馆。许多阿婆拿着地图和明信片在兜售,加上熙熙攘攘的游人和红尘滚滚的汽车,感觉很是现代。
在高三十三米的全福塔脚下又有一座高大巍峨的仿古牌楼,那便是古镇真正的入口了。还没有进去,从旁边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靠近后问我是不是需要一位导游,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她又压低声音告诉我她可以以低于门票不少的价钱领我进去……我当然宁可自己买票进去了,至少这样比较坦然和踏实。
走过“贞丰泽国”的牌楼,里面同样是小店云集。都是些手工艺品,仿丝的衣裙、内画的鼻烟壶之类的,虽然琳琅满目却没有什么特色。当然还有比比皆是、各称正宗的“万三蹄膀”。随着一个个旅行团的拥挤人流,我转过了古镇照壁,径直奔“双桥”而去。
双桥是世得桥、永安桥的合称,一座如飞虹拱起,另一座似玉簪横亘,两桥成九十度角连接,造型独特浑如古时的钥匙,因此旧称钥匙桥。这一弯一平的两座桥,因陈逸飞先生妙笔生花创作的《故乡的回忆》而一鸣惊天下!
双桥的确古色古香,桥边的泡桐树花也开得正好,酷似一幅淡彩水墨。本想将双桥美景收于相机之中,不想桥上桥下游人如织,大家都在奋力抢拍留影,那场面好像赶集一般,大概照片上应该是许多陌生面孔莫名其妙的合影吧,就连桥下的木船也已首尾相接,船娘的歌声也快由独唱变成合唱甚至轮唱了。
双桥附近的古式房屋均是面向街道背朝流水而建,游人是不能贴着水边行走的,因为在房屋和水道之间并没有路,那河本就是如网的街道——以水为路、以舟代步,这正是古镇周庄的一大特色。我只好穿行在拥挤的店铺之间,浏览着十元三串儿的“珍珠项链”和二十元一套的“紫砂茶具”,偶尔在房屋之间的咫尺空隙间得以管窥那涓涓的流水。
已有九百年历史的周庄“镇为泽国、山环水绕”。相传春秋战国时期称为摇城,北宋元■年间始称周庄。元代中期的传奇人物沈万三不仅留下了与皇帝斗富,比赛修建南京城、又要代替朱元璋劳军而触怒龙颜、被流放异乡凄凉而死的传奇故事,还留下了后裔沈本仁于清乾隆年间建成的房屋相连、气宇轩昂的庞大走马楼“沈厅”,更有色艳肉酥、肥而不腻的万三蹄膀。
从石桥上望去,周庄的景致真的是格外优美!但悠长的水道弯曲依旧,却有太多的船只填塞其间,两岸的旧屋白墙黑瓦,却有无数只做幌子的彩灯高高悬挂,纵深的小巷不再是通幽的曲径,蓝布包头的村姑也成了精明的店家……
即使是在傍晚,游人仍在徘徊,古镇也还是那么的繁忙。点点的红灯串在屋檐上、映在流水中,指引着人们去就餐、去消费、去购买纪念品。当我站立在一个卖熟食的店铺一侧,想借着微弱的灯光再看一眼地图以决定去留时,店主人——一位操着外乡口音的女老板几乎是愤愤然拉灭了电灯,顿时将一片黑暗和一种失落留在了我的身边。
思来想去,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中国第一水乡”,恐怕只有“繁华”了。以为古镇的感觉应是淡淡的、静静的,好像内心深处的一段朦朦胧胧又无法忘怀的如烟往事,绝不可能与繁华扯上关系。那几经沉浮后宠辱不惊的古镇在哪?笑对沧海桑田波澜不惊的古镇在哪?
转念一想又不禁释然,我们要寻找的不就是小桥、流水、人家吗,又何必苛求一定是老砖、旧瓦、古屋。世界已经在变化中走进二十一世纪,难道这里就一定要街景破败、朽木横陈吗?谁知道宋时作为苏州葑门外粮食、丝绸、陶瓷集散地的周庄就一定不像现在这样喧嚣热闹?
看着周庄,我还是生出一丝怜惜。
责任编辑 林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