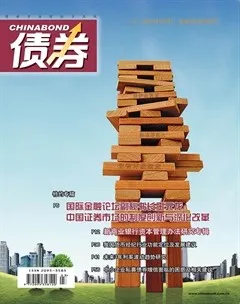小议国内债市的投研转化与收益空间
2013-12-29王晶

如果要找一个恰当的比喻来阐述金融投资与产业投资的关系,我会选择自然界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和谐共存来作比。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复杂而紧密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食草动物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进食,而食肉动物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觅食,二者的生存方式完全不同。一个显著的联系在于,二者之间的食物链关系使得两个群体都拥有了大自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机制。
由此及彼,作为国内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我们的所有收入从本质上来说,都源于实体产业的价值创造。但如何有效地参与分享这一价值创造过程?这便要求金融机构的投研人员倾注时间和精力用于练就发现机会、捕捉机会的“生存技能”。
投研转化在投研工作中的重要性
对于投研人员业务“生存技能”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大致包含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基础研究,这其中涵盖了对经济基本面、政策面、供求层面等多重考量因素的理解。这项工作的目的在于确定投资收益的大致“方位”,为后续的工作指明方向。
第二步是投研转化,讲究如何把缜密的研究逻辑“翻译”成具体的投资策略。这项工作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未来组合的获利能力,即投资收益的空间大小。
第三步就是运用一切合理的交易技术将策略付诸实现,让收益跃出脑海,化为现实。
应该说,在目前的国内债券市场中,绝大多数的投研工作都集中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但是,从内在的机理上看,如果缺乏第二步的衔接处理,第一步和第三步之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第一步基础性的研究逻辑往往是大方向的,是定性的;而第三步的债券投资操作却是非常具体的,所构建的组合要具备久期、凸度等诸多定量特征。举例而言,现阶段,市场普遍认为2013年的国内债市缺乏单边上涨的内在动力。假定这一预判的假设和逻辑是合理的,那么我们随之要问,作为应对,今年具体的债券投资组合的信用评分应该设定为多少?组合久期应该控制在多少?杠杆倍数应该是多少?等等。回答这些问题就意味着要把定性的研判定量化,也就是笔者所说的“翻译”工作。
如果“翻译”工作没有做好,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年初我们判断对了全年收益最好的品种,但年终却发现这个品种并没有带来多少实际的回报,因为我们没有押上足够多的筹码。而如果我们做好了必要的“翻译”工作,那么效果很可能是,我们仅凭借一个几乎被市场所忽视的获利机会,通过有效地放大,取得了不俗的投资业绩。
一个典型案例
在投研转化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上世纪90年代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它的兴衰历程都和其自身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密不可分。
LTCM的投资运作始于1994年3月,投研团队拥有两位诺奖得主、一位美联储前副主席等众多精英。1998年之前的4年内,LTCM的投资成就被华尔街视为传奇,除了卓越的获利能力——4年获利3倍,风险控制更堪称典范,前4年的获利过程中,组合回撤鲜有超过2%,净值增长完全是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支撑这些非凡成就的基本投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宏观环境稳定的大背景下,不同债券品种间的信用利差会趋向收窄。这一点相信市场上的其他机构也同样认识得到,但为什么最终各自的收益空间却有着天壤之别?最本质的差异就是各家机构将定性研判“翻译”成具体投资的能力高低。LTCM准确度量了这一对冲套利操作的收益和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它运用杠杆操作将收益空间拓展到了极致。而其他机构对相关风险收益的度量则相对模糊,最后也就使得其投资组合的表现流于平庸。
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正是由于LTCM前4年卓越的投研业绩,使得它忽视对风险和收益的度量工作。面对经济危机这种非常规事件,它显得过于自负,以往严谨的对冲套利演变成了赌性十足的单边下注。现实异常残酷,在1998年的5月到9月间,LTCM亏损超过90%,最终,公司在成立5年后不得不宣布破产。
投研转化在国内债券市场的应用
令人震撼的历史事件往往会激发人们的探索热情。怀揣着对LTCM兴衰历程的敬畏,我们不妨审视一下身边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内债券市场。众所周知,作为市场上最活跃的逐利机构,券商自营和基金对投资获利这一“生存技能”的渴望无人能及。由于没有低成本吸纳社会储蓄的负债能力,它们一开始便将债券投资的主要标的设定为信用类品种上。从最基本的评价投资业绩的相关指标上看,这种从研判到投资的“翻译”过程是有效的,2007年至今,信用债整体的夏普比率[注:.夏普比率是指每单位的风险所得赚到的报酬。 ](Sharp ratio)是国债的2倍有余(见表1)。
但是,如果从更细致的组合配置有效性角度来衡量,我个人认为,目前市场上券商自营和基金的债券组合配置效率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也就是说,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债券投资的收益空间还可以进一步拓展。
历史数据显示,中债高信用等级债券(1-3年)财富指数在2007年至今的表现要好于信用债的整体水平,说明AA级(含)以上债券表现要好于其他品种,这似乎有悖于多数机构偏爱高收益债的主观认知。更有趣的统计结果还在于,那些到期收益率最低的一类信用债,即中债高信用等级债券(1年以下)财富指数的历史表现更是远远跑赢市场,6年来的平均夏普比率高达3.89,3倍于信用债整体水平,6倍于国债整体水平。这也就意味着,理论上通过恰当的交易技术,可以在风险等同的情况下,获得3倍于信用债平均水平、6倍于国债平均水平的超额收益。
其实,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之所以会如此,正是因为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偏爱高收益债这一固有认知,导致市场的定价体系存在某些不合理的成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至今仍可以对国内债券市场的收益空间抱有不错的预期。但如何把握这个收益空间,这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和数据挖掘,这个过程会逐渐量化各种策略的风险收益以及概率分布。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当一些“黑天鹅事件”发生时,这样的分析收效甚微。那时更需要的是像索罗斯一般的哲学思考和艺术操作。但这并不构成我们摒弃投研转化这一“翻译”环节的理由,相反还是我们进一步改进这项工作的动力。因为,精细地投研转化,有效地拓展收益空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技能,是我们长期追求的事业。
作者单位:金元证券固定收益总部
责任编辑:夏宇宁 罗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