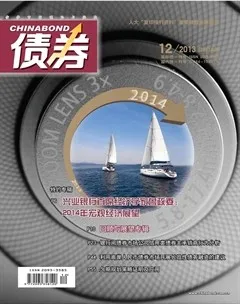“融”之是与非
2013-12-29肖雄伟

金融魅力之关键在于“融”
金融究竟是什么?这可以从“金”和“融”两个方面来理解。
通常情况下,“金”被理解为货币。但是,在现代金融的概念下,对“金”的理解不应仅限于货币,因为传统的货币概念已经无法将诸如杠杆交易为现代经济带来的放大作用等机制囊括其内了。“金”应当解释为一切货币及与其等效的社会经济手段。
“融”即融通,是指对“一切货币及与其等效的社会经济手段”的引入机制。笔者认为,金融魅力之关键就在于“融”,正是具备了“融”,人类的经济活动才拥有穿越时空隧道的神来之笔,促使经济飞速发展,甚至产生质的飞跃。“融”之妙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化“分散”为“集中”
通过储蓄的形式,可以实现社会大量闲散、小额资金的集中,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从而加速经济建设。通过招股、发债,也可起到集中资金的效果,甚至比储蓄更为直接。
2.化“静止”为“流动”
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激活静态的资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做足了文章,为此创造和发展出了形形色色的结构化融资证券。
3.化“未来”为“现在”
通过信用卡消费以及住房按揭贷款等透支未来现金流的形式,可以使个人梦想得以提前实现,同时也使社会商品交易得以提前完成,从而大大降低了社会库存,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
4.化“风险”为“安全”
通过股份制、投资组合策略,可以分散风险;通过期货制度、保险制度,则可以转嫁风险;还可以通过做市商制度,逐级“收集”风险头寸,并进行风险头寸的适当集中,然后在更高级别及更广的范围内将“风险”进行对冲。
5.化“不合规”为“合规”
商业银行通过一定的结构制度安排或者业务创新,可以合理规避行业监管政策,实现业务的放大发展。
尽管“融”有以上诸多妙用,但在对金融工具或结构化产品进行大力开发的今天,一定要谨防“过融”(即过度消费、过度透支、过度杠杆交易等)现象的出现。“过融”会导致信用链过长,虚拟经济异常增长,从而加剧金融业系统性风险。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对“过融”带来的危害的最佳诠释。
“融”之利与弊
(一)金融经济因“融”而生
人类社会活动必须消耗物质,而物质的原始取得(所谓原始取得,不包括买卖、赠与乃至盗抢等形式)简单归类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该物质本来就存在于自然界,只需通过人类生产劳动将其探明、取回;二是该物质并未大量存在,但是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将其大量繁殖(包括种植、养殖)。具体而言,第一种物质的取得方式构成了以采选业为起点的产业循环链。以钢铁为例,先是通过采选业取得铁矿石,再辅以一定的能源供给,冶炼成钢铁,再制成各种成品钢,通过物流业分发,最后通过建筑业、汽车业等行业的生产组合,形成人类社会生产以及生活的硬件基础设施,如建筑物、道路、桥梁以及车辆等;第二种物质的取得方式构成了以农林牧副渔业为起点的产业循环链,主要为人类生活提供个人生活资料。
上述两大产业循环链构成了实体经济的基本。由于人类社会并不满足于简单再生产,也不满足于依靠个体资本的原始积NyedbfvVY+zB4/8iv8H+T+cWT5LakXOS8l3YUABaF3w=累来进行生产,因此在两大生产部门内部及其之间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金融资源(金融工具)配置行为。而这些符号化成果以及符号之上的二次乃至N次衍生品(如基金、期货、期权等综合化后的复杂结构型金融工具)就汇集成了一条庞杂冗长的符号经济链,笔者暂且将其称为“经济镜像链”。这条链条既反映实体经济,又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它使得当代经济运行越来越符号化,这是当代金融经济的重要特征。
(二)虚拟经济及财富幻觉
虽然“经济镜像链”的产生有利于加速实体经济交易,深化资源配置,并且还可以实现通过控制符号经济来快捷地控制和调整实体经济的功效,但是它同时又带来财富幻觉及市值的暴涨暴跌,并使得财富保有和流通变得更加诡秘而具有不确定性。对此,笔者假设一个案例加以说明:
甲自建10套房,以10张证券来代表,每张证券代表1套房的财富价值。现甲将其中1张证券及其代表的房产以50万元卖给乙,保留其余9张证券,此时甲的个人资产总市值为500万元。假定已经出售的证券及其所代表的房子沿着以下价格变化进行交易转让:
甲(50万元)→乙(100万元)→丙(150万元)→丁(200万元)→A
在以上交易中,乙赚50万元,丙赚50万元,丁赚取50万元,此时甲手中尚有9套房产,此时甲的资产市值已经跃升至1850万元(=200万元/套×9套+50万元),浮动盈利高达1350万元。而此时全部房产的总市场市值为2000万元。
假定资产价格“过热”引起了经济监管当局的担心并采取紧缩性调控政策,此时房产市值开始节节下降,并沿着以下价格变化顺序进行流通转让:
A(150万元)→ B(100万元)→C(50万元)→D
在上述交易中,A、B、C分别亏损50万元,此时甲手中的另外9套房屋的市值又回到了450万元,相比于200万元/套的市场最高价,甲整整损失了1350万元。而整个房产市场的市值也由2000万元缩至500万元,蒸发了75%。
上述现象实际上仅仅是一种财富幻觉,这其中唯一的现实是:乙赚50万元+丙赚50万元+丁赚50万元=A亏50万元+B亏50万元+C亏50万元,财富在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
财富幻觉现象也普遍存在于股票市场。2008年中国股市号称市值蒸发了24万亿元人民币,但实质上追根溯源只有几万亿元的投入资金而已,其本质是几万亿元资金炒高了整个A股市场的市值,在股市最高点计算的市值并不能代表真正有那么多资金在股市。市值上涨并不等同于等量的资金入场,市值蒸发并不等同于等量的资金离场,这种现象源于“边际撬动”,即某个交易日里仅有10%的股票发生交易,但却能把股票价格推升至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而其他没参与交易的90%的股票也自动分享了这一“疯狂的荣耀”。
(三)“过融”之下系统性风险剧增
因“融”而生的虚拟经济,或称符号经济,通过与现实经济的对接渗透,为实体经济发展贡献正能量。但如果放任其发展,造成“融”之过度,则可能带来诸多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加重对实体经济的盘剥;二是引发大面积流动性危机;三是造成资产泡沫;四是引导实体经济资金反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资金“短路”,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空心化。
自2012年年中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呈低位震荡态势,宏观政策以稳增长、调结构为主,很多行业遭遇去库存化和去杠杆化的痛苦调整,正常的融资渠道已经难以满足其需求,因此企业转而借道金融机构其他非常规途径,派生出了各种结构化方案,这就促使国内银行理财及同业业务飞速发展。商业银行理财、同业等金融市场业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短养长”,银行理财产品靠不断续发维持,同业业务靠不断借钱扩张。而这些业务在绕开信贷监管的同时,大都或多或少地与地方债务平台及房地产有着联系,一旦任何一个资金节点出现问题,因其规模庞大,必然是大面积的资金链断裂,从而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正因为有如此大的潜在风险,所以银监会于2013年3月下发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8号文”),意在规范商业银行对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投资运作,要求改变理财业务中不透明的资金池运作模式,实现资金和投向的一一对应,并规定非标准债权资产投资的比例上限等。
选择最佳自由“融”度,以保我国经济金融安全
经济因“融”而生,亦可因“融”而危,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012年以来,人民银行不断加强对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的监管,监管的目的并不是要限制此类业务的发展,毕竟“融”乃金融经济的本质属性,而是要商业银行维持合理的杠杆和符合经济发展阶段需要的工具结构,最终的目的是维持整个金融生态链的平衡和健康发展。
“融”之利害不在于非此即彼的取舍,而在于“融”的自由化程度问题。纵观人类经济金融发展史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总结“融”之是与非,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所要做的是:全面规划,多管齐下,合理引导,鼓励创新,兴利除弊,针对社会经济不同阶段的政策目标选择最佳自由“融”度(可近似理解为杠杆率),以保证国家经济与金融的安全。具体应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一)雄厚的实体经济是“融”之基础
一般说来,经济分为实体经济、符号经济和信仰经济三大块。合理的结构应为:实体经济占GDP的60%左右,符号经济占25%左右,信仰经济占15%左右1。没有雄厚的实体经济做基础,完全凭借过度发展符号经济和信仰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快速、平稳发展的。
例如,在2007年之前,美国受全球化分工的影响,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大量人力从事着符号经济和信仰经济,使得这两种经济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从而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
再如冰岛。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金融业是冰岛唯一的支柱产业,冰岛人均GDP曾排名全球第四。然而,危机爆发后,该国股市单日跌幅曾一度高达70%以上,整个2008年冰岛股指(OMX指数)跌幅最终高达94.4%,“熊”冠全球。冰岛政府因此背上了承重的债务。痛定思痛,冰岛重新确立了大力发展地热及海洋渔业等传统实体经济的目标。
可见,实体经济乃国之发展根本,我国必须夯实实体经济这一基础,并持续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
(二)对金融业务的全面指导和监管是“融”之关键
理论上,金融经济的运行受制于实体经济,是对实体经济的反映,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金融经济运行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但金融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非理性运行(如股市的疯狂涨跌),只会为经济泡沫的形成和破灭埋下隐患。
因此,建议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多与符合国家产业投向及政策调控目标的实体经济行业对接,而尽可能限制与虚拟资本或资产的对接。同时,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会加重资金最终使用者的负担,为了防止资金空转,要限制过于复杂的金融工具设计。
鉴于此,我国监管机构必须构建完整的监控体系,建立对金融机构业务全维度监管的一揽子规范,而不是进行打补丁式监管;要切实提高自身的监管水平,并要学会将金融风险进行切割化解,探索市场内在的风险对冲机制;要对国内金融业务或工具创新进行立法,要对新型金融产品工具的推行范围进行适当性评估。通过对银行业金融市场业务全方位分类管理、机构分类管理、业务风险分块隔离,实现有效控制当前金融创新业务风险的目标。
(三)防止国家经济发展出现“过融”之风险
我国必须在国家经济发展效率和经济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选择的最大自由“融”度必须与我国的监管水平、实体经济的规模及健康程度相适应。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发展不能过度依赖透支未来、过度依赖复杂的金融交易。这一点要吸取美国的教训。
第二,不能为了发展,脱离经济基础、脱离国情,过度开发金融产品与工具;不能使金融资产体系衍生迭代过度、链条过长,加剧系统性风险。
第三,要注意引导市场开发设计更多基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或工具,在合适的范围内引入投机对赌机制,切实维护金融业的稳定。
第四,对于虚拟财富在资产配置中的比例必须加以限制,同时不能高估虚拟资产的市场价值。
第五,不能过度规避国家监管政策,将业务与国家限制的淘汰落后行业或高风险行业进行包装对接,把风险引入金融系统。
(四)做好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守护是“融”之终极目标
一国财富安全与“融”息息相关。人类的理想是,世界金融市场风险监管能够做到全球统一协调,但现实中各国国家利益诉求的独立性,各国经济实力、监管水平的差异化,使得在短期内这一理想很难实现。
鉴于此,我国应针对对接国际市场的管道,深入研究设计“融”之机制,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防御体系,既要做到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又要防止国际上“过融”产品或工具盲目地输入或对接国内市场。具体而言:
一是要加强对于国际游资以及结构化产品的入境管理,防止其“狙击”国内某一市场或资产;
二是要引导和控制国家对外投资的规模和结构;
三是要在国家存量财富的配置上多下功夫,采取多样化的积极措施,做好对国家财富的保值守护。
注:1.参见南华工商学院易江解读金融危机[EB/OL].http://news.hexun.com/2009-01-22/113677902.html,2009-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