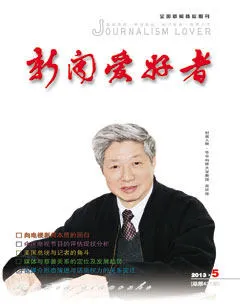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想到的
2013-12-29李彬
据《中华读书报》报道,《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苏联作家鲍里斯·瓦西里耶夫,2013年3月11日在莫斯科辞世,享年88岁。这条新闻,让我不由得浮想联翩。
沐浴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春风的人,对这部中篇小说想来都不陌生。这部作品富有浓郁的诗情画意,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淡淡忧伤的情调,而故事情节却暗流涌动、曲折惊险。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苏联后方一场实力悬殊的遭遇战,一位苏军准尉带着五名女战士,同十六个人高马大的德国伞兵,在一片丛林地带展开斗智斗勇的搏杀,五名年轻战士相继牺牲,留下一曲英雄主义的哀婉悲歌……
以此改编的同名影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更成为80年代令人难忘的文化记忆,与同时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的故事》等佳片一样,使人们在感受深挚的情感波澜时,也体味了颇具俄罗斯风情的美感。影片导演斯坦尼斯拉夫·罗斯托茨基,以本片以及《白比姆黑耳朵》等名作驰誉世界影坛,1992年应邀来北京广播学院讲学,当年第3期《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刊发了其讲学纪要,题为《对未来一代艺术从业者的希望》,《现代传播》首任主编朱光烈教授在“主编札记”里特意写道:
本期正要发稿的时候,著名的电影艺术大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罗斯托茨基应邀到北京广播学院讲学。他不是教师,不是理论工作者,讲的似乎有点散,但是形散而神聚。这个“神”便是处处闪耀着的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和平,热爱和献身于艺术的崇高精神,以及那开阔的、溶通的思路。大师年已七旬,整个讲学全是一生艺术实践的生动经验及其升华,听来使我们许多人激动不已,许多话看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实际上却是无价之宝,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空气普遍浮躁的今天。
清华园南门外的蓝旗营,有家普通超市,毗邻民营书店“万圣书园”。超市现名“金泰”,内辟一间门面不大的特价书店,进的多为价廉物美的经典,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著名译丛书”等。像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精装版《三国演义》,售价仅仅10元。一次,我花了200来块钱,就抱回20余部名著(多数都有):《变形记》《十日谈》《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永别了,古利萨雷》《一生》《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等,以及傅雷先生翻译的《贝姨》、宋兆霖教授翻译的《赫索格》等。那天回复蒋方舟同学的邮件时,也不由得谈到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这本书不记得读过几遍了,每次读都感到心灵的洗礼与精神的震撼。五位女兵,形象鲜明而性格各异,一个个活灵活现,最后各以不同方式殉国,而且死得无不令人心痛。第一位阵亡的姑娘,是个性格文静的高才生,与恋人一样爱读诗歌,在替准尉去取烟荷包的路上,死于德军侦察兵的利刃。由于对方没想到是女兵,一刀下去,扎在她的左胸,没有当即致命,所以发出了一声“微弱、仿佛叹息似的呼唤”。这一声似有若无的呼唤,被经验丰富的准尉捕捉到了。“他的神情逐渐严峻起来。这一声古怪的呼唤仿佛深深印在他的心上,仿佛至今还在耳边鸣响”,准尉的心“顿时凉了,他已经猜想到这一声呼唤意味着什么”。后来手刃凶手后,准尉无比心痛地想到:“索尼娅能够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可是现在这根纱断了。在人类这连绵不断的棉线上,一根细小的纱被一刀割断……”
小说属于战争题材,而主题却是和平,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所示,和平是用英雄的鲜血换来的,诗一般的书名也流露着这一意味。结尾处的一起一伏、一动一静两个场景,更是对比鲜明、寓意深长。“一起”“一动”是准尉怒发冲冠、破釜沉舟、独身一人、硬闯敌巢,用仅剩的一颗手枪子弹和一枚失效手榴弹,逼降最后五个德寇,读者似乎听到他撕心裂肺的怒吼:“怎么样,胜利了吗?……胜利了吗?……五个姑娘,总共五个姑娘,总共只有五个!……可你们别想过去,什么地方也别想去,就得老老实实地死在这里,统统死掉……哪怕上级饶了你们,我也要亲手把你们一个一个毙掉,亲手!让他们审判我好了!由他们审判去!”至于“一伏”“一静”,则是随即过渡的尾声:一片迷人的田园风光,人们尽享安宁、静谧、鸟语、花香,湖畔有人垂钓,还给朋友写信:“我今天才发现,这里的黎明是那样的静悄悄,静悄悄。”如此动静相融的结尾,让人想起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随着梁山伯祝英台殉情时惊心动魄的高潮涌过,音乐迅速滑向余音袅袅的尾声,在如梦如幻的意境中渐行渐远……
俄罗斯文学翻译家高莽先生(乌兰汗),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一部杰出的小说,一本杰出的译著》里,讲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1987年,瓦西里耶夫随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有一天游览长城,高莽同他谈起这部小说及其同名电影在中国的巨大反响。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在一家餐厅吃饭时,随便问起一位女服务员:“你看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吗?”她一愣,不知道这个问题同进餐有什么关系,于是轻轻答道:“看过啊……”高莽说:“这位苏联朋友就是小说的作者!”她一下清醒过来,睁大眼睛,满脸喜悦,惊呼:“我看过两遍!我感动得哭了!”然后,开闸放水,滔滔不绝。她不停地讲啊讲,高莽已经无法翻译。瓦西里耶夫望着她,热泪滚滚,说:“你不用翻译了,我都明白了!”在场的一位卡尔梅克诗人看到这个场面,插了一句:世上有些作家很有名气,大家都知道,可很少读过其作品;世上有不少人知道一些作品,很少知道其作者,这样的作家是幸福的——而你,瓦西里耶夫,就是这样的作家。
类似这样的艺术家或文化巨匠,在苏联以及俄罗斯的历史天宇上可谓灿若星辰,闪闪烁烁。且不说哲学、神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绘画、诗歌等一座座连绵不断的高峰,也不说普希金、勃洛克、莱蒙托夫、契诃夫、果戈理、列宾、屠格涅夫、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格林卡、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高尔基、肖洛霍夫、茨维塔耶瓦、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等精神巨擘,仅看家喻户晓的《克雷洛夫寓言》如《乌鸦和狐狸》,仅听绚丽多彩的俄罗斯歌曲,就足以让人觉得妙不可言、美不胜收——《小路》《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喀秋莎》《神圣的战争》(电视剧《潜伏》的片尾曲即化用这首世界名曲)……
不言而喻,现代中国与俄罗斯及其文化的密切关联,主要源于世界格局的演化,特别是抗衡资本主义野蛮运动的社会主义浪潮在全世界的汹涌兴起。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学者祝东力,在为《凤凰周刊》记者玛雅采写的《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作序时指出:
世界近代史的总体走向是从西方到东方,这个走向在地理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革命”的路线:从英国革命(17世纪)到法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19世纪),再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20世纪),自下而上的、暴力的社会革命一波接着一波,巨浪般由西向东传递。另一方面,相反相成,从西方到东方还伸展着一条“资本”的路线:环地中海(文艺复兴时期)、北大西洋(16—19世纪)和亚太地区(20世纪末至今),依次成为近代世界经济和贸易的热点或中心。第一条“革命”的路线主要走陆路,它在解放了相关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潜力之后,也曾经形成新的异化。第二条“资本”的路线主要走海路,它直接导致了对美洲的种族灭绝、对非洲的大规模奴役,但同时也积累了财富并传播了技术和文明。位于“远东”的中国,作为最后一个被纳入近代世界体系的东方大国,恰好是这两大政治、经贸路线的交汇点。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现代中国一方面深受“国际资本”影响,另一方面又与“世界革命”密不可分;何以一方面与万里之遥的美国“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与近邻俄罗斯“心心相印”。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更对中国革命以及现代中国的旧邦新造产生了“第一推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共产党宣言》到《国际歌》,从共产国际到社会主义阵营,从“苏联老大哥”到中苏论战的“九评”,此间有多少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现代汉语有一个新词汇“司令员”,就是留苏的刘伯承元帅参照苏联红军体制引进并翻译的,之所以用“员”字,也是为了体现官兵平NAD+KCSgw0ye60qiRfRqZ1Xd2PzVfvYpge1xoPULJIM=等、人人平等的观念,犹如司号员、炊事员、战斗员、卫生员、服务员等,都在于突出普通一员,而有别于国军的“司令官”。
学者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对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间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与中苏关系做了翔实考察,为从广阔的时代背景中理解现代中国及其走向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也凸显了现代中国本属现代世界的有机构成,而非自行其是的孤立运动。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少将,在雅俗共赏的“畅销书”《苦难辉煌》里,更以大开大合而生动有趣的笔触,展现了共产国际、日本军阀、共产党与国民党四种政治势力,在中华大地上演的一幕幕活剧。总之,在现代世界的巨变中,中俄两大邻国有诸多相关与相似之处:苏联曾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本营,而中国则是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在二战中都曾遭受法西斯的荼毒蹂躏,伤亡惨重,也都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过首屈一指的贡献,如果“西线”没有苏联红军的英勇奋战和伟大胜利,“东线”没有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拼死抵抗与巨大牺牲,那么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势必沦为人间地狱。为此,《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国人民永不磨灭的心声,如同莫斯科无名英雄墓永不熄灭的火焰——“你的名字无人知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在这一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动态过程中,苏联以及俄罗斯文化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广泛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以鲁迅、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左翼新文化运动,还是成千上万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血青年;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还是普罗大众的思想观念与日常生活,都曾长期以苏联以及俄罗斯文化为楷模、为样本、为“时尚”。俄语以及俄罗斯诗歌、小说、绘画、音乐,如《天鹅湖》、柴可夫斯基、手风琴乐器等,都曾是一个时代的流行风。“文革”期间,能够上映的外国影片一度只有苏联的《列宁在十月》与《列宁在一九一八》,片中高帅忠勇而身手敏捷的列宁卫士瓦西里,是那个年代男孩子的青春偶像。至于高尔基的散文《海燕》,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尼娜》),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写下的“在清水里洗过三次,在血水里浸过三次,在碱水里煮过三次”,以及普希金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更是一代知识青年精神世界的鲜明符号: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2013年,习近平主席作为新任国家元首出访的第一站定为俄罗斯,也不妨视为这一历史渊源的延续,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里谈道:
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我们这一代人也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有着深厚基础。
就新闻而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经由苏联传入中国,并与中国近代新闻传统与共产党的新闻实践相结合,从而成为主导新中国新闻传播的“核心价值体系”。尽管其间不无失误、偏差、变异,但其基本原则与核心理念始终如一,并融入中国新闻业的血脉,包括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等。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记者范敬宜,书生意气,风华正茂。一次,他采访蜚声世界的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写出了一篇辞藻华美的报道。正当他兀自得意时,没想到从解放区走出的总编辑批了八个字:“涂粉太厚,未必是美。”这八个字,让他铭记一生。后来,无论位居人民日报总编辑并写下《总编辑手记》,还是就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并在大学课堂传道授业,他都不忘这个描眉画眼的故事,正如“勿忘人民”的穆青一生记得延安的那个“掌声”。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的原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从学生时代到担任国家通讯社总编辑,一直手不释卷。2008年,他应邀为新华社年轻记者做了一场关于读书的报告,题为《把“阅读”培养成为一种爱好》。在这篇刊发于当年第5期《中国记者》的报告里,南振中还谈到当年通读《列宁选集》的经验:
《列宁选集》第1卷858页,第2卷1005页,第3卷933页,第4卷765页,4卷合计3561页。由于采访报道任务繁重,要在短期内读完这4大本书,的确有一定困难。为了解决读书同时间的矛盾,1973年元旦我拟定了一个总体学习计划:按照每小时平均10页的阅读速度,将《列宁选集》1-4卷通读一遍需要356个小时。如果每天挤出1小时,不到一年就可以把《列宁选集》1-4卷通读一遍。有了这个总体规划,零碎时间就像珍珠一样被串了起来。实践的结果是只用了6个月,就把《列宁选集》通读了一遍。
2011年,可谓新闻学界的“凶年”,当年有数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相继谢世,包括原北京广播学院93岁的新闻理论专家康荫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中国新闻史权威丁淦林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的外国新闻史学者郑超然教授等。放牛娃出身的郑超然教授,天性淳朴,平民本色,乐观豁达,风趣幽默。他与同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名教授的夫人刘明华有对宝贝女儿,夫妇视若掌上明珠,郑老师戏称为“上尉的女儿”。他对我解释说,他在“五七干校”时当过连长,而连长的军衔是上尉。显然,此说来自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一部世界文学名著。
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对苏联解体,自然也同苏联人民一样,百感交集,惺惺相惜。北京有家知名的“莫斯科餐厅”,位于俄罗斯风格的北京展览馆附近,姜文执导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些场景与镜头就出自这家北京人俗称的“老莫餐厅”。苏联解体后,公主坟附近又开了一家“基辅餐厅”,菜肴同老莫餐厅类似,不同的是基辅餐厅雇有一批俄罗斯艺术家,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为就餐的顾客演唱俄罗斯歌曲,有时还唱些中国名曲,字正腔圆,气息悠长,每当餐厅响起“一条大河”“歌唱祖国”等歌声时,现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在餐厅的入口处,挂有一排他们的照片及其履历,大多来历不凡,诸如“功勋演员”“人民艺术家”以及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高才生、国际音乐大赛的获奖者等。虽说道理上都明白“人人平等”“劳动光荣”等,但想到一个曾经傲然屹立的大国解体,而艺术家为此“流落”他乡、“卖艺”为生,情感上总难免有点不是滋味。在长诗《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里,诗人昌耀就直抒胸臆:
看哪,滴着肮脏的血,“资本”重又意识到了作为“主义”的荣幸,而展开傲慢本性。它睥睨一切。它对人深怀敌意。它制造疯狂。它蛊惑人心。
这个世界充斥了太多神仙的说教,而我们已经很难听到“英特纳雄耐尔”的歌谣……然而生命之树常青。人类抗拒不公正历史的脚步不会暂停。
苏联解体错综复杂,一言难尽,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播放的纪录片《苏联解体:八·一九事件内幕》,对此作了全面、深入、详尽的反映,给人留下鲜明印象。结尾处的场景,更觉凄凉酸楚: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黯然离去的当晚,西方正沉浸在圣诞节的欢乐喜庆之中,苏联国旗伴随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悄然落下,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动静,这里的深夜静悄悄、静悄悄……这一场大卫·科茨所称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就这样定格于这幅俄罗斯风情画中而落下帷幕。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里,科茨还对苏联解体中的新闻传播以及意识形态重重乱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迄今仍属最具权威的解读,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巍的有关分析不谋而合:
在苏联,文化领导权也经历了一种微妙的转移,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家手中旁落到了反苏联的苏联知识分子和西方意识形态家的手中。一旦文化领导权旁落,那苏联意识形态家的任何表述,即便是如实的表述,都被当作谎言,而反苏联的人士的任何言论,即便是不实之辞,都被看作真理。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1924年生于苏联的斯摩棱斯克,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参军入伍,后来负伤住院。他创作的30余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多与战争和军人有关。他是“工农兵”中走出的作家,如同那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更是激励了几代中国人: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