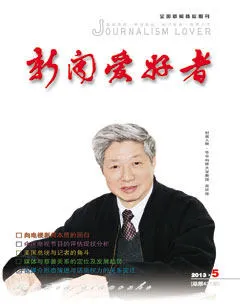“皮格马利翁效应”与人内传播
2013-12-29杨奕陈力丹
【摘要】人内传播的一种心理现象,即“一个有关你的预测,会导致你按照预测的方式行为,从而使其变成现实”,这种现象又称“皮格马利翁效应”。本文讨论了这种传播效应在生活中的三种表现。
【关键词】皮格马利翁效应;人内传播;认知协调
“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一种现象。它体现了一个人面对外界期望或者自身期待时的反应。在此过程中,人与自己对话,达成内在的认知协调之后,才能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这就涉及了“人内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本文的旨趣在于从“人内传播”的角度分析“皮格马利翁效应”,并阐述该效应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及对人们的启示。
“皮格马利翁效应”的由来
古希腊的塞浦路斯岛①曾有一位名叫皮格马利翁的王子。他十分厌恶塞浦路斯妇女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于是立誓终身不娶。这位王子同时也是一位雕刻艺术家。他用象牙雕刻出一尊栩栩如生的绝色少女雕像。反复琢磨、日夜欣赏,最后竟然爱上了这座雕像。皮格马利翁苦苦哀求爱神维纳斯把酷似这座雕像的女子赐他为妻。维纳斯被皮格马利翁的深情打动,并赋予雕像生命,皮格马利翁如愿以偿地和这位少女结为夫妻。
在日常生活中,他人对我们的期待也有可能让我们恰如别人所想的那样成功或者失败,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皮格马利翁效应”恰恰也能够说明这种情形。
1966年,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R.Rosenthal)对一所小学的学生进行了一个“发展试验”。试验结束后,他和助手给学校的老师提供了一份名单,并告知众人:这份名单上被选出来的20%将是未来最有出息的学生。8个月后,他们再次来到这所学校,发现这20%的学生在学习表现和与人相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事实上,心理学家只是随机选取了20%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些成绩和表现很好,有些则不然——成绩落后,也不愿意积极融入校园生活。仅仅只是心理学家权威的“暗示”,使老师们对这些孩子充满期望。孩子本人也从老师的眼神、动作和话语中感知到外界的重视与期待,不断地给予自己积极的暗示,最终验证了心理学家的预言,发展得更加出色。这正如皮格马利翁对雕像的热望使雕像真的拥有生命一样。
因此,人们就把老师对学生的期望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继而转化为自我暗示,最终达成自我实现的现象,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或者“罗森塔尔效应”(The Effect of Rosenthal)。
这个概念起初被运用在教育心理学之中。拓展至传播学领域,可以定义为:他人的期望导致我们真的像期望中那样成功或失败。当然,这个期望的发出者也可以是我们自己。
从“人内传播”的角度理解“皮格马利翁效应”
诗人北岛曾经写过一首诗《生活》,全诗只有一个字“网”。这首诗精准地描述了现代人当下的生活状态:就整体而言,每个人都是社会这张网上的一个节点,人之相与,往来不绝;就个体而言,每个人都身披大网,诸事缠身;在信息的高速路上飞奔,情感与时间皆成碎片与飞沫。在这样的状态下,回归自我,尝试和自己对话,未尝不是一个消解烦恼的好办法。这里,就涉及传播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又称为自我传播,是指人接触到外部信息或刺激后发生在人体内部的信息处理活动。将这个概念分解一下,可以得出自我、信息、内部处理等几大要素。具体分析如下:
“自我”是人内传播的对象。简单而言,人内传播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同自己对话的过程。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讲的就是人内传播。美国心理学家米德认为,“自我”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主我”和“客我”组成。[1]“主我”是自发的、冲动的,具有创造性和行动力;“客我”是反思性和社会意识的自我。“客我”意味着具体的情境,“主我”体现了此种情境下人的反应和行动。“皮格马利翁效应”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在“客我”的层面,人感知到外界对自己的正面或者负面的期待。“主我”对此做出回应。
就过程和效果来讲,人内传播是人自身进行信息处理、达成认知协调的过程。人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境之中,时刻都会接收到形形色色的外部信息,这些信息被拿来同此人原本掌握的信息比对、碰撞便遇到了马克思所说的情形:“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2]125
这种“生命活动”的结果有可能是新信息居上风,也有可能是原有的信息占优势。总之,经过了这个过程,人在内心说服了自己,达到认知协调的境地。这种追求认知协调的情况存在多种可能:人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认知,接收新的信息;有可能增加新的认知,通过新接收的信息来强化、加固原有的观念;也有可能改变认知的相对重要性,认为自己选择的就更加正确;亦有一种结果是改变自己的态度,使新态度与行为相符。
我们可以假设自己是罗森塔尔试验中的一个被试验的学生。如果我原本的表现就很好,那么心理学家的肯定和老师的期许对我来说是锦上添花,我掌握的固有信息(我很优秀)和新接收的信息(你很优秀)是一致的。相反,如果我原先在校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此时就面临一个选择:是维持现状呢,还是在行动上有所改进,使自己的表现符合外界的期待?
可见,“皮格马利翁效应”与人内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皮格马利翁效应”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自己说服自己”的艰难过程。
“皮格马利翁效应”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
结合“皮格马利翁效应”与人内传播,我们可以觅得一些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既对个人生活具有启示或警醒意义,也涉及某个具体行业的发展。
积极的自我暗示对个人至关重要。面对坎坷跌宕的人生,个人应当积极自处。时移事易,积极的自我暗示始终能赋予一个人热情和勇气。台湾作家三毛每天对着镜子说“我很快乐”,以这样的方式来赋予自我正面的期待。面对社会上许多不良现象,很多人迷失了自己或者丧失信仰。白岩松对自己说:“信那些该信的东西,因为它能改变你。因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没法不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②这句话就是典型的“皮格马利翁效应”的运用。人的记忆和信仰都是有选择的。相信那些正直的、对得起良心的人和事,自己也会耳濡目染、感同身受。而对于那些负面的、阴暗的人和事,我们无法也不能忘记,但可以选择不受它们的影响。
个人应当正确认识自己的位置与角色。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125我们每天都要与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打交道,源源不断地从外界接收信息;置身于社会的舞台之上,我们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也观望着其他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应当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持有准确的认知。
震惊全国的“周克华案”就是一个负面的例子。2012年8月14日早晨,多地作案、流窜8年、背负10条人命的周克华被重庆警方击毙。从成长轨迹来看,周克华从小就沉迷于武侠与侦探类书籍;成年之后酷爱枪战、侦探类影片,极为崇尚个人英雄主义。这与他后来极端、凶残的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个例子提醒我们注意“皮格马利翁效应”的负面应用:在生活中,我们总会接触到一些负面的角色或者信息,这个时候应当具备基本的判断力。不要盲目崇拜,更不要一味模仿。否则,对内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对外则会带着怨气和不满为人处世,甚至有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传媒释放正确的期待可以引导公众人内传播的方向。对新闻行业来说,身处众声喧哗的时代,新闻工作者可以利用“皮格马利翁效应”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做好这一点的前提是,新闻工作者本身要行得正,走得直,然后再运用自己手中的注意力资源去释放正确的期待与引导,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养成和行为实践。
央视节目主持人柴静主持的一档节目《看见》,使她访问过很多社会上有争议的人。有期节目中,她访问了中国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彼时,后者刚刚因为伦敦奥运会的“假球事件”备受争议。节目播出之后,许多人质疑节目不该总是访问这种有争议的人物,因为这样易煽动公众情绪。对此,柴静回答:“争议出现,说明社会中新的判断已经开始生长,新旧力量交相汇集,激荡中正可以看见社会变化发展的轨迹和方向。一个公共电视台,在争议中理应提供事实,引起思索,才能平息想象,消解不必要的冲突。不去报道这样的人物,才是漠视自己的公共责任。《看见》珍惜这样的报道可能,希望我们能善用。”③
“善用争议报道的可能”是对电视节目的要求,而“引起思索”“消解不必要的冲突”则是对观众赋予的期待。新闻工作者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示人,而是坐下来和受众对话、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注入平和、理性的态度。这种过程无疑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柴静在博文上的阐释令许多观众备受启发并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有一位观众这样留言:“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当我看不惯一件事情,除了怒斥,还可以静下心来看看对方的转变,在转变中寻找机会,救赎自己的愤怒不平。归根结底,要尽力影响周围的人,营造更适合良性竞争的氛围。”③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不论是个人还是行业,都应当保持内省的常态、时常与自我对话。当然,这也并非一日之功。我们在了解人内传播的常态和具体情形的基础上,当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影响自身的行动,从而达到一个内外协调的目的。
注 释:
①塞浦路斯(Cyprus),希腊语为Κσπροs,早在8000年前就已有定居的村落。前16世纪,希腊人移居于此。古代及亚述帝国时期称之为基提岛。现分裂为两个政权——南部的希腊族政权,即塞浦路斯共和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北部的土耳其族政权,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仅得到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的承认。——笔者注
②摘自白岩松2012年9月1日在重庆大学的演讲《爱你现在的时光》。——笔者注
③摘自柴静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2eixa.html,2012年10月9日访问。
参考文献:
[1]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
(杨奕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陈力丹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