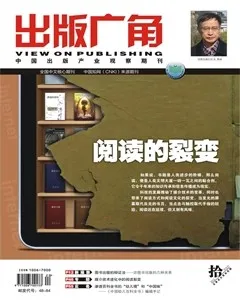王富仁的“呐喊”:中国需要鲁迅
2013-12-29宫立
中国需要鲁迅、中国仍然需要鲁迅、中国现在比过去更加需要鲁迅。
复旦大学出版社“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之《幸存者言》《春润集》《昔我往矣》,记录了钱理群、吴福辉、赵园的经历、感受、思索和体悟以及他们独特的精神姿态,让我得以了解我所尊敬的三位师长从事学术研究三十年的心路历程。如今又读到安徽大学出版社新近隆重推出的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丛书之一《中国需要鲁迅》,虽然这本论文集未能把王富仁研究鲁迅的文章全部编入,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它当做一面镜子,来反观王富仁三十余年的鲁迅研究心路历程以及由此形成的独属于他的精神姿态。
王富仁在《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一书的自序中曾做过这样的表白,“假如有人问我,你最看重哪个中国现代作家?我的回答是毫不犹豫的:鲁迅!”的确如此,王富仁几乎把他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鲁迅研究。无论是写鲁迅,还是写其他什么题目,王富仁始终都在“阐述一种观念,一种与鲁迅的思想有某种联系的观念”,他总是选择以鲁迅的眼光读人读史。
1981年,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据王得后回忆,唯一一个不是代表而被选中了论文的,是王富仁。这一篇唯一一个不是代表的论文——由“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学术活动组”从173篇中选出30篇编入《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是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收入本书的这篇论文只是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一书的总论。王富仁还通过对鲁迅与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的比较研究,阐释了为何“鲁迅前期小说与中外文学遗产的多方面联系之中,它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联系始终呈现着最清晰的脉络和最鲜明的色彩”。
当然,写《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时的王富仁只算是在鲁迅研究界的新人,真正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还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本书所收的《〈呐喊〉〈彷徨〉综论》是他博士论文的“摘要”,在《文学评论》1985年第3、4期一经刊出,就引起极大震动。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我们应该“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主导创作意图!首先发现并阐释《呐喊》和《彷徨》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他的主要观点是要区分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并把鲁迅放在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潮流中来理解和分析,《呐喊》和《彷徨》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在这个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里被折射出来的。王富仁此时的研究就是想努力摆脱凌驾于自我以及凌驾于鲁迅之上的另一种权威性话语的干扰,用自我的现实人生体验直接与鲁迅及其作品实现思想和感情的沟通。
李大钊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中曾说,“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限制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可谁能想到一篇博士论文竟然被某些人扣上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研究”的罪名,比如陈安湖在《写在王富仁同志的答辩之后》中就说,“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来检验,我觉得确乎可以说,他已经从根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可王富仁正如他的研究对象鲁迅一样,并非是可以随意就被吓倒的人,他有山东人的倔强脾气,他无视这种非学理的责难,继续他的鲁迅研究征程。
王富仁的专著《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结合他对中国社会和鲁迅研究的思考,简略地考察了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梳理了中国鲁迅研究演变的历史脉络,并对鲁迅研究的前景作了概略性的预测。当然他对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更多地侧重于论,而非史料的梳理和发掘。鲁迅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有的侧重于鲁迅思想家的侧面,有的侧重于鲁迅文学家的侧面,而王富仁坦言他更为重视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侧面,本书中所收的《鲁迅哲学思想刍议》即是证明。正如高远东所说,“鲁迅的文学是在文学者鲁迅与思想者鲁迅的关系中发生的,思想者鲁迅先于文学者鲁迅出现,鲁迅的文学则是二者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同的人阅读鲁迅的作品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人眼里的鲁迅自然也就各有不同。王富仁继而又写了《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单从书名就可知他眼中的鲁迅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始终清醒的“守夜人”。本书所收的《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鲁迅与中国文化》即是对“中国文化的守夜人”这一观点的详细阐述。
大体勾勒完了王富仁鲁迅研究的轨迹之后,我们再对他的研究特色和行文风格略作分析。关于这一点,已故的樊骏作过最精确而又最简洁的概括:“王富仁有良好的艺术鉴赏能力,但更多地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问题,他总是对研究对象作高屋建瓴的鸟瞰与整体的把握,并对问题做理论上的思辨。在他那里,阐释论证多于实证,一般学术论著中常有的大段引用与详细注释,在他那里却不多见,而且正在日益减少。他不是以材料,甚至也不是以结论,而是以自己的阐释论证来说服别人,他的分析富有概括力与穿透力,讲究递进感与逻辑性,由此形成颇有气势的理论力量。他的立论,也往往是从总体上或者基本方向上,而不是在具体细微处,给人以启示,使人不得不对他提出的命题与论证过程、方式,作认真的思考,不管最终赞同与否。他是这门学科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不管是他的博士论文还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研究专著,都鲜明地体现了樊骏所说的这一点。虽然王富仁是“最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但他的文章明白如话,绝不是八股文式的“高头讲章”。钱理群的文字是富有激情的,“堂吉诃德”式的呼喊,王富仁的文字则是老年人的“呓语”,虽然絮絮叨叨,但只要是认识汉字,能说中国话的人都可以读得懂他的文章。他的学术文字正如他每次报告的口头禅一样,是“闲聊天”式的文字。我认为最好的文章(不仅仅是学术论文)都应该首先做到“明白如话”,也许只有做到了“明白如话”,“每一个词句就像一个漆弹打出来,要击中人,在人的身上破掉,最好颜色再染进他的衣服”。
当然王富仁除了具备深厚的理论思辨能力,对文本细读的艺术鉴赏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本书中收录他解读的《狂人日记》《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学界三魂》《青年必读书》等篇章,尤以从语言的艺术角度对《青年必读书》的解读最为惊艳。鲁迅的这篇文章一直引起各种争议,存在各种误读和误解,这是笔者目前看到的解读《青年必读书》最为精彩的篇章。他说,“只要我们不以自己的先入之见轻率地对其进行否定性的判断,只要我们愿意理解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会更切实地考虑当今中国青年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就会更切实地考虑他们的实际需要,同时也会更切实地思考中国书和中国文化以及外国书和外国文化”,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不断丰富这篇杂文的具体内容”。
鲁迅研究者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自身的研究让更多的人走近鲁迅,了解鲁迅,以至理解鲁迅。面对关于鲁迅的各种质疑,作为资深的鲁迅研究者,王富仁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章培恒所言,直到今天,鲁迅“仍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具有最大影响的一个,但同时也是受歪曲、污蔑、攻击最甚的一个”。对于部分作家、学者非议甚至否定鲁迅及其鲁迅研究这一现象,王富仁在接受访谈时,曾说这是正常现象,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是一个“焦点人物”,鲁迅研究也是一个“焦点问题”,“对某一个焦点人物或焦点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同时,每一个人也应该承认别人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同时,每一个人也应该承认别人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而不能对别人的异议采取一种不能容忍的态度,或通过外在的力量来压制不同的意见”。但是他同时强调,“作为一个作家或者研究者,他对鲁迅及鲁迅研究的异议应该来自于他对鲁迅及鲁迅作品的真实思考,而不应该是来自于他的某种主观需要,如通过发表对鲁迅及鲁迅作品的异议来泄私愤。”也就是说,“研究鲁迅应该从鲁迅出发,非议甚至否定鲁迅也应该从鲁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印象出发,更不能因为不能或不敢正视现实人生的实际问题便把目光转移到鲁迅身上,企图通过鲁迅来发泄自己对某些现实问题或现实人物的不满。”他在本书的前言《我和鲁迅研究》一文中,从外国文化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现状四个方面对非议甚至否定鲁迅这一现象之所以产生的文化背景作了细致地解读。
王富仁2011年在《文艺报》撰文《中国需要鲁迅》,说“关于鲁迅,我已经说过太多的话,至今仍然有许多话想说。我现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我现在最想说的话就是:中国需要鲁迅、中国仍然需要鲁迅、中国现在比过去更加需要鲁迅”,因为鲁迅的思想就是“立人”思想,过去需要“立人”,现在需要“立人”,将来仍需要“立人”。记得康德曾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任何东西都无权逃避批评。如果宗教想以神权的名义,法律想以威权的名义逃避批评,那么只能加深人们对它的疑惑,从而丧失它们尊严的地位,因为只有经得起由理性和自由所做的公开审查的东西,才是配享受理性的尊崇的”。因此,我相信时间将会证明,无论是鲁迅,还是王富仁的鲁迅研究,都能“经得起由理性和自由所做的公开审查”,并且也值得拥有“理性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