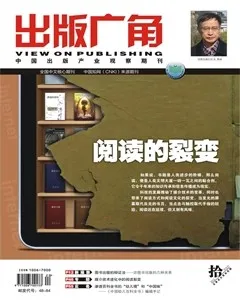媒介技术进化中的阅读裂变
2013-12-29周捷王炎龙
网络环境下,阅读行为不断向数字化靠拢,经历着“媒介技术裂变—传播载体裂变—阅读方式裂变—阅读文化裂变”的路径演化。
在传播技术革命进程中,媒介样态涌现与融合,新旧媒介交替或取代,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公众经常无所适从,人们创造新技术,同时又不断被技术所驾驭。重读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俯身审视这个信息社会,会发现这位预测家提出的“比特时代”“人性化界面”“数字化生活”已经成为现实,而且还在往前推进。无怪乎他说:“当我们日益向数字化迈进时,会有一群人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1] 自互联网诞生发展至今,人们在海量信息中获得体验,在体验中逐步失去自我。这种体验,就是碎片化阅读,一种过度依赖媒介技术的“阅读崇拜”。
技术进化中的多元阅读与偏好
阅读是“大脑接受外界,包括文字、图表、公式等各种信息,并通过大脑进行吸收、加工以理解符号所代表的意思的过程”。由此可见,阅读是读者解码,同时也是重新利用自己脑内储备知识进行意义再建构的过程呈现。
历史上,我国人民最先通过甲骨文记事和获取信息,这是古人早期阅读的雏形代表。进入农业社会,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和由上至下的纵向型社会结构在客观上造就了传统阅读的小众化与单一化。技术革命后的工业社会,传统阅读转型为现代阅读时代。工业社会的环境要求人们的阅读内容更偏向于实践,阅读的性质也更具有功利性。而在信息社会,开放与快速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阅读的黄金时代,阅读这种行为也终于由少数人的“寂寞”变成了多数人的“狂欢”。
达尔文的进化论曾经描述了生命起源和演化的过程,其意义却不仅限于生物界。英国社会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世界是可以类比的,文明的进化就是不断趋向于某一个理想目标的进步过程。而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进化论”。[2] 那么,阅读又如何呢?从甲骨文到数字化,从单纯的纸质阅读到多元的数字阅读方式,这正是进化的特征。
在这一进程中,不同的技术给阅读带来了不同的变化。当下,新技术主要表现为互动技术、数字技术与宽带技术。互动技术强化了信息的反馈与交流,改变了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模式,也使传统的单线阅读变成了交互性的阅读;数字技术注重存储,使信息呈现碎片化趋势,也使阅读更加便捷,增强了阅读的移动性;宽带技术注重信息传输,使可阅读的对象变得海量,也让信息的传输更加快捷,同时大大提升了阅读的效率。
2013年4月,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3] 显示,2012年我国国民(18—70周岁,下同)图书阅读率为54.9%,比2011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76.3%,比2011年下降1.3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国民报纸阅读率为58.2%,比2011年的63.1%下降了4.9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45.2%,比2011年的41.3%上升了3.9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DA/MP4/MP5)方式的接触率为40.3%,比2011年的38.6%上升了1.7个百分点。另外,纸质图书的阅读率连续7年保持稳步提升的态势[3] 。从这些数据和阅读率来看,虽然纸质图书和期刊的阅读量有所上升,但是仍旧改变不了国民图书阅读综合阅读率下降的现状。
调查中,超过五成的18-70周岁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较少,而接近七成国民希望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这一比例比2011年增加了6.6个百分点。国民对于阅读的期许和自身阅读量的稀少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的现象也体现了他们对于阅读渴求的急迫度。然而当前的阅读环境却不能满足这种“迫切”。如今正是我们进入信息社会的过程,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在各种终端上即时上传、共享与更新构成了“井喷式”信息爆炸,信息的海量达到了一个制高点却也让我们陷入了一个被动式的阅读环境。已经习惯了信息自动供给的阅读者似乎已经丧失了翻阅书刊、经典的主动性。
阅读裂变的路径阐释
网络环境下,阅读行为不断向数字化靠拢,经历着“媒介技术裂变—传播载体裂变—阅读方式裂变—阅读文化裂变”的路径演化。
媒介技术裂变。阅读对象和知识储备是产生阅读行为需要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众多事实证明科技进步是满足阅读条件的前提。11世纪,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克服了雕版印刷术的弊端,提高了印刷效率,带来出版物激增的同时也使阅读的对象日趋丰富。n9gucpkUwbiDaXk4GPxfpRdp9Om+9P5ZA3W6XtPeGN4=15世纪,德国古登堡改善的活字印刷术在欧洲迅速普及后,短短50年内就已经印刷了三万种印刷物,共计12万份印刷品。可以说,古登堡印刷术导致了一次媒介革命,迅速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18世纪,产业革命发生,蒸汽机的诞生及其在出版印刷机械上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19世纪50年代以后,以电报、电话为代表的电子信息技术出现了,利用这项技术,人类的声音和信息的传播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范围。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电影、无线电广播、电视、录音录像技术的相继诞生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以模拟式电子传播为代表的大众传播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网络化和数字化则成了当代传播的时代特征。媒介技术正在不停地提供着阅读对象,而阅读对象的增加是知识储备提升的前提。
传播载体裂变。如果说媒介技术是阅读行为产生及变化的前提,那么媒介的不断完善则是促使阅读裂变的关键。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他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比起各个时代提供给人们的信息,媒介本身才更具有意义。麦氏将媒介的作用放大到了极点,我们无需模仿伟人的思维,只需要借鉴他对于媒介重要性态度的重视。从口头传播到现在的网络传播,媒介的发展历经了从早期的符号媒介到手抄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然后到现在的新媒介的过程。“新媒介并不是自发地和独立地产生——他们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产生。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他们会继续演化和适应[4]。” 证明这一结论的最好证据就是现代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共存和互相融合的现状。罗杰·菲德勒认为“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4]。” 如果用另一个理论来解释菲德勒的话语的话,即:传播媒介的变化受到传媒生态环境的影响。传媒生态环境是指传媒开展传播活动以及自身生存发展所涉及的环境条件。传媒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一个子环境,它与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信息环境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媒介系统正是运行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所以,传媒生态对媒介的发展水平、运行方式、传媒资源、媒介资源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推断互联网的诞生就是当代传媒环境对媒介提出的一个必要要求呢?当代社会是一个讲求速度和便捷的信息化社会,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量之大和对信息需求种类之多给传统媒体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在这样的传媒生态环境下,整合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多种传播渠道的高速快捷的传播方式网络就出现了。麦克卢汉曾预言“地球村”的出现,而后互联网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转变正在不断地验证着这个假设的正确性。
阅读方式裂变。我们目前正处于第三次的媒介形态变革当中,而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信息化和数字化,一切都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数字化和信息化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迅速快捷,人类进入了一个“加速世界”。在这个“加速世界”里,相较于以前,每个人都必须尽可能地节约时间去提高效率,当然,这个效率是体现在社会各方面。不管是微博的短小精焊还是微信的语音短信,无疑都更注重效率和迅捷。人们需要了解这个世界,为了不被“out”而拼命努力,门户网站和微博上提供着海量的信息,凭借着不断被发明的移动终端,人们随时随地的信息需求完全得到了满足。结果就是,新型简洁的“快餐式阅读”应运而生,正餐式的经典传统阅读似乎遭到了威胁。进入信息社会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典阅读都占据了统治地位。正餐式的经典阅读更注重阅读的品位和质量,注重阅读带来的心灵感受和精神思索[5] 。它强调思考和细嚼慢咽,更注重理解和融会贯通,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概括为一种“慢”阅读。不同于经典阅读,“快餐式阅读”是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而兴起的,它是一种当人们在忙碌中度过每一天的时候,可供人们消遣休闲的阅读方式。快餐式阅读以一种无目的的随意性浏览,放弃思维的辅助,成为填充大脑中暂时的空白状态的消遣。它或以新颖荒诞的视角,或以大量具有视觉冲击的图片,诸如卡通、科学幻想、生活幽默等等,来博得人们轻松一笑[5] 。这是一种符合现代人生活方式的阅读,所以越来越受到当前受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喜爱。
阅读文化裂变。阅读行为的转变必然会引起相应的阅读文化的变化,那么,阅读文化又指的是什么呢?有学者通过对文化理论、阅读行为、读者和文本的考量,总结为:阅读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形态和物质形态基础上,受社会意识和环境制度制约而形成的阅读价值观念和阅读文化活动[6] 。既然阅读文化要受到社会意识和环境制度的影响,那么当前不断处于“加速”的社会环境是否影响了阅读文化的发展呢?答案是肯定的。学者周蔚华根据社会形态特征将阅读分成了古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阅读阶段,认为据此也会产生三种阅读文化,即古代阅读文化、现代阅读文化和后现代阅读文化。后现代的阅读是在信息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注重效率和迅捷,放松思考与深入。在纸质阅读盛行的年代,古代阅读和现代阅读都是传承着经典的线性阅读模式,但是新技术的发明和普及使得受众作为传播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得到了强化,它不仅让传统阅读中的单向传播模式转变成了互动性的现代阅读模式,还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从单渠道变成了多渠道。网络化的现在提供给当前阅读模式最大的改变就是非线性和跳跃式的碎片化阅读模式。碎片化现象不仅使传统的话语方式和消费模式被瓦解,还使受众细分成了不同的群体,同时引发受众个体的信息需求,从而导致整个网络传播呈现为一种碎片化的语境。而这种碎片化的语境正是当前后现代阅读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阅读碎片化与信息网络化的体验迷失
碎片化的视觉式浏览,让电子阅读成为一种消遣与体验。“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国民的阅读率从最初60.4%提升到了如今的76.3%,人均年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也达到了4.39本,虽然与国外发达国家有差距,但从数字上来看似乎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另一方面,以手机阅读为代表的新兴阅读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热爱。既拥有互联网的资源上传与共享的功能,又享有小巧便捷、可随身携带的天然优势,手机网络从最初的网络附属品发展到今天,成为传播媒介和阅读载体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似乎本来就有一种必然性在。作为依附互联网的阅读方式,各种移动的阅读终端的出现和更新无疑给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阅读方式,同时也通过网络共享提供了更多的阅读内容。亚马逊和巴诺书店在2011年10月相继推出Kindle Fire和Nook Tablet,到2012年3月,其几百万台的销量已将电子书发行站整个图书发行的比例提高到了6%,很快又将突破8%。购买Kindle Fire的用户中,为了阅读电子书的占到了71%。
信息网络化的“浅阅读”,使读者容易在短暂式信息消费中迷失。“全国少年儿童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中国7-14岁的少年儿童每个学期平均仅有3本书的阅读量。《透视大学生的“浅阅读”》报道,现在部分大学生很少读经典名著和“大部头”的书籍,以流行、时尚、省时、省力的“快餐化读物”和轻松、有趣、缺乏思想内涵和人文底蕴的“浅阅读”为主[7] 。网络大发展的环境下,阅读似乎出现了危机。让我们再来解读一下如今流行的“快餐式阅读”。快餐式阅读的过程,是人们利用网络搜索信息时主动或者被动地接收信息的过程,无目的性和盲目性是它的特点,它不讲求精深,只需要高效。所以,快餐式阅读从诞生之始就伴随着天生的缺憾,缺乏思考和深度,这是快餐式阅读最遭人诟病的地方。说到思考,我们现在似乎陷入了一个极端化和片面化的思考模式,对于一些问题不仅不能系统地进行解答,甚至做不到客观公正的分析。心理学上的阅读崇尚的是把一条条思维的“线”转变为一张“网”[8] ,但是数字世界里的零碎化阅读却无法把“线”织成“网”。网络提供的高效却零碎化的信息正是这一条条的“线”,这可以让我们更快更迅速地知道这个世界,但无法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这个世界,数字化容易让人思维产生惰性而缺失系统与理性。原本时间和思考的堆砌是知识积累的基础,很少受到外界干扰的宁静是传统阅读的环境,但是数字化社会的高速和喧嚣却提供不了这样的环境。所以,公众在畅享信息的同时,也在信息里迷失。
网络便捷与技术发展推动了阅读革命,但如何在数字世界里避免思维和思想支离破碎,需要每个人思考。很多时候我们感叹自己知识缺乏,抑或思维贫瘠,很少有人会想到阅读方式出了问题。我们应明白阅读量不是能用“刷新率”能代替的,经典也不是“转发量”所能衡量的。当我们可以凭借自身知识储备,带着明确目的性,不依靠“链接”来进行逻辑思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被信息化社会所绑架。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 尼葛洛庞帝.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M] .三亚:海南出版社,1997.
[2] [英] 苏珊·布莱克摩尔.高申春等译.谜米机器.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3] 蔡华伟.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N] .人民日报,2013-04-19.
[4] 罗杰.菲德勒. 明安香译. 媒介形态变化:理解新媒介.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5] 武少民. 从快餐式阅读中突围[N] .中国教育报,2003-07-17(6).
[6] 王余光、汪琴.关于阅读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 . 图书·情报·知识,2004(5):3-7.
[7] 袁跃兴.拯救 阅读危机[N] . 徐州日报,2010-06-01(10).
[8] 李晓源.论网络环境中的“碎片化”阅读[J] .情报资料工作,2011(6):P8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