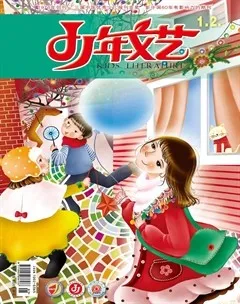鱼爷
2013-12-29郑孝文
张大爷晚年的时候,决定拿出点积蓄,弄个小鱼塘。
人家问他:“张大爷,您就在家中享享清福呗,何必弄个鱼塘来操劳呢?”
张大爷躺在椅子上,抽着烟,笑而不答。
张大爷的儿子顺子站在一旁,无奈地对邻居解释:“我爸就是这样,一辈子不愿歇会儿。”
一个灰蒙蒙的雨天,掘土机来了。村里人吆喝着:“瞧!掘土机!”这样一个偏远山脚下的小村子,总共只有百来户人家,谁家要是有点新鲜事儿,便会引来全村人围观。人潮一会儿就涌上来了,李三娘家的小甲子,杨大嫂家的小玲儿,连吴老爷家的小太岁也来了。众人好奇地打量着这庞大的机器,议论纷纷。
王大伯问顺子:“你爸拿那么多钱砸到鱼塘里,你就不心疼么?”
顺子踮着脚尖往人群里望,回过头来对王大伯说:“他老人家的积蓄,我心疼顶什么用?”
掘土机很快在村边挖出一个大坑来,坑的周遭,堆叠着大堆小堆灰黄色的泥土,雨丝打落在泥堆中,很快冲淌出一道道深黄色的泥浆沟。
即使下着雨,围观的人也不见少。有的是跟着掘土机跑来的,有的是听人说起赶来凑热闹的,还有的是看到了村道上掘土机驶过的痕迹,觉得蹊跷,也跑过来了。
小甲子就是后面的那种。看见路上的车迹,赶忙去唤小玲儿和小太岁,不料他们早跑去看热闹了,只得一个人跑过来,气喘着说:“怎么不等我呢?”
一时间里,张大爷请来掘土机挖鱼塘的事儿,传遍了整个村子。
张大爷安然地躺在椅子上抽烟。人家问:“张大爷,你这是为何呢?”
张大爷还是静静地躺着,睁着眼,没有答话。
“这老头子快疯啦!”隐约有人嘀咕。
可不久人们便慢慢懂了:纵使大伙儿说破嘴皮,张大爷也不会轻易改变想法。每日照常来看掘土机挖鱼塘。
整整挖了三天,张大爷热情地将工人师傅请到家中,付了工钱,陪着吃了午饭,笑呵呵地将他送走。
人们高声地喊:“嘿!掘土机要走啦!”
围观的人群又跑到街上,站成两排,恭恭敬敬地让开路,仿佛要送走一位贵宾似的。
这样折腾了好一会儿,围观的人群才各自散去。
又过了一天,邻家王大伯问:“老张啊,你家的鱼塘弄好了?”
“还没呢。”
张大爷从镇子上请了个施工队。这些工人是来修塘沿的,沿着两米多高的鱼塘,铺起一面面水泥墙,封闭得像个大盘子,只在塘边上留了一个排水的口儿。
张大爷远远站着,大声喊:“还要在塘边搭个凉亭子。”工人们应了一声。
施工队没有掘土机来得热闹,大多数农夫都干过这样的活儿,不足为奇,提着锄头下地去了。但也有观众,都是些无事做的老人和小孩。
村西四岁的小虎子,呆呆地坐在一段倒下的枯树干上,看得出了神,被邻居的小玲儿从背后吓了一跳,赶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尘,自豪地对大伙儿说:“我将来长大了,肯定也要当个工人的!”陈二奶奶笑着打趣:“哟,小虎子都有理想了呀!”
张大爷从屋里拎出一壶茶水,一边倒茶,一边招呼:“大伙儿都过来喝茶吧!”工人们放下手中的活儿,走了过来。
小甲子立马从小伙伴那儿跳出来,歪歪趔趔地跑到张大爷面前,接过一碗茶,笑着夸张大爷的手艺:“张爷爷,您家的茶可真甜!”可不是,工人们接过茶,喝了两三口也都说甜。
修塘沿虽然没有掘土机那般稀奇,却也要做上四天的活儿,所以那些未念书的孩子,每每帮父母干完活儿,也都往鱼塘这边跑。
工人们按张大爷的意愿,在鱼塘的东边搭起一个凉亭,用的是村子里边的竹子,现成的没人管,只有用得着的时候人们才提着镰刀去砍。
送走工人,张大爷从家里搬出一张躺椅,靠在凉亭里,抽着烟,对着天空自言自语:“这几天真是好天气呢!”
王大伯望见了张大爷,凑过来问:“老张,鱼塘弄好了?”
张大爷笑着说:“就差引水养鱼啦!趁这几日天气好要晒塘沿,我得去挖一条渠沟……”
第二天张大爷便带上锄头,跑到最近的小河边,咚咚地挖起来。儿子看见了问:“爸,您这是干啥呢?”张大爷回答:“挖渠沟啊,不挖渠沟怎么引水?”
张大爷挖了两天,才把小鱼塘灌满了水。
“鱼苗呢?”王大伯问。
“昨天从镇子上买回来哩!”
于是张大爷一早放了鱼苗,办起鱼塘来。
自打有了鱼塘,张大爷便每日守在鱼塘边。他静静地抽着烟,静静地望着鱼塘,笑眯眯地看那鱼苗吐出一颗颗泡泡来。
人家问他:“张大爷,您老整日坐着不孤单么?”
“有鱼儿陪着呢。”张大爷眯着眼,笑着说。
说久了,有人便听出几分“味道”来,管张大爷叫“鱼爷”了。鱼爷并不敏感,随大家叫去。
有一日,王大伯问:“鱼爷!你的鱼苗咋样了?”
鱼爷从兜里掏出一袋儿烟草,装上烟抽了一口:“我正看着呢。”
鱼爷看管鱼塘,日复一日,在凉亭里边或躺或坐。
一个雨天,小甲子光着脚丫,扛着小锄头,从田里修墩回来,路过鱼塘,看见塘里鱼儿吐出来的小泡,说:“鱼爷,您这儿的鱼真多呢!”
鱼爷半躺着,安静地看着塘边的浮藻,听见小甲子的声音,坐起身来,“可不是!赶明儿钓上几条尝尝鲜。”
“钓?鱼爷您这鱼塘可以钓鱼吗?”小甲子惊讶极了。
“可以的,赶明儿小甲子过来钓。”
“好嘞!”小甲子抖着斗笠,甩了几下衣襟,走远了。
一个大晴天。小甲子提了一根刚做成的竹鱼竿,拿着蚯蚓罐儿,领着小玲儿和小太岁,往鱼塘这边过来了。
“鱼爷!您说话得算话!”小甲子这口气,真是有点大人的味儿。
“好着呢!”鱼爷应着,顺手指向漂满浮藻的那一片,“那块儿鱼多。”
小甲子顺着塘沿,找来一块大青石,坐定,回头招呼小玲儿和小太岁:“你们俩快过来!”
小太岁罐儿里的蚯蚓并不多,钓鱼竿也是略微发霉的,敢情对钓鱼没抱多大的指望。然而有鱼钓总是好玩,他和小玲儿跑过去,一个挨一个坐定,往鱼钩上挂饵了。
顺子血气方刚,快二十七了,还没成家。这会儿从屋里出来,远远望见三个钓鱼的小人儿,扯开嗓子大喊:“好厉害的三个钓鱼贼啊!”
钓鱼一旦跟“贼”联系起来,那便是不得了了。小甲子吓了一跳,眼睛瞅瞅凉亭里的鱼爷,很快安下心来。
鱼爷发话了:“是我让他们来的。”
顺子一看老爹站在亭里说话呢,跑上前去,“爸,咱自家的鱼,你让别人来钓?”
鱼爷见儿子生气,便打趣说:“办鱼塘不就图个乐么,再说那些孩子未必个个是钓鱼能手。”
正说着,小甲子“嘿呦”一声拽上来一条大鲫鱼。顺子越过鱼爷的肩膀瞧见,气得直跺脚,恼火地走了。
一个时辰的工夫,已是半桶塘水半桶鱼,小甲子与小太岁歪歪趔趔地将水桶搬到凉亭下,小玲儿跟在后边,手里抱着鱼竿和蚯蚓罐儿。
“这鱼要怎么分?”小玲儿跑得气喘,歇了一会儿说。
小甲子觉得“分”字有些刺耳,毕竟是钓人家的鱼,总有些不好意思,于是装出几分成熟来,“让鱼爷发话!”
鱼爷一皱眉头,有些不高兴,“分就分,耍什么心眼!”
鱼爷毕竟是鱼爷,三个娃儿折腾一个下午,岂能让他们空手回去。
“我拿两条,小甲子和小太岁各拎两条,小玲儿是女孩儿,得要三条,这不得了。”鱼爷的手在桶里翻了几下,瞬间分好九条大鱼!
三个娃儿各自拎着鱼,乐呵呵回去了。
过了几日,鱼爷提着两条深黑色的鲫鱼,到村西串门,遇上小太岁的爷爷吴老爷。吴老爷住在村西,待人和善,声誉顶好。吴家是村里唯一住小洋楼的人家,大伙常说:“吴家有福气!”
吴老爷不善言语,见人总是会心一笑。这会儿见到鱼爷,老远就搭话:“鱼爷,前两日小太岁带回来的鱼儿,味道真鲜呢。”
鱼爷一惊,忙应着:“您要是喜欢,赶明儿叫小太岁再来钓。”
“这不大好吧?”吴老爷有些不好意思。
“没事,您要是喜欢,就叫他常来。”这是真心话,鱼爷养鱼就是图个乐。
过了两日,小太岁和小甲子他们来钓鱼了。
鱼爷在椅子上躺厌了,走到娃儿身旁,看他们钓鱼。
三个娃儿果然都是能手呢,一个个光着脚丫儿,贴附在油亮的塘沿边,竟没掉下去。红塑料桶里有几条黄黑色的鱼,三个玻璃罐儿,装着黝黑的土。
鱼爷还在瞅罐儿里乱窜的蚯蚓,小甲子突然大喊:“这鱼好大的劲儿!”
“我来帮你!”小玲儿跑过去。
不料那鱼一使劲,小甲子转了个身,猛地撞到小玲儿,小玲儿歪斜着身子滑到水里。
八岁的小孩,两米多深的鱼塘,小甲子慌着喊:“鱼爷!鱼爷!小玲儿落水了!”
鱼爷也慌了,虽说是“鱼爷”,却不识水性,赶紧跑到路边呼救。
人救上来的当晚,张家的院子里聚满了人。
鱼爷接到镇上治安员的通告,不许小孩再到鱼塘边去。人们议论开了:“鱼爷这会儿该悔恨了,当初劝他他不听……”
鱼爷的儿子也站在一旁,跟着人们指点着:“爸,我早说别让他们钓鱼来着,你看怎么着……”
鱼爷病倒了。他躺着,连日地咳嗽。
鱼爷的房间里挤满了人。有人说:“昨天我来时,鱼爷捧着‘鱼奶奶’的相片儿,念叨着‘我该去陪你了’。”
有人接:“鱼爷!您可走不得,您走了您家的鱼塘怎么办啊?”
顺子嚷嚷:“你们别胡说!”
王大伯匆匆赶来,见了鱼爷,脸一沉,厉声说:“快!送医院!”人们这才一惊,纷纷说送医院。
救护车来了,顺子在医生后边跑。忽听有人说:“怪啊!怎么现在才送?”
顺子又愧又恼:“说什么呢!是他老人家不愿意!”
顺子一直忙到深夜才回家。
第二天,顺子收拾好衣物,准备暂时搬到医院去,远远望见鱼塘边亭子下的红桶,扫眼过去,三个娃儿又在那儿!
气汹汹地走过去,一脚踢飞蚯蚓罐儿:“怎么着?你们三个兔崽子还敢来!”三个娃儿吓愣了,又惊又怕地望着顺子。顺子夺过娃儿手里的鱼竿, “啪”一声,折断了。
小甲子战战兢兢地上前解释:“顺子叔叔,我们只是想钓几条鱼,送到医院去。”
“别叫我叔叔!谁是你们的叔叔!”顺子攥着断鱼竿怒不可遏,“叫你们顶嘴!”一棍子下去,三个娃儿都哭了。
鱼爷走的时候,下了一夜雨,雨水涨满了鱼塘。
送鱼爷的时候,顺子在前边捧着遗像,狭小的村道,嘈杂地挤满了送行的村民。李三娘领着小甲子,杨大嫂带着小玲儿,吴老爷牵着小太岁,三个娃儿连声哭泣,比大伙儿都伤心。
一周后,儿子卖了鱼塘。
突然听说鱼爷的儿子要办喜事,大伙儿又凑到了张家的宅子里。王大伯吸着烟,平淡地说:“这刚办完丧事,要办喜事总不大好。”
儿子被说得愧了,将喜事推迟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掘土机又来了,一日便把鱼塘填平了。
而后再谈到鱼,大伙儿常叹息着说:“鱼爷走啦。”
发稿/田俊 tian17@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