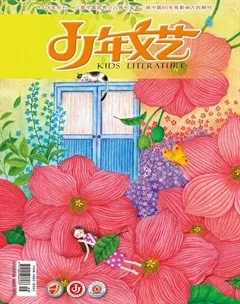猛犬暴雪
2013-12-29牧铃
自从把创作重心移向“大自然写作”,我一直在作这样的努力:尽可能客观地描写真实的动物,让动物小说的主人公走出人类为之设定的某种角色;更不以人类的道德观去衡量动物的所作所为。于是引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那些以人类的眼光看去确实犯了“不赦之罪”的家畜和野兽?
“暴雪弑母”是我亲眼所见的惊悚场面之一。我如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以及那一刻的感受,却没能对那个问题作出正面解答,留下的依然是一系列问题:
假如不经过人的“教化”,暴雪会干出那种事吗?
对动物的成功驯化,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不是对其天性的扭曲?
小说的任务不是提供答案。而对成长中的少年读者来说,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或许比提供一个现成答案更有意义。
我知道,今天的少年读者,会以平和的心境平等地看待所有动物。而动物的可爱,并不是看它们能否取悦于人类,恰恰在于它们天性的自然流露——就这一点而言,野生动物远比家禽家畜要幸运得多!
一
暴雪是我十四五岁当“牛仔”期间结识的一条牧犬。
说“结识”有些夸张。因为这个高傲的家伙压根儿没正眼瞧过我——我只是一名不起眼的小徒工,它却算得上一个元老级的“人物”。五年前,老场长创办牧场,它母亲便随一批怀孕的良种奶牛远渡重洋而来。
那会儿,暴雪还在母亲的肚子里。
一个月后,暴雪成了新牧场上降生的第一条小牧犬,而且是独生子。于是小暴雪得到牧工们无微不至的关照。它被畜牧组长曹胡子看中,作为牧犬头儿的苗子培养起来。
曹胡子性格暴躁。他驯狗的首要标准就是“绝对服从”。据他的理论,唯有充分发挥出狗的奴性,让狗为了主人甘愿赴汤蹈火,才能培训出所向无敌的猛犬;而饥饿和棍棒,则是他“挖掘动物奴性”的两大法宝。
暴雪经受住了考验,以出类拔萃的体力和勇猛受到牧犬们的拥戴,当上了头儿。从此,这片山地牧场周边食肉猛兽骚扰牧群的行为有所收敛。一次身先士卒驱逐老豹的壮举,暴雪又给了曹胡子莫大的启发;老曹认识到,牧场不能老处于防御地位,对付野兽,应该像暴雪似的主动出击。他组织了一支业余性质的狩猎小队,让暴雪母子当上兼职猎犬。
据说,狩猎大战只要有暴雪参与,猎人底气会更足,别的狗也必定气焰高涨,以一当十。
暴雪因此获得“猎犬之魂”的美称。
二
我始终想象不出,念过高中的老曹究竟使用了怎样严酷的手段来“奴化”他的爱犬。但我亲眼看到,进入壮年(一般把2至7岁看作牧犬的青壮年时代)的大白狗,对曹胡子的命令仍不敢有丝毫违拗。那络腮胡大汉一声低吼、一声咳嗽,都能使暴雪的情绪产生微妙的变化,忽然进入激昂、亢奋状态。然后,它将按照自己对主人意图的理解,迅速行动。
老曹喜欢利用不寻常的条件来考验暴雪的忠诚和勇敢:顶着暴雨渡河,砸冰潜水捞物,以及雪夜奔袭追赶野兽等等。暴雪似乎很乐意向“恩主”显示它的忠心,也很在意围观者的赞赏,对每一次考验,它都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百分之百的认真,仿佛那便是它生存的终极目标。
为了让来年春草萌发得更茂盛,牧场要趁着残冬,向老化的草场发起“火耕”,烧尽残草,只保留草根。老曹看上了大火席卷之后滚烫的草木余烬。
“阿暴——”他站在老远处的山背上发令,那嗓门儿宏亮得如同军号,“过来——”
守候山脚观望的暴雪应声而出,一纵一跃地穿越大片腾烟冒火的焦黑色山坡,朝主人招手的方向奔去。刚跑出数十米,那北极熊般洁白的大狗就蹭上炭迹烟灰,变得黑一块,黄一块。
暴雪毫不在意。为走捷径,遇上残火它不屑绕道,就那么直闯过去。嗷,汪汪汪汪!它像是替自己鼓劲儿。狂风啸集阴云的天穹之下,大狗飞腾的四肢从黑灰中踢起串串复燃的火星,更显得神威凛凛。
风向陡然逆转。火场边沿六七米高的火舌朝中心反扑,呼呼有声。尚未冷却的草茎竹节又被引燃,发出噼里啪啦的炸响,那儿顿成一片火海。
暴雪仍不退缩。眨眼之间,它整个儿陷入烈焰浓烟。牧工们发出惊叫,唯有曹胡子不动声色。汪,哐哐!如雷的吼叫声中,暴雪突烟冒火而出。它浑身焦黑,背上还闪着火苗儿,依然跑得那么精神抖擞。
这惊险的一幕,使我对暴雪产生了敬意。一条如此忠诚勇敢的狗,老曹干吗非要用“奴性”二字去亵渎呢?
穿越最后一圈火焰,暴雪呼哧呼哧冲上了陡坡,奔向曹胡子,在他面前放下一只同样熏得焦黑的野兔,一件冒火突围时顺便抓来的战利品。
草场四周遏制火势的牧工发出欢呼。暴雪坐在老曹脚下,神色坦然地接受着远远近近的赞叹。看那模样,除了外形受损,它的皮肉并无烧伤。事后才听说,情况远比我猜想的糟得多——为治疗暴雪爪底和背上的多处烧伤,场部兽医用尽了库存的万花油,还给它注射了3天抗生素,才抑制住烧伤感染。
暴雪良好的体质战胜了伤痛,康复得特别快。新毛长齐后,它又恢复了一副英俊洁净的外貌,不凑近看,谁也不知道它的体毛下遗留了永难治愈的疤痕。
三
来牧场之前,在省城长大的我从未见识过这么雄壮的狗。它体重约40千克,胸宽腿长,爪子比我的拳头还大;双耳耷拉,眼睛老是阴沉着。最漂亮的是那身浴火重生的白毛。这个四季都下河泅水的家伙,浑身上下总保持干干净净,看不到一撮乱毛、一块污渍。
暴雪缎子般闪亮的洁白还是一种伪装。
一般来说,毛色越深的动物性子越暴烈,而浅色家畜多半温驯和善。纯白无瑕的暴雪却偏偏是个极不好惹的角色。
它轻易不吱声。一旦它发出带爆破音的咆哮,如同出膛炮弹般发动攻击时,我想,无论多么镇定的对手也得毛骨悚然;胆子稍小的,甚至会斗志顿失,精神彻底崩溃!
就算麻木到不懂害怕吧,又有谁能经受一枚40千克炮弹的冲击呢——何况这“炮弹”还武装着利爪,和比别的狗粗长得多的虎牙!
暴雪不是只仗着外形唬人。它拥有绝对的实力。
这不好惹的大狗跟它母亲一道,曾为保护牧群立下过汗马功劳。它们从饿狼口中夺回了良种羊羔,从老豹爪下抢救过奶牛犊子,听说还救过场长的命——两年前的某个雪夜,场长和牧工大保为寻找走失的荷斯坦牛犊,在山林遭遇到饿狼的包围。千钧一发之际,暴雪母子赶到,怒吼着冲进狼群……
一场场搏斗,在牧工口口相传中被渲染得惊悚惨烈,也给暴雪母子披上了炫目的光辉。老牧工说,暴雪平日太懒,不能算一条好牧犬,它对主人的忠诚却是无条件的,能经受任何考验。
暴雪认可的主人,除了老场长,第二个要数它的“教父”曹胡子。此外,大保等几位资格最老、又经常参加打猎的牧工,有时也能使唤它,不过,那只能是以朋友身份跟它打交道了。
后来老场长退休,暴雪跟曹胡子一道分到了奶牛分场。与他们“主仆”相伴的,还有暴雪的母亲,那条比它体形略小,披一身浅灰色短毛的垂耳朵老狗。
四
刚当上牛仔的我对这两位同样敬畏。
好长一段时间,我没弄明白它们到底属于哪个牧群。作为实习徒工,我协助师傅曹胡子管理着50多头高产奶牛。师傅兼职太多,大多数日子,伴我放牧的只有一条名叫毛头的小型牧犬。
每天,我和毛头驱赶奶牛群走向草场,总能看到暴雪母子蹲在场部大门外,像一对石狮子。打这儿经过的母牛都小心翼翼地绕开它们,仿佛那是两头野狼。
我曾试图用一块牛肉作贿赂,跟它们套近乎。两条大狗毫无反应。
我大着胆子走近,把手伸向暴雪白熊似的脑袋和粗脖子。起初它龇牙警告;见我赖着不走,这家伙汪一声跳了起来。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非逃跑不可了!
幸亏那一刻附近无人,要不,我以超常速度逃进牛群、爬上牛背的狼狈形象,准会在同伴中间落下笑柄。
碰了一鼻子灰,我对暴雪的好感荡然无存,从此再不敢招惹它们。
暗中留神,我发现暴雪母子基本不上牧场干活,它们的工作几乎全在夜间。当牛羊归栏,曹胡子和业余猎手们动手整理猎枪弹药时,这母子俩便活跃起来。它们兴奋不已地蹦着跳着,马似的打着响鼻,然后抢在猎人前面,跑向暮色沉凝的山道……
那还是20世纪60年代。当时打猎被称作“除山害”,是备受鼓励的行为。报上经常刊登打虎英雄、灭狼模范的光荣事迹,牧场更是希望猎人们将四周山林中的野兽收拾得一干二净,让牛羊安享永久太平。再说,皮毛能卖钱,兽肉还能给大伙改善伙食,由牧犬兼职猎犬、又晋升为专职猎犬的暴雪母子,当然受到大伙的特别宠爱。
打猎小队多半在深夜归来。有时,我刚挤完每天的最后一次牛奶,跟毛头一起走出牛栏,就能碰到猎归的热闹场面。
猎人们一个个须发上凝着白霜,脸膛兴奋得发红。他们将肩头的猎物重重地扔在伙房门外,大声豪气地嚷嚷着,吩咐炊事员起来剥皮割肉。
暴雪显得比他们更神气。它踩着猎物跑上跑下地嗅着,充满激情地撕扯凝血的伤口,像是泄恨,又像在检验野兽们死得是否彻底。
它的母亲,那灰色老狗则端坐一旁,摆出一副拒人千里的冷漠嘴脸。
五
冬尽春来,白昼一天天延长了。狩猎进入了淡季,猎犬和猎枪一起闲了下来。
闲得发闷,暴雪也会离开老母,到草场上逛荡。它在草木之间优哉游哉,时隐时现,潇洒得像《西游记》中不服天规管束的散仙。
那天,我们几个小牛群的牧犬联合行动,从山边荆棘丛中赶起一头黄麂。黄麂细瘦善跑,脚短体胖的土种牧犬想要逮着它十分困难。狗们不自量力穷追不舍,仅仅是出于对野兽的天然敌视。
起伏延绵的绿草坡上,飞旋着一个变幻的战阵,遍体油亮的黄麂从容优雅地跳跃前进,把杂牌犬队抛得老远。
忽然,一道白影掠过群狗,闪电般追了上去。是暴雪!它潇洒地一跃,从背后扑倒黄麂,咬住了脖子。
那不足10千克的小兽徒劳地蹬踢着,被暴雪叼上一块山石,踩在脚底。
牧犬们欢呼着拥向那边。暴雪却无心与它们共享战果,它威严地低吼一声,众狗就吓傻了似的,被钉在数米之外不敢近前了。大白狗慢条斯理地清除了身上沾的麂血,拖着胜利品扬长而去。
中午,这只麂就做了牧工们的下酒菜。
六
往后时常看到暴雪在牧场周边忙碌,寻觅猎踪。不屑于邀别的牧犬助阵,孤猎的大白狗命中率并不高。不过,一旦有了斩获,它立即精神百倍。它守在猎物边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仿佛一位准备参加隆重庆典的将军。休息够了,洁白的“礼服”也拾掇得满意了,暴雪才叼上猎物去向主人报功。
接受了狗儿上缴的战利品,曹胡子会拍拍它的脑袋,摸摸它的脊梁,以示嘉奖。这显然是暴雪深感幸福的时刻之一。它绕着主人嗬嗬叫着,又是亲吻又是打滚儿,平素那冷峻凶狠的神情从它身上一扫而光。
“够了,去吧——去玩儿!”没工夫跟它嗲,忙碌的老曹打发它走开,“去,快去!”
大狗跑开了,又兜回来,用脖子用额头使劲儿蹭着络腮胡大汉的靴筒,非得曹胡子再次下令,或者不耐烦地抬脚踢它,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暴雪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争取主人的爱抚和赞扬,获得那么一段短暂却激情奔放的幸福。
似乎,它只为“主人”而活着。
七
真正见识暴雪的骁勇善战,是被叫去参加围猎的那天。那是一场针对3头野狼的歼灭战。为提防被追剿的野狼铤而走险,窜入牧场伤害人畜,我们几个半大男孩都被分到了各自的岗哨上。
我们的任务,是守住与场部牛栏羊圈接壤的半面山坡。万一狼群朝这边逃窜,我们就得及时点燃倒悬在镔铁奶桶中的鞭炮,把野狼吓退,以确保全歼。
天还没黑。守在两只铁桶边,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山坡上的围猎场面。草木遮掩着,人与猎狗的包围线在时隐时现中收缩。砰——砰砰——枪响了,“中啦!中啦!”有人喊。
两头棕灰色的死狼被扔下山坡,滚落到山腰的小路边。牧工猎犬却没有收兵的征兆,人人狗狗围定了一片墨绿的杂树林。显然,最后一条狼就藏在那里。现场气氛更为紧张。
包围圈逼近了林子外围,几杆猎枪先后在岩石和大树后,找到了各自的伏击点。跑在最前面的大白狗闷不吭声地闯入那片绿荫。
深沉的墨绿涌动着,一头大狼从中蹿出,随之冲出的暴雪紧贴着狼的侧后。
汪汪!老灰狗奋不顾身迎头拦截。
野狼一闪,避开暴雪母子的前后夹击,撞向端枪瞄准的曹胡子。
猎枪失手,曹胡子拔出腰间鞘中的砍刀奋力抵抗。人狼缠结之际,别人不敢开火,只有两个擎虎叉的汉子从左右攀援过去。
眼看着虎叉将解决战斗,人狼纠缠的一团却滚下了陡坡。
老曹失声惊叫,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可隔着那么深的山坑,我们只能干着急。
暴雪骤发的怒吼随着它灿白的身影从绿荫中飞出,野狼就在下一瞬间被拽离了曹胡子,跟大白狗厮咬着翻滚而下,直达暮色沉淀的坑底。
接下来的战斗在昏暗中进行。我们弄不清谁胜谁负,只听到暴雪低沉的咆哮与野狼的嘶嗥绞成一团……
等我们几个跑到那边,3条狼分别扛上了猎手的肩头。其中最大的一头(也就是跟暴雪肉搏的那家伙)个头与暴雪不相上下。在当时,如此大块头的野狼已属罕见。它身上没有枪伤,几道刀痕也不很深,咽喉部那致命的大豁口,完全是暴雪的杰作!
凯旋的暴雪受到了牧犬热情的欢迎。它的伤口也在滴血,但威风丝毫不减,仍然在每一条狗面前保持着它的尊严。兽医给它处理过伤口又注射了狂犬疫苗后,暴雪就跑到母亲身边,殷勤地替老母理毛,舔伤。
做母亲的便报以同样的关爱。母子俩像是忘却了刚才的激战,彻底沉浸在温情脉脉的天伦之乐中……
八
老牧工说,一对一与野兽干仗,暴雪不知干过多少次,它始终保持全胜。
我知道这些格斗有猎人猎枪作后盾,算不上真正的“一对一”。比方说那头被它“身先士卒”赶跑的金钱豹——老豹害怕的其实不是狗,而是追在牧犬身后的人和枪。
但暴雪终于找到机会向人们证明它的实力。它独个儿走出猎人猎枪的控制范围,在远离牧场的深山老林,与一头云豹进行了一场完全公平的生死较量。
云豹个头小,一般不超过20千克,但凶悍狡捷,号称“飞虎”——这种树栖小豹善于趁着从空坠落的刹那击杀对手。曾有两条牧犬在那小霸王迅疾有力的虎牙和巨掌下丧命。
决意为狗复仇的曹胡子也屡屡扑空。云豹特别谨慎,见到猎人猎枪,一定深匿不出,它只打有绝胜把握之仗。
暴雪却通过跟随主人的侦察掌握了更为精确的情报,它背着主人开始了单独行动。
没人跟着,那头树栖大猫也许有胆量向它发起攻击吧。可是,暴雪硕大的身躯同样引起了云豹的警惕,“以身作饵”之计根本行不通。
暴雪在那儿埋伏下来。老曹安置的捕兽套奈何不了云豹,却套住了两只肥兔。野兔不停地挣扎,暴雪选择的伏击点就在两只野兔之间。
一天过去了,半夜过去了……饥饿的云豹再也忍受不住,它飞身扑向不再挣扎的野兔。以它惯常的敏捷,数秒之内即可取下猎物退回树上。它不会想到,一个更有耐性的杀手在下面等待——云豹扑下的同时,暴雪出击了。为得到这个近身搏杀的机会,它在秋蚊成群的草丛中一动不动坚守了一天半夜。
对阵的刹那,林中如同爆响了炸雷。两个猛兽绞作一团。口裂极深的猎犬在颚部咬力上占了上风,云豹却拥有更为柔韧、伸缩自如的四肢和利爪。暴雪拼命扑咬,云豹三番五次想要逃回树上、重获空中优势的企图,都遭到了阻挠。
那从未遇见过强敌的飞虎将军怒不可遏,它吼声连连,对大狗展开了雄狮猛虎般的组合攻势……
这场秘密决斗瞒过了人眼,还可能因其凶狠浩大的声势,吓跑了林间所有旁观的小动物。我们只能在事后,从战斗现场、从大白狗身上撕裂的二十道大小伤口,来猜测犬豹恶战的经过和激烈程度。
最终,暴雪仗着体力上的绝对优势,将急欲逃回大树的云豹死死摁住,咬住了那头野兽又粗又硬的脖子。
此后必定是长时间的僵持。云豹挣扎,抓挠;暴雪忍受着利爪切割皮肉的痛苦,越咬越紧。最终,那凶悍的小霸王一命呜呼,大狗也精疲力竭,瘫软在地……
暴雪在黎明前挤奶时分挠响了曹胡子的房门,向主人献上一条肥壮的豹尾,就趴在门槛上一动也不动了。
它身后,断断续续的血痕指向大山。正是凭着这血迹,牧人牧犬顺利地找到了死去的云豹。
九
暴雪蔫了好些日子,才终于恢复了惯常的矫健。它康复得正是时候,因为下一个猎季又来临了。
这个猎季旗开得胜,第一仗,便扛回了大大小小七头野猪。不幸的是,暴雪的母亲也是扛回来的,它被一头大野猪的长嘴獠牙挑破了肚子。
老灰狗伤势严重,到家时周身发烫,已处于半昏迷状态。急于为它处理伤口的兽医却遭到出乎意料的反抗,老狗不让人手碰它的伤口。
“别乱咬,是我!”曹胡子从后面向它接近。
老狗还是哦儿嗬儿低声威胁,剧痛和高烧令它神智迷乱,它谁也不认识,对谁也不信任了。
老曹抓住了老狗的帆布项圈,老狗反应奇快,两排利齿喀嗒一下咬过来。早有准备的曹胡子趁势将一块劈柴横搁在狗嘴里。
犬牙无法咬合,其他便不足虑了。
可是兽医仍不敢近前——暴雪端坐在一旁,也在喉咙深处发出威胁的低吼。看那阵势,如果谁胆敢冒犯它的母亲,它随时可能出击。
“没你的事儿,阿暴!”老曹喝令,“走开些!”
暴雪寸步不让,那双冒火的眼睛似在宣告:为了母亲,它不惜反叛主人!
老兽医把消毒药水递给曹胡子,慌忙退开了。曹胡子就将药水小心地淋在老狗血污的伤口上。
药水的刺激,又使老狗从昏迷中痛醒。它一摆脑袋,磕掉了横搁在口腔的劈柴,随即一挺腰身,将猝不及防的曹胡子撞倒,张口就咬。
老曹抬手抵挡。狗牙划破他的肘部,半条胳膊顿时被鲜血染红。老狗又咬向他的咽喉……
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暴雪一跃而起,张嘴咬住母亲的脖子,硬生生将老狗从主人身上拖开。原来它并非护母,而是唯恐老母伤害主人。
“阿暴,别乱来!”曹胡子爬起来去揪它的项圈,大保也跑上前,想要制止暴雪的过激行动。
暴雪哪里肯听!此时此刻,它完全被老母亲对主人的叛逆激怒得发疯了。它呜嗷呜嗷地嘶吼着,紧紧咬住母狗的颈皮使劲儿摇晃,任老曹大保手扯脚踢,都不肯松口。
这才叫奴性大发呢,为了讨好主人,它竟向生母痛下杀手!愤怒令我勇气大增,我跑过去,拾起地上的劈柴,拼尽全力砸向暴雪。
暴雪透着牙缝痛叫一声,咬得更紧。
“打!”几个人围了上来。暴雪的行为已经激起了公愤,“杀掉这没良心的!”
“砍,砍死它!”更多人响应着。木棒、枪托疾雨般击打在那个逆子身上。还有人拖来了铡草的大刀。暴雪显出了十足的犟劲儿,它继续拖拽着母亲,逃避打击。
痛苦不堪的老狗哼了哼,忽然中止挣扎,蹬直了四肢。
此刻,暴雪已被怒火中烧的牧工们揍得血肉模糊,曹胡子和大保还端起了猎枪。
弑母的凶手这才扔下咽气的老狗,撒腿逃向场部后侧的山林。砰!砰砰!枪声在后头追赶。我看到暴雪歪了一下,随即被浓密的草木遮掩。
十
暴雪逃跑后好久没露面。
猎人和牧工们赌咒发誓要干掉它。老曹宣布:等逮着那个逆贼,他非亲手活剐了它不可!
说这话时,曹胡子被老狗咬破的手肘上缠着绷带。暴雪的确是为了维护他,才与生母反目成仇的。可是,谁又能因为那条狗对主人的忠诚,就饶恕它残杀亲娘的罪过呢?
急于严惩凶手,业余猎人们兵分两路,对牧场东南两侧的山林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按说,有嗅觉出色的牧犬引路,要找到暴雪不是难事。可是几天过去,打猎小队的人没得到一次向暴雪开火的机会,暴雪像是钻进了地缝。
我想,那些狗不会出卖暴雪的。在它们眼里,不管暴雪干了什么,都是它们的“英雄”,它们的“王”。
依靠它们,只会把对暴雪的搜捕引入歧途。
日子在牛哞犬吠,在牧人的响鞭和吆喝声中缓缓流逝,大伙差不多把干掉暴雪的誓言忘了。
转眼又是春天。我接替一位老牧工,独个儿来到远离场部的第5放牧组,承担了管理20多头奶牛的任务。场部的三轮车一天三趟到我这儿拉鲜奶,顺便给我捎来一日三餐。别的时候,与我相伴的就只有牛和牧犬了。
一天,我赶着牛群“远征”,去寻找雨后猛长的野苜蓿和禾芒。登上一道山脊,我无意中看到了那条失踪了好久的大狗。
它显得又老又瘦,原本雪白的皮毛,经血污泥裹,脏成了灰黑,还缠结着大大小小的“棉絮”疙瘩。倘不是那酷似冰熊的硕大头颅,我简直不敢相信,望远镜锁定的“癞皮狗”竟是暴雪。
变化最大的是它的神情。从它的眼睛里,已看不到往日那目空一切的傲气,倒像充满迷茫,似乎它始终不明白主人何以要驱逐它、厌弃它——无条件地忠于主人、为救主而大义灭亲,难道它做得还不够吗?
否则,就是那违悖本能灵性的弑母之举,此时还令它懊悔不已、肝肠寸断?
不管从哪一方面分析,我都敢断定,眼前这头大狗,正经历着一场心灵的酷刑,经受着极度的痛苦折磨!
我慢慢儿向它挪近。
一向机敏的暴雪居然没有发觉。它仍然朝着场部的方向,痴痴地遥望山野间远远近近的牧群、牧犬和牧人,遥望起伏的草浪,以及天际翻滚的浓云。
吁——咿!我冲它打了个唿哨。
暴雪霍地转过头,疑惑地看了看我——啊,这是它第一次正眼瞅我!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了。它背脊上的长毛所剩不多,干瘦的臀部凹陷下一大块。我猜想那是猎枪子弹留下的纪念。
总算有一枪击中了它——这也许能令曹胡子感到欣慰。可冷静地想想,暴雪的凶残和奴性,不都是老曹赐予的么!当那位牛仔英雄用吼斥、用饥饿和棍棒塑造所谓“猎犬之魂”时,这条狗的天性已开始扭曲,残暴和奴性的恶魔悄悄在它的脑瓜里盘踞下来,并最终酿造了后面的悲剧……
我心头发紧,没有向业余猎手们告发暴雪的去向。
第二天,我带去了一大块酥焙羊排,放在暴雪待过的山脊上。
它会来的。它不能决然舍弃这儿的一切,否则,它早该走了。它对主人还心存幻想,随时准备听从呼唤回到狩猎小队……而且,眼下它是那么虚弱,那么饥饿,一定亟需得到营养补充……我应当帮助它度过难关。
可是,暴雪竟一去不返。
遭主人遗弃的大狗可能选择返祖道路,回归荒野,去投靠红豺或者野狼的部落。但那些野兽肯收留它吗?为了向主人邀功请赏,它曾经那样卖力地协同猎枪驱逐和残杀过它们。
那条路走不通。过去的猎犬只能做一条孤独的野狗,在野兽们仇恨的注视下,在危机四伏中苦苦熬过它的后半生……
三天过去,暴雪不曾来领取这份美食。
第四天,晒得发白的酥羊排上爬满了蚂蚁,一只土黄色的狐狸偷偷溜近,叼着羊排跑了。
暴雪就那么失踪了。在我当牛仔的三个年头里,它再也没有出现过。
十一
事情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
我还时常记起暴雪,那条对主人无比忠诚、按人类的道德标准又确实犯下了不赦之罪的恶狗。随着时光推移,暴雪的高傲和“罪过”在我印象中早已淡化,唯有那一瘸一拐离去的干瘦背影,至今清晰如初——山雨欲来的晦暗天穹下,狂风掀簸着草波,吹拂着它身上所剩无几的乱毛。脏污成灰黑的大狗朝着与牧场相反的方向,渐去渐远。
哦,我还记得,就在那个夜晚,下了一场罕见的大暴雨。暴雪能找到地方躲避雷电和骤发的山洪吗?被炸雷从睡梦中惊醒,15岁的我老在担心。贴着窗玻璃往外看,只见电光闪烁,浊水横流,狂风扫荡的树木野草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啸……
发稿/田俊
作者简介
牧铃(1951—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岳阳市作协副主席。近期代表作有长篇系列《一个人的牧场》《艰难的归程》等。20世纪90年代起在《少年文艺》发表过大量中短篇小说,并因此由成人文学转入少儿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