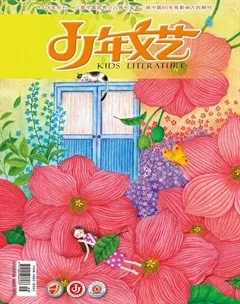离歌
2013-12-29林佳嘉
我刚回到家,爸爸把我拉进房间,很严肃地对我说,声音平静得发冷,“你姑姑她……今天早上七点多的时候过世了,是心肌梗塞。”我下意识地“哦”了一声,脑袋与心脏却陷入无垠的震惊与迷茫之中,心绪骤乱,挣扎着试图拨开死亡的混沌。
我没有见她最后一面。她的死,是从爸爸嘴里说出来的一句话,一句轻飘飘的话,但是事实却如同一具黑色的幕布,沉重压抑。
我总觉得,无论再怎么亲与爱的人,在死亡的一刹那都与我们是陌生人。姑姑死亡的那一刻,是黑暗而不为人知的洞,但是,关于她的回忆,永远都恬静,其间还夹杂着遗憾与愧疚。
姑姑生前曾经住在一处叫“一村”的老旧的居民区。六十多岁的姑姑有一个近四十岁的脑瘫女儿,她坐在轮椅上,我叫她“大姐姐”。大姐姐的手和脚都软塌塌地搭在轮椅的扶手上,当她要上洗手间的时候,瘦瘦的姑姑一手揽起她的腰,踉跄着缓慢地移向洗手间,一天好几次,每天如此。
那时候的我对此见惯不怪。
小时候爸爸妈妈总是不在家,我便总是被送到姑姑家,姑姑很疼我,我经常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天。
我不记得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姑姑,我只从爸爸的口中与旧相片中得知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姑姑就开始照顾我。相片中小小的还是婴儿的我,稀疏的头发带点金黄色,坐在石质的滑梯上,姑姑在一旁扶着我,面孔映着金色的阳光,表情恬静。那是姑姑为数不多的相片之一。之前姑姑还带我去相片中的石质滑梯所在的现在已经很旧了的小花园里,我已不记得我曾在婴儿时期去过那里,但是心中似乎对那里总有隐隐约约的模糊印象。每次想到相片中那个普通的、恬静的画面,我就感到无比幸福。
姑姑的家很窄小,客厅里只有一扇不大的玻璃窗,但是小小的客厅只要有一点光从窗外射入就会变得很亮堂。而从两个小房间窗户进入的光与客厅的光汇合在一起时,整间屋子就像是个亮堂的盒子。
我喜欢姑姑的家,那儿很随意很自由,我喜欢那里几乎胜过喜欢自己的家。
姑姑的手很灵巧。家里窄窄的房间中有一台老旧的缝纫机,缝纫机的构造在那时的我看来是复杂、神秘而有趣的,但是姑姑从不让我动她的缝纫机,她总是戴着她的粗框老花镜在机前埋头苦干。我在客厅摆自己的积木时,总能听到房间里传来缝纫机发出的“咕噜咕噜”的声音,还有剪子的响声,那些细碎的声音简直成了姑姑家的背景音乐了。我有事没事就喜欢走进房间看姑姑做缝纫,看机子上那根固定的针一上一下在布料上留下整齐的车线。
姑姑常常将一块块的布料铺在床上,这里折一折,那里裁一裁,然后摊在缝纫机上,不一会儿又拿下来。那些布块的形状总是很不规则,但是一两个星期后,一件干净、完整的衣服就做出来了。
有一件灰紫色的大衣是姑姑的得意之作,它刚刚制作完成的时候,姑姑很开心地将衣服举在我面前,我却说不好看,很老土。现在想想才觉得,那大概是姑姑弄到的最好的一块布料吧。
姑姑还和我说,家里那两顶小蚊帐是她用一顶大蚊帐裁成的。我为此仔细地观察了那两顶蚊帐,发现它们无论是剪裁还是车线看起来都很繁琐。
姑姑的家有两个小房间,却有五张床,全都是手工制作成的,阳台放的那一张最好玩,平时当椅子,睡觉的时候可以变成床。我平时在姑姑家睡的就是那一张。
每天晚上我都在汽车驶过的呼啸声中睡去,那呼啸声,像是起伏的鼾声。我听爸爸说姑姑家因为靠路边所以噪音太多,但在我听来那不是噪音,而是睡前美好的陪伴。偶尔,我也会在深夜莫名醒来,听着那“鼾声”,只觉满心静谧。
记得一个炎热的夜晚,我在冒着热气的浑浊空气中迷迷糊糊地醒来,依稀看见身旁亮着昏暗的灯光,姑姑伏在我的身旁。我一开始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只觉得她的手一直在慢慢摇动,微弱但清凉的风一点一点地钻入我的皮肤。她原来是在给我扇扇子。我记不清当时她的表情,只是意识模糊地感到世界上似乎只剩下黑夜、姑姑,还有那丝丝凉风。
姑姑家的清晨有着一种舒适感,一种不急不躁的淡然。刚从睡梦中脱身而出,睁开眼,一切由混沌转为清晰。我看见姑丈坐在我身旁抽烟,神情淡漠,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我听见姑姑家的画眉鸟不断重复唱着那熟悉的、从不改变的调子;或许是厨房里,或许是客厅里传出姑姑细碎的脚步声,水龙头开闭时的响声;房间里还有大姐姐初醒时浑浊不清的叫喊。
一切都平常而不足为奇,却温暖了我的心。
清晨,阳台光亮得如同梦境,我醒来后总爱在阳光里醉一会儿,才在姑姑的催促声中钻回屋里刷牙洗脸。
温热的午后,我意识迷乱地躺在木床上休息,听姑姑与大姐姐之间的对话,那都是些类似于晚餐吃什么、棉被要不要晒、下午要煮橘子汁之类的话语,琐碎而恬淡,似乎与空气融为一体,没有突兀感。
我待在姑姑家的时候,并不喜好出门的姑姑见我闷得慌,偶尔也会带我出去逛逛。有一次姑姑带我从一座小花园里走出来,我听见她突然间喃喃地说:“要是你大姐姐也可以这样摇摇晃晃地在街上一边吃甘蔗一边走就好了。”我看见我们前面走着一个胖胖的吃着甘蔗的女人。我很奇怪地问:“为什么你希望大姐姐在街上买甘蔗吃呢?”姑姑没有回答我,她显然知道我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但是那时我却纳闷了很久,为什么姑姑那么希望大姐姐出来买甘蔗吃。
小时候,我只觉得姑姑的生活很明朗。
但是,这种明朗或许仅仅缘于我的年幼。年幼孩子的内心就像一把筛子,总能够把所有的不好过滤掉,而在长大的同时,我们看世界的眼光越来越清晰,所有的不好与苦痛也跟着突兀起来。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一半懂事,一半不懂事。有一次我看着姑姑把沉重的大姐姐从轮椅上拉起,费劲地把她安置到床铺上。我第一次对这种见惯不怪的情景发出评论:“姑姑,你好大力啊。”姑姑发出一种奇怪的笑声,那似乎是从牙缝中挤出的,“没有力气也要有力气呀……”她心不在焉地回答。接着我又问大姐姐:“如果以后姑姑不在了谁抱你去洗手间呢?你要怎样洗澡呢?”没有人回答我。我不知道坐在客厅的姑丈有没有听到我的问题。
我后来才发现,我的这个问题是如此的不留余地,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有些事情足以让人想都不敢想。
似乎是从那时候起,我渐渐体味出姑姑的生活中那隐匿于幕后的一点点绝望。它看不见,闻不到,没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却一点一点从空气的裂缝中渗出。
渐渐地,姑姑就不再做缝纫工作了,那台老旧的缝纫机被弃置在一旁,堆满杂物。我对此感到遗憾,央求姑姑继续缝衣服,但是姑姑只是坐在椅子上疲惫地半睁着眼睛对我说:“姑姑眼睛不行了呀……而且我都老了,要那么多新衣服做什么呢。”于是,缝纫机发出的熟悉的“咕噜咕噜”声便只能在记忆中落寞地回荡。
我越来越发现姑姑的疲惫与郁郁寡欢,平时我去她家,与她谈话,她也会笑,但笑起来总让人感觉她心不在焉。我想起小时候在姑姑家体会到的那种纯粹的舒适恬淡的感觉,如同渺远的回音。我开始相信那“舒适恬淡”是我的幻觉,是我用美好单纯的童心所看到的,姑姑的痛苦我无法理解,或许这种痛苦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明白。
后来,姑姑所在的居民区有传闻,说小区内最靠马路的那一排居民楼要拆迁。姑姑的家在拆迁范围内。
我也听闻了消息,却以旁观者的身份乐观地觉得这不会是真的。而平时我也甚少听姑姑和姑丈谈这件事情。不过,我不会知道他们是否彻夜谈过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非常严峻的问题。
传言后来变成了一张张拆迁合同。我这才开始感到不安与心痛,姑姑姑丈都那么老了,还带着脑瘫的大姐姐,他们可以去哪里?但是拆迁公司没有留太多时间给我们去想这些问题,几个月后,姑姑的家成了一片废墟。政府说他们会在另一处新建居民楼安置拆迁户,但是建新楼的日子,姑姑他们只能在外面租房子。
姑姑搬家的那一天,我没有去帮忙,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在那一天搬家了,只是在某个下午接到姑姑的电话,她说他们在另一处旧居民区租了一间房子住。我不知道姑姑和姑丈是怎样把大姐姐抬下楼的,也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少钱请搬家公司。我异常懊恼当天我没有在他们身旁。
那时候我已经不经常去姑姑家了,也再没在那儿住过。第一次去那间他们租的房子时,我惊讶于房子的昏暗。我安静地坐着,在昏暗的房子中看不清姑姑脸上的表情,我有点勉强地说:“姑姑,这间房子好像比你们之前的那一间要大一点哦。”“大?呵呵,哪里大呀,况且大也没有用,这又不是我的家。”姑姑用心不在焉的语气回答我。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于是一言不发地看着姑姑做一切琐琐碎碎的事。有时候我会想,她有没有留意过自己手头在做着什么呢?
临走的时候,姑姑拼命地塞水果给我带回家去。她还记得,以前我待在她家的时候有事没事总喜欢打开冰箱看有没有水果吃。
一段日子过去了,我问爸爸,姑姑他们的新房子建好了没有?爸爸说连房子的影子都没有,然后他又说,姑姑一辈子都没住过新房子,等到差不多七十岁了才有这么个机会。
其实,姑姑哪里想要什么新房子,她只需要一个安稳的、不用拆迁的家。那次拆迁,对姑姑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或许她早已经开始等待着自己的最后一天了。
冬天的一个星期六,我跑去看望姑姑。我看见她裹着灰绿色的旧大衣从房间里走出来,样子异常疲惫与憔悴,而且眼睛周围油腻腻的,她见到我后眯着眼睛看着我,似乎是想看清我是谁。我忽然间鼻头一酸,问她是不是病了。她才突然眉开眼笑,“是佳嘉呀,哎哟你离我那么近我都看不清是谁,最近眼睛出问题了,看什么都朦朦胧胧的,天天涂眼药膏都不管用。”说着还用手挠了挠眼角。天哪,这还是那个以前几乎天天踏着缝纫机车布的姑姑吗?“姑姑,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呀?”“看什么呀,可以去药店买点眼药膏的嘛。”姑姑摆摆手说。“可是你怎么可以不去医院看病就自己买药来用呢,你又不清楚你的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试图向姑姑说明这个问题,可是姑姑却说:“我去医院,你大姐姐谁来照顾?你姑丈是男人,怎么方便照顾她呢。”我顿时无语。
傍晚,我依旧没有回家,待在姑姑家看电视。我看着姑姑眯着眼睛费劲地拖着大姐姐去洗手间洗澡,姑姑看起来是那样羸弱,可是我除了帮她们固定住轮椅,再也帮不上什么忙。
过年之前,我和爸爸去过姑姑家,那时候的姑姑简直就像一片干枯的叶子,眼睛浮肿,周围油腻腻的,脸色蜡黄,双手抓在一起搭在腹前。她看起来比之前更加憔悴。姑姑说她这段日子腹部经常疼痛,有时候甚至疼得晕了过去。但是她依然只是去药店买药回家吃。我总感觉她对自己身上的病痛抱着自暴自弃的态度。
那一天,我听见姑姑低声地自言自语:“没事,再过个三两年就解脱了……”那时候我的心都寒了。
但是死神并没有等满三两年就来了。
过完年,我在家中听见爸爸和妈妈在谈话:“佳嘉她姑姑今天被送进医院做肿瘤切除手术了。”“过年前去她家坐过,那时候就觉得她病怏怏的了……手术费要多少啊?”“不知道啊,他们也不让帮忙。唉,真是病不起呀。”我惊呆了,虽然肿瘤切除手术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大手术,但是我的内心依然七上八下,姑姑年老体弱能熬得过去吗?
还好第二天我听爸爸说姑姑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很好。我很欣慰地想:不知道姑姑脸上是否有了些许红润呢?傍晚爸爸去医院看姑姑,我因为学校有事便没有去,心想着过几天等姑姑恢复得好一些了再去看也不迟。
可是没有想到,正常人都不会预料到的结局却在姑姑入院第三天发生了。那天傍晚,爸爸把我叫到他房里……
没有任何征兆,没有给人任何心理准备。
“唉……我昨天还跟她聊过天呢,今天怎么就……”爸爸满脸遗憾地喃喃说。可是,可是,我都没有去见姑姑最后一面。我肠子都快悔断了。我甚至不记得我最后一次从姑姑家离开与她告别是什么时候,也不记得当时她是什么样的表情,对我说了些什么,或许她递给了我一个苹果叫我带回家去,或许她拍着我的肩对我说好好学习,或许她还默默地在后面目送着我离开。她悄无声息地走进我的生命,又悄无声息地离去。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卧在床上想了很久,想象着姑姑生命最后一刻那如同猛烈的潮水般的呼吸,那时候她的脑海里想的会是什么?是在家中等她回去的大姐姐,年迈冷漠的姑丈,还是只有无尽的绝望?
我不忍心再想下去,我就连想象一下姑姑死前那痛苦的样子都感到战栗。
爸爸对我说,姑姑年轻的时候生下了大姐姐,可是一年后就发现大姐姐的身体很不正常,她总是像痉挛那样扭动着身子,无法坐起来,也无法用双腿爬行,如同蛇一样。所有的人都议论纷纷,说大姐姐是蛇胎,劝姑姑扔掉她,但是姑姑和姑丈舍不得。于是姑姑便一辈子将大姐姐带在身边照顾,上洗手间,洗澡,吃饭,睡觉,换衣服……姑姑的生命就一直拴了一颗大石头。
爸爸说是大姐姐拖累了姑姑的一辈子,但是我不想这么说,大姐姐没有错,姑姑更没有错,没有人有错。
一辈子,有谁对自己的时光概念能够超越一辈子?我们就只有一辈子而已,姑姑被痛苦纠缠了整整一辈子,绝望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这不是我能懂的。
姑姑已经去世好几个月了,我总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她,想起她所有的好,想起她的苦闷,想起她的一切。
每次想起她,我就会在黑暗中哽咽得难以呼吸。
发稿/田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