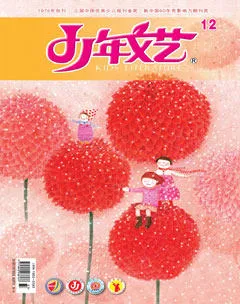我在城市寄居的那一年
2013-12-29张晓玲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妈妈忽然决定带我去县城读书。
妈妈是很能干的女人,虽然身在农村,但她的眼神时刻望着远方,仿佛要看到天际线的另一端。她的人生犹如一场梦魇,梦魇和噩梦是不同的,梦魇的意思是头脑醒了而身体不能动,你能听见,能看见,可是不能动弹。她被环境以及她的见识所拘束着,模模糊糊看到天边的一线曙光,但不清楚那是什么。只有一点她心里明白:要和别人活得不一样。要打败这周遭聒噪的、贫穷的、捉襟见肘的一切,寻找更为体面的生活。
她决定要把我送出这一场梦魇去,所以,不知道她七拐八扭找到了哪些关系,运用了哪些超乎农村妇女想象力的手段,总之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正站在县城城东的桥上往下望,河岸上鲜明的白墙黑瓦,是师专第一附属小学。
我走的时候,原先小学校里的老师都极其惋惜,因为他们无比爱我。我的班主任送我很多东西,同学们为我写惜别的肉麻话,写满了一个破本子。
我没有流眼泪,带着这个破本子没心没肺地走了。
县城在三十里外,小学生不能寄宿,城里又没有房子,而乡下的家里,有太多事情需要忙碌,所以一开始,妈妈只能把我放在别人家寄居。
最开始的时候,我寄居在城东的二爷爷家。二爷爷家是个大家族,每天来来去去都是人,女人居多。一开始我也跟他们一起在大桌子上吃饭,他们形容我搛菜的时候如同“扛芦柴”,然后就轰然地笑。
后来他们不让我一桌吃饭,特地为我准备了一张小桌。我很高兴,因为可以不必叫人,不必等别人开动了再吃,不必在吃完饭之后一个个地让人“慢点吃”。我总叫错人,把姑妈叫成姐姐,把姨妈叫成奶奶,人太多,记不住。吃完饭,把小桌上的米粒汤汁抹净,便就着小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睡觉。
星期天妈妈接我回家,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她小桌的事。很快,下个星期,自尊心很强的她就虎着脸与城东二爷爷家短暂地断绝了关系,把我送到了另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的户主姓陈。因为我妈妈也姓陈,她让我喊户主舅舅,喊户主的妻子舅妈,户主的两个女儿,就是表姐。
至今不知道我妈妈怎么会跟他们相熟。想来他们应该欠我妈妈一份人情才是,所以,我才能到这户真正的城里人家,受到非常好的款待。
小表姐叫娟娟,大我一岁。和我上一个学校,比我高一年级。
到她家的第二天,她帮我洗头,洗出半盆泥来。
她说:“我看你有一个星期没洗头了。”
我嗯了一声。
她看看那盆水,又说:“不,我看你有两个星期没洗头了。”
我又嗯了一声。
她再看看那盆水,又说:“你不会有一个月没洗头了吧?”
我不得不申辩:“不是,我上个月洗过的。没满一个月。”
两位表姐每天要喝一勺B族维生素液,以促进发育。维生素液装在一个大大的棕色瓶子里。我也跟着她们每天喝一勺。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喝,每天一勺哪里够。于是在一个玩耍的下午,我偷偷地拿起那个瓶子,像大人喝酒一样,喝了一大口。然后盖好瓶子,把瓶子放回原处。
我以为没有人会发现,若无其事地到卧室和娟娟玩。娟娟都没抬头看我,摆弄她的洋娃娃。忽然她说:“你喝维B了?”
我微微吃了一惊,但我无可抵赖,只好说:“嗯。”
她得意地说:“我闻出来的。”
我又“嗯”,尽量把嘴巴闭紧。
她问:“好喝吗?”
“嗯。”
她下床去,“我也去喝。”
我站在卧室门口看她拧开维B的盖子,咕嘟嘟喝了一大口。然后,她呵了好大的一口气给我闻。维B气。
我也哈了好大的一口维B气还给她。
那一刻,我真喜欢她。
他们家经常请客吃饭。娟娟动不动就跟我说:“今天我爸爸请客。”于是,在狭窄的餐厅里摆上一桌。他们家住筒子楼,房门朝北开,厨房在阳台上,餐厅就是客厅,沙发摆在卧室里。
她爸爸厨艺真好,所以经常请客人回来吃饭。她爸爸是某个企业的小头目,经常请的人是大头目。大头目一来,我们就回避,去卧室吃饭。
没有客人的时候,他爸爸也会给家人施展厨艺。有一回做面拖蟹。螃蟹切成两半,蘸上面糊,放到锅里烩,加各种佐料,没出锅就香味四溢。我吃得很多,后来,娟娟跟我说:“我姐姐说你吃相不好。”
娟娟的姐姐叫燕燕,已经十几岁了,她大概不喜欢我。她经常一个人坐在沙发里看言情小说。我坐在另一个沙发里,把她刚看完的书都看了,因为看得比她快,很多时候就眼睁睁地等着她。她妈妈就骂:“高中生呢,看小学生看的书!给妹妹看!”
燕燕大概因此更加不喜欢我。
但这种喜欢和不喜欢都没有任何的结局,很快,我又转移阵地到了一个服装厂的宿舍里,照顾我的人是在服装厂做工的大姨姐姐。
大姨姐姐那时刚离婚,带着个两三岁的女儿生活。我跟她们昏天黑地挤在一起,放学了就自己拿碎布料为我的洋娃娃做衣服。我给洋娃娃做了两件连衣裙,可以供它一洗一换。领口太小,洋娃娃头大,套不进去,我就先把洋娃娃的头拧下来,等衣服穿好,再给它把头装上。
有次学校手工比赛,我拿了两条小连衣裙去参加,惨败而归。有一个女孩的女红比我好太多,因为她用的是缝纫机,线裰得很齐整。
我也想学踩缝纫机,大姨姐姐劈头骂我:“你妈费这么大心思,让你过来学踩缝纫机的?就算踩成我这样,又有什么出息?”
害得我到现在都不会踩缝纫机。
妈妈终于成功地跑到城东的一家工厂做工,晚上可以和我住在一起。一个月租十元的房子,就在大姐姐的宿舍隔壁。
我觉得自己像个接力棒,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传了一圈,终于被传回来了。
妈妈那时三十三岁。虽然她没做成功过什么事情,可是她对生活充满热情,充满奇思妙想,让我很崇拜。
妈妈当时的工作是在台灯厂烧灯泡。带我去过一回,年月久远,很多细节不记得了。只记得车间很大,很亮,非常热,几十个人排成几排,低头工作。我看着一滴液态的玻璃水慢慢凝固成一个细如小指的小灯泡,忍不住就去摸了一下。只一下,那尚未冷却的玻璃灯泡就粘在了我手上,烫得我直叫。我把它拿下来的时候,粘掉了食指的一层皮,痛了好几天。
妈妈的奇思妙想也许跟她的工作有关,估计是整天看着玻璃水凝固的场面产生了灵感,她有一次把家里所有的照片都糊上一层黄色的胶水,说这样可以保存得长久。我觉得那大概是相纸覆膜的前身。糊上胶水的照片固然都不会掉色,也不怕沾水,可是她不曾料到的是,到了冬天,固化的胶水开裂,让照片碎成了片片。
她还用一块花布覆在桌面上,再糊上那种黄色的胶水。糊好了胶水的桌面像起伏的黄色波浪。我着迷地看着这块有了岁月色调的花布桌面,觉得它非常美丽。直到冬天来临,起伏的波浪裂成消融的冰面。
每次看到麦兜的妈妈麦太,总让我想起我的妈妈。
留在我印象里的还有一盏台灯。非常漂亮优雅的台灯,陶瓷的印花灯柱,米黄色棉布灯罩,是妈妈从工厂里带回来的。有两个灯泡,一大一小,拉一下,大灯亮,再拉一下,小灯亮,再拉一下,都不亮。真的很奇妙。我能一下一下拉上半个小时,且一有客人来就展示给他们看。
后来小灯泡先爆掉,小灯泡不实用,妈妈一直都没有再配。
有一回我把手指头伸进螺口里,触电了。
触电的感觉也很奇妙,像被人当胸重重打了一拳。我被打倒在地上。地面是木头的,台灯很快从我的手指头上掉下去,我一骨碌就爬了起来。
这件事情我没跟妈妈说起。是我自己做错事,她不知道,是万幸。
在那个极小极小的寄居地,一个铺着美丽桌布的桌子,和一盏陶瓷的、带着米黄灯罩的台灯,当然,还有坐在柔和的台灯光下写作业的我,都肩负着年轻的妈妈对于未来的渴望。
那一年没有跟妈妈说起的事,还有几件。其中一个是有关米卷的。
小学校里经常有人来卖米卷,五分钱一根。我那天有了两毛钱。两毛钱呐,买一根米卷,还有一毛五,我可以再买别的。买什么别的?没有想好。
买米卷的孩子很多,小手高高地举着,有一毛的、五分的,我的两毛很扎眼。
我挤在人堆里,高举着两毛,喊着:“一根!一根!”
有一只手来把我的两毛拿走。我看不见谁拿走了我的两毛,我的小手仍然举着,等着那根米卷和即将找给我的一毛五。
有米卷到了别的小朋友手里,可是没有米卷到我的手里。
我喊:“我的米卷!我的钱付了!”
没有人给我米卷。
上课的铃声响了,小朋友们一哄而散。只有我还在那里。
“我的钱付了,我要米卷。还有一毛五的找头。”我说。
那人凶巴巴地横了我一眼,“什么时候付的?付给谁了?”
我看着那人的手。那是一只苍老的手,遍布皱纹。拿走我的钱的是一只白白的年轻的手。
我不再说话,转身向教室走去。
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向妈妈说过。那是我的错,我想,她不知道,是万幸。
我在课堂上很认真。老师讲伽利略,我就把橡皮和三角尺举得高高的,然后一起松手,看它们是否能同时落到课桌上。老师因此让我站到墙角去。我在墙角仍然听得很认真,想着要把簸箕和扫帚同时拎起来再松手,看它们能否同时落到地上。
这件事情,应该也没有跟妈妈说过。其实在此之前,我几乎什么事情都会跟妈妈说,但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学会了缄默。
因为我希望每天回到那间小小屋子里,都能看到她开心的、舒展的笑容,希望我没有让她感到失望,没有让她的努力白费。
成长真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不过有件事情铁定说过,那是唯一一次在这所很好的小学里受表扬。老迈的数学老师举起我的作业本,用一种夸张的声音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干净的、最工整的作业!”
数学我一向不好,可是竟然因为数学作业受表扬,我的数学成绩就突飞猛进起来。
期末考试,我得了第七名。
我觉得自己像小马过河一样,不知道前面河水的深浅,不知道考这第七名是好还是坏。
很快,妈妈所在的工厂倒闭了。妈妈又拿回来两盏台灯,一盏送给了舅舅,另一盏送给了大姨姐姐。没有办法再付租金了,她必须回到乡下的家里去。
大概还有别的原因吧,但是,正如我不会把自己犯的错告诉她一样,有些事情,妈妈也会对我选择沉默。在岁月的长路上,我们的目光和心思所能照见的,唯有我们身旁的那一小团地方。
妈妈走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和她一起回去。
我毫不犹豫地、欢天喜地地说“要”。
五年级开学,我又回到了最最亲爱的大兴乡中心小学。我一回到那门上有个大洞的破旧课堂,找到我刻满小乌龟的破旧课桌,看到那斑驳得都分辨不出粉笔字的黑板,我的心就安稳得像落到软软的海绵里。
我又看到了班主任乌黑的指甲。他在教课之余收废铁,被他摸过的白粉笔都成了铁锈色。此外,他还有五亩地,我们班的男生都帮他种过地。可是我多么爱他,多么爱这课堂,多么爱这学校外无边无际的田野。
我写了一篇作文,叫《我的家乡》。他给我90分,让我读给全班同学听。
我写我妈妈“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他特地仔细地问过我妈妈的姓,跟我说,要改成“陈娘半老”,“徐娘”是人家的娘,你怎么能照抄呢?
课文有一篇《骆驼与马》,他一遍一遍地教我们。“各它与马,”他说,“各它,是一种比马还大的动物……”
在这样一所愉快的学校里,我考试无一例外,每次都得第一名。我得第一名像吃炒豆子一样,不,吃炒豆子还得费劲嚼,对牙口不好的人来说也是个难题,所以应该说跟喝水一样方便。咕嘟,第一名,咕嘟,第一名,就这样。
我不知道第七名怎么样,但是肯定地知道,第一名是好的。
我的第一次的城市流浪生涯,就此结束。
我以为我就此可以一辈子窝在妈妈和家乡的怀抱里。可是很快,十二岁那年的八月底,我收到县中的录取通知书,从此离开我生长的小村庄,很少再回去。“反认他乡是故乡”,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吗? 总之,我背负着妈妈的梦想,开始了我几乎是永久性的寄居与流浪。
妈妈很得意,因为她终于实现她的理想,把我送出了那片灰扑扑的土地。如果没有妈妈的努力,我现在大概正在某所乡镇企业,或者擦洗玻璃瓶,或者摇横机,或者缝制布娃娃的耳朵,或者,我会跟着做泥瓦匠的丈夫进城,为他浸泡瓷砖以及搅拌水泥。我的孩子会在裸露的水泥墙底下玩耍,拖着长长的鼻涕。我呢,在一边搅拌水泥,一边想着,不惜一切代价,要让孩子得到好的教育,离开这样的生活。
现在想想,妈妈后来看我的眼光,一直等于是在看那盏美丽的台灯放出的光芒。看着看着,那光芒便远去了,留下她一个人孤独而努力地生活着。
在妈妈去世之后不久,有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起一件事情来。
八岁那年,我寄居在大姨妈家。在一个寒冷冬夜,我躺在被窝里,忽然想回家。我在黑暗里哭起来。
大姨妈说,不要哭啊,哭了老虎来吃你。
我不怕被老虎吃,继续哭。我说,我要回家。
其实我家离大姨妈家并不远,走路大概二十分钟。
但那时是冬天的深夜。大姨妈说,路上有狗啊,咬人呢。
我哭得更响。大姨妈没办法了,叫大姨父,说,算了,送她回家吧。
大姨父骂骂咧咧地起床,抱怨着说,被窝才刚焐暖呢。
我们三个出了门。一出门我就不哭了。繁星满天,空气冷得像冰,我们用自己的身体破冰而行。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果然听到几声狗叫。可是我一点都不怕,我小小的心里满满的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喽!马上就可以被妈妈搂着睡觉喽!
一想到这里,我在异乡无边的黑暗中,泪流满面。
妈妈去世的第二年,我从远方回家过年,年三十到家,我一只脚在门内,一只脚在门外,站了很久。外面鞭炮阵阵,可是无法驱除家里的凄冷,我觉得,只要外面的那只脚一进入,我的眼泪马上就会汹涌而出。所以我只能提着行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让父亲看到我回家,可是看不到我的眼泪。
在那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当我从寄居之地回家的时候,妈妈会不在家里等我。
没有妈妈的家,最终也变成了荒凉的流浪之所。
今年已是妈妈去世的第七个年头,终于我可以用平静而愉悦的语调告诉她有关我十岁那年发生的这一切。
亲爱的妈妈,那些年我没有对你说的事情,有关维B,有关米卷,有关伽利略,有关那盏美丽优雅的台灯,有关我对你所有的眷恋……从现在开始,让我统统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