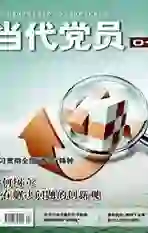掐断肿瘤的“补给线”
2013-12-29李衍
1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奖颁奖仪式现场。
颁奖仪式开始。
来自第三军医大学的卞修武站起身,整了整军装,扶了扶军帽,深吸一口气,迈着一名军人特有的坚定步伐,走上领奖台。
此时,卞修武突然想起了实验室里那些“老朋友”。
“老朋友”
1986年,出身皖西农村的卞修武经过层层筛选,保送第三军医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我国著名病理学家史景泉教授。
“别看这小子平时话少,但一提起科研就滔滔不绝。”史景泉说,“能吃苦,又能耐得住寂寞,这种人天生是块干科研的料!”
然而,入学不久,师徒之间就出现了分歧。
当时,史景泉带的研究生大多从事烧伤研究,这是第三军医大学当时实力最强的研究领域。
可卞修武却想将科研的主攻方向瞄准肿瘤。
“烧伤这块学术基础雄厚,更容易出成绩,你如果选择研究肿瘤,标本不多,方向不清,困难重重呀!”史景泉劝他。
面对导师的好心劝告,卞修武礼貌但又坚决地回答说:“肿瘤是病理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领域,不能因为存在困难,我就逃避。”
见学生决心已下,史景泉尽管略感遗憾,但十分欣赏卞修武的勇气。
正如导师所言,一进入肿瘤这一全新的领域,卞修武就遇到了重重困难,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标本。
“标本不够,找!”卞修武开始行动。学校的病理学教研室没有现存标本,卞修武将目光投向第三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距离学校最近的西南医院,成为他收集标本的主战场。一有肿瘤标本送到病理科,他就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打交道”的机会。
固定,脱水,浸蜡,包埋,切片,染色……对于每一块肿瘤组织,卞修武都会像对待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处理。碰上一块典型的肿瘤组织病理切片,他会爱不释手,恨不得通过显微镜把它看个一清二楚。通过日积月累,如今的西南医院病理科已经保存上百万张病理组织标本。
这些标本,既是卞修武研究的对象,也成为他特殊的“朋友”,他希望通过这些“老朋友”,去探寻肿瘤生成的蛛丝马迹。
“在各类肿瘤中,数恶性脑胶质瘤最为顽固,特别容易复发,就像韭菜一样,割掉了还会再长……”擒贼先擒王,卞修武决定拿脑胶质瘤“开刀”。
在长期随访恶性脑胶质瘤患者的过程中,卞修武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有一些患者并没有出现复发,手术后恢复很好,活上十年都没问题。”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个肿瘤。“即使是同一种肿瘤,它们之间也存在不同之处,那会是什么呢?”面对“老朋友”——显微镜下的病理组织切片,卞修武陷入了思考。
搜寻肿瘤的血管
1991年,第三军医大学图书馆。
阅览室一角,正在寻找博士研究课题方向的卞修武静静地坐着,埋着头,皱着眉,全身纹丝不动——除了眼球。
他捧着一篇医学论文,双手已微微出汗。
论文题目下面印着作者姓名和单位:“弗克曼,美国哈佛大学。”
三个多小时里,卞修武将这篇论文读了三遍。
论文中,弗克曼提出一条肿瘤治疗的新思路:减少肿瘤血管生成,“饿死”肿瘤细胞。
“这个思路很有道理!”但细看论文发表的时间,是在1971年。“20年前提出的理论,对现在还有多少意义?”卞修武有点拿捏不准。他决定仔细研究这一理论的应用成果。果不其然,20年间,根据弗克曼“饿死肿瘤”理论开发的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临床用药效果并不好。
“问题出在哪里?”在实验室里,卞修武又习惯性地找到他的“老朋友”——肿瘤切片,希望从它们身上找到答案。
“血管?没错,问题一定出在血管上。”显微镜下的病理切片上,与肿瘤细胞交织在一起的形态各异的血管,让卞修武恍然大悟,“20年来,大家都关注肿瘤细胞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血管,研究的方向是如何抑制血管生长,但恰恰没有深入到肿瘤血管的内部,去研究那些血管有何不同,为什么不同……”
“此后,我就专心做一件事情,研究肿瘤里面的血管。”卞修武回忆说。
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实验室,显微镜下,病理切片上,血管,血管,还是血管……五万多张肿瘤标本石蜡切片,被卞修武放在显微镜下,逐一分析。通过对这些“老朋友”的深入了解,卞修武终于有了发现:“八种,肿瘤微血管有八种不同类型!”
“小子,从1991年到1995年,你都是一个人在做,不容易呀。”卞修武的研究初步取得突破后,一直关注并支持他的史景泉称赞道。
“没事,我不累,况且我也没感到寂寞!”卞修武拍了拍显微镜说,“我的朋友可不少呢。”
史景泉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对父母尽到孝道。”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父母相继去世,成为卞修武此生最大的遗憾。
由于选择的课题难度大,又是基础研究,卞修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获得任何奖项。
为了深入研究肿瘤血管的奥秘,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卞修武组建了科研团队,他们利用手头的标本,组建了肿瘤组织芯片库。经过集中攻关,通过分析数以万计的肿瘤标本,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卞修武和他的科研团队,终于摸清了为肿瘤输送“给养”的“补给线”——血管。
掐断“补给线”
血管是肿瘤生长和转移的“帮凶”,但启动血管生长的细胞是什么,潜伏在哪里?这个未解之谜,严重制约着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的效果。
“国外一项研究显示,一种‘种子细胞’可能就是造成肿瘤复发和转移的‘凶手’。如果能找到这种细胞,对截断肿瘤的‘补给线’意义重大!”为了搜寻这种细胞,卞修武带领他的团队,又和“老朋友”较上了劲。
一天,团队成员余时沧找到卞修武:“在一些耐药性强的肿瘤里,会不会就有你所说的‘种子’?”
“有这个可能!”卞修武眼前一亮,“你立即进行这项研究!”
半年后的一天,病理科实验室。
“找到了!”一声惊呼响起。
一向沉稳文静的余时沧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显微镜。
经过不懈攻关,他不仅找出了“种子”细胞,还归纳出寻找这些细胞的方法!
实验室沸腾了。
“这将是研究肿瘤病理的一个重要新起点!”跟肿瘤组织打了20多年交道的卞修武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
2007年,卞修武团队成功鉴定了仅占肿瘤细胞总量约1%的肿瘤干细胞。两年后,国家“973”计划项目——肿瘤干细胞项目在西南医院启动,西南医院病理科建立的肿瘤干细胞库成为卞修武的“新朋友”。
在“新朋友”的“引领”下,卞修武及其团队按图索骥,找到了肿瘤的一大秘密。“肿瘤干细胞就是其他肿瘤细胞的起源。”卞修武说,对医生而言,这种细胞就是药物攻击的关键“靶点”!
“这是一项完美的研究!”消息传出,国际权威学术杂志《神经外科》如此盛赞。
“老卞,把你的研究成果申报评奖吧!”西南医院领导不止一次地劝他。
“不忙,不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小卞”变成“老卞”的他,总是摆摆手拒绝。与评奖相比,他更着急的是另一件大事——找到掐断肿瘤“补给线”的“七寸”后,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研究攻击肿瘤“靶点”的新药。作为一个医生,他知道,有很多肿瘤病人,正等着新药拯救生命。
除了1999年获得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后近10年,卞修武没有申报任何奖励。他说,搞基础研究,要的就是这样的精神。只有敢把冷板凳坐穿,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才能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推动科学向前发展。
正是这种“敢把冷板凳坐穿”的精神,支撑着卞修武长年埋头于实验室,与各种肿瘤病例切片为友。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卞修武及其团队负责的《肿瘤血管生成机制及其在抗血管生成治疗中的应用》项目,荣获201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月18日,在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奖颁奖仪式上,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的手中接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奖牌,卞修武突然想起了实验室里那些“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