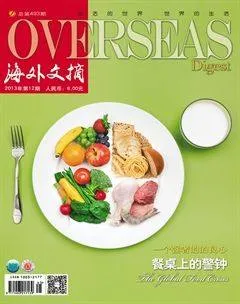母爱深沉
2013-12-29琳达·拉·普兰特

母亲去世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琳达,你确实发福了。”在那个时刻听到母亲的这句话,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笑还是哭。
母亲弗洛希的最后五年是在我家里度过的,她需要别人帮着穿衣服,夜里也需要有人照顾,但每天早上9点起床后,她就会容光焕发:化妆、梳头,穿上精心挑选的衣服。
母亲有个习惯,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每日邮报》。她会专心致志地把一份报纸从头看到尾,并且把她想要看的电视节目画上记号,作为利物浦足球队的球迷,还要在体育节目下面划上横线。有我出演的电视剧播出时,她经常是毫不犹豫地说,如果电视剧和球赛在同一时间播出,她会看球赛。
弗洛希那时90多岁了,我只能原谅她、接受她,但很多时候,我发现做到这两点很困难。我经常听到她为自己钟爱的球队呐喊助威,但几乎从没感觉到过她对我的支持。说实话,她变得非常以自我为中心,说话生硬,虽然我乐意照顾她,有时候也感到恼火,因为她好像从来都没理解过我。她知道我出了书,也演过电视剧,但她从不和我谈这些。
我只记得她提起过一次我写的小说《黑寡妇》,那还是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们俩一起看这部小说,母亲认为其中的一些性爱场面描写过于露骨,于是就读不下去了。“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些素材”,她斜了我一眼,对我说,“你应该写一些喜剧。”
我每天都要蹒跚着上楼给她送午饭,只要晚了10分钟,她就会抱怨。要是送饭太早了,迎接我的同样是不满的脸色。“噢,又不是鲑鱼,你该买几条了。”我上楼时经常看到她手里握着一杯雪利酒,见我没端来鲑鱼,她就这样问我。我们的午饭一般都是一盘肉、两盘加了肉汤和土豆泥的蔬菜,只是偶尔吃一次鲑鱼,她明明知道这些,却还是要故意抱怨。要是鸡肉炖得过火了,肉切得不够精细,或者我忘了先给盘子加热,肉汤不对她的口味,那她的牢骚就更不用提了。
直到她去世之后,我才懂得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那段日子。想起过去,我的心里有一种负罪感,因为我一直把照顾母亲视为一件头疼事。当一件件往事重新浮现在眼前,我开始欣赏起母亲那令人叹服的幽默,还有,她其实是理解我的,她从没劝过我要像别的什么人那样生活,或者逼着我去做我不爱做的事情。
她喜欢去看我的舞台演出,最爱看的是音乐剧《野姑娘杰恩》。母亲和父亲不止一次去看我演出的这个音乐剧。从谢菲尔德市的克鲁斯堡剧院走出来之后,他们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只不过弗洛希还会像往常一样给我一点小小的刺激:“你有一副歌唱的好嗓子,但是你不妨演一演喜剧。”
妈妈会为我的成就而自豪吗?我不记得她是否看过电视剧《黑寡妇》,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成功地被搬上荧幕。她从没提起过它,也没太多过问过我的事业。但她现在人已去世,我也不再多想这些。
相反,我回顾更多的是我在利物浦度过的美好童年,心里充满了对母亲不尽的感激。那是我人生中最为开心幸福的时光:在斯尼格里森林里骑自行车、在海滩上一玩就是几小时、假日里全家人出去玩时车上堆着一堆的板球拍、那些巨大的充气橡胶轮胎、还有妈妈讲给我们的叮嘱,我们家那时候总是养着很多动物,狗、猫、还有哥哥的鸟笼里养的一只驯鹰,一切历历在目。我们兄妹几个常去港口外的一座露天游泳池,我们像鱼一样在泳池里游着,我们那可爱的妈妈会几个小时在泳池旁坐着,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着我们,生怕我们出事。我们经常是在泳池大门刚一开时就到,玩到大门要关时才离开。
每当我们遇到麻烦,一定会得到父母的保护。记得有一次,我把邻居女孩的齐腰长发剪成了平头,即使这时母亲也替我撑腰。她没有训斥我,而是一脸严肃地告诉那个小女孩:“你绝不能让琳达拿着剪子接近你,她可什么都敢剪。”
母亲不是在开玩笑。有一次我又惹了祸,我和几个伙伴想在家里的车库中演一次节目,并且从当地教堂里要来了几件服装。这几件衣服穿在我们身上显大,我想都没想就把衣服剪下了一截,好让这些衣服适合我们的身材。弗洛希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才把些衣服缝好。
检查母亲要求随葬的物品时,我惊讶地发现竟然只有寥寥几件。她要求在下葬时穿一件她喜爱的利物浦足球队球衣,还有她用薄纸包裹起来保存着的三件东西:一只玩坏了的玩具熊、一个学生束发带和一件手织儿童背心。这三件母亲视为宝贝的东西是我的一个姐姐达尔的,她在我出生前就不幸意外夭折了。
达尔长得很漂亮,有着和母亲一样的浓黑卷发,和姥姥一样的水晶般的蓝眼睛。她六岁在一场车祸中受了重伤,后来只活了两个星期。父母很少提到过她,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丧失爱女留下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们的生活。
我是在母亲去世很久之后才理解她的爱女之心的,那是在我儿子生日那天,他吹灭生日蜡烛的时候。他是个可爱的小家伙,聪明,有时很调皮,但很有爱心。看着儿子,我就想起了达尔,儿子现在六岁了,和达尔去世时一个年纪,假如我失去了他,会是多么痛苦!达尔不仅是像照片上那样是个长相完美的小姑娘,而且幽默、聪明、健康活泼。我的父母当年失去的就是这样一个宝贝孩子,在我的儿子也长到六岁那天,我才真正地明白了父母的丧女之痛有多深。父母从没有让我们分担过一点点他们的痛苦,相反,他们一直是给予我们力量和自由,一直在鼓励我们尽情地实现自我,而不会带着生命无常的恐惧而生活。
直到现在我才对父母的悲伤和对我们几个孩子——哥哥、姐妹和我无条件的爱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失去母亲之后,我才懂得、才明白母亲曾经对我说的那几句刺耳话语和颐指气使根本不算什么。
[译自英国《好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