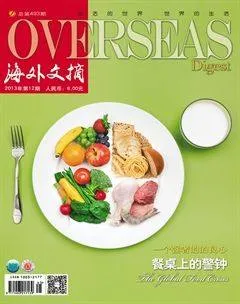印度医生谢蒂的平价医院革命
2013-12-29基多·明格尔斯


“您知道吗?印度每年有2800万婴儿出生,即平均每秒一个,而其中300万在五岁之前就因为本可以治愈的心脏病死亡。”谢蒂医生说。他曾是特蕾莎修女信任的医生,是穷人的外科医生、博爱主义者,也是医疗企业家、廉价医疗的领跑者。
他正打开一位病人的胸腔,采访就在手术过程中进行。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生命。收音机中放着印度流行乐,他喜欢在工作时听音乐。这里是印度班加罗尔,周一下午三点。
“印度每年有30万婴儿在出生的那天夭折。全世界五岁前死亡的孩子中,有七分之一是在印度。每十分钟就有一位印度母亲在生产时死去。”
他戴着口罩,我们只能看见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叫德维·谢蒂,白大褂上贴着的标签是德维。这个60岁的男人迄今为止已经为3万多病人做了手术。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其为“心脏外科的亨利·福特(福特汽车公司建立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的人)”,因为他将批量的原则应用在医疗上,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
他的目标是引起第三世界医疗领域的工业革命。谢蒂医生一边用刮板刮去病人血管中的钙化部分,一边讲述着他的观点。“印度培训出了一大批医生和医学专家,我们的患者人数世界最多,治疗方法也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在十年内,印度将成为全球卫生工业领头羊。”
人口大国印度,总人口12亿,到2050年可能达到16亿。在地图上观察这个次大陆的轮廓,可以看到一颗巨大的犬牙。对于3.5亿日收入少于一美元的印度人来说,生活非常困苦。这个世界人口第二的国家,世界核大国,本世纪中旬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过去2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是7%,世界饥饿指数排名却在81个国家中处于第67位。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但仍有几百万人创业失败。印度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尔塔·森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印度这样,进步如此迅速而全面,穷人却从中获益甚少。
生命的标价牌
德巴西斯·桑塔四岁,心脏里有个洞。
他和父母一起坐在谢蒂医生开办的“纳拉亚纳健康城”(Narayana Health City)大厅中。这个矮小、营养不良的男孩患有心室膈缺损,血液中没有足够的氧气,手指、脚趾和舌头因此常常呈现蓝色,人们叫他“蓝孩子”。德巴西斯咳嗽着,他的妈妈普拉提玛在他双眉之间画了一个黑点,她认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如果不进行手术,这个男孩肯定命不久矣。而他只是印度几百万穷苦病人中的一个。
“我给生命一个标价牌。”谢蒂医生说。在他门诊室的写字台上,放着心脏模型、甘地塑像,墙上挂着印度神明克里希纳的彩色油画像。下一位病人正在角落的沙发上等候。谢蒂说,他每天要接诊50到70位病人,做两到三台手术。
“给生命一个标价牌”是什么意思呢?谢蒂回答,他年轻时在加尔各答做外科医生,在他告知那些没钱的病人手术的必要性时,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需要多少钱?“当我告诉他们手术费用之后,他们对我表示感谢,从此再也没来过医院。”谢蒂暗下决心,不能再因为费用问题让病人无助地死去。2001年,他用岳父的资金在班加罗尔城郊建起自己的诊所,努力降低成本,同时保证质量。价格表上的数字要足够低,就是穷人也能够承受,能够继续活下去。为了达到这一点,医生谢蒂成为一个商人,心脏的折扣商。
在12年的时间里,谢蒂的诊所扩展为19家连锁医疗中心,遍布整个印度。谢蒂有很多榜样:美国连锁企业沃尔玛,Ryanair和Air Asia这样的廉价航空公司,日本汽车工业。谢蒂将超市的原则应用到公共卫生领域:便宜、简单、可靠。医院已经购入1.3万张床位,到2018年要达到3万张。医院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班加罗尔的医院获得了权威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JCI)的认证。全世界仅有78个医疗机构拥有这一资格,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只有极少在发展中国家。
谢蒂能够拿到认证,归功于他大宗购买的策略。班加罗尔纳拉亚纳健康城是他健康事业王国的首都,在10万平米的面积上,坐落着心脏病、癌症、眼病和其他疾病的专科医院。医院一共有3200个床位,就像那些让飞机尽可能少时间在地上的廉价航空公司一样,谢蒂医院的手术室也一周六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有1000个床位的心脏病专科医院,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规模巨大,这里的外科医生去年共完成了1.14万次心脏手术,平均每天30多次。相比之下,德国夏里特医院心脏病中心只有168个床位,去年进行了共3000次手术。在谢蒂的医院,每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平均费用是1500欧元,只有印度其他私立医院价格的一半。在德国,这种手术根据其复杂程度费用为1.2万欧元到1.7万欧元不等,在美国甚至达到1.5万欧元到3万欧元。
德巴西斯的生命标价牌上写着:12.5万卢比,合1500欧元。
不免费治疗
在医院中,一头牛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心脏病中心大厅里,几百位病人坐在椅子上,几个锡克教教徒蹲在地上,一位穆斯林母亲给罩袍下的婴儿喂奶。
穷人们站在拉克西米·马尼办公室前等待着。马尼是医院捐款部门负责人,这个65岁的男人有着坚毅的目光,那些就连纳拉亚纳医院的最低费用也无法承担的病人,会过来找他。门打开,轮到德巴西斯和他的父母了。德巴西斯坐在他哭泣的母亲普拉提玛膝头,他的父亲司瓦凡沉默地站在一旁。司瓦凡是建筑公司的帮工,每月能挣4000卢比,合50欧元。马尼看着电脑屏幕,告诉他们,如果要拯救他们儿子的生命需要多少钱。
“这是一场复杂的手术,全价要21.3万卢比,我们给你们特价,只需12.5万卢比。”
孩子的父母面面相觑,他们没有这么多钱。
“你们有多少?”
“3万,我们可以找朋友借到这么多。” 普拉提玛说,“一旦我们收到售出的土地得来的钱,还有3万。”
6万卢比大约是700欧元。手术还差6.5万卢比,即800欧元。这笔钱将由马尼为他们向一个慈善基金会申请。
桑塔夫妻俩不禁跪倒在地,好容易才抑制住想要亲吻马尼脚的冲动。三天后,他们又来了,向和谢蒂医院有着合作关系的“拥有一颗心”基金会的代表讲述家里的情况。只有在确定病人确实需要这笔钱后,基金会才会同意捐款。
马尼说,不能免费治疗穷人,这样医院会陷入经济困难,“会被病人淹没”。在谢蒂的医院,价格是适应顾客承受能力的。约60%的病人付全价,40%的病人能够获得折扣价,极少数可获得免费治疗。富人会给穷人补助。班加罗尔约40%的病人以某种形式获得了国家补贴。而桑塔一家没有得到。
桑塔一家来自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小乡村,距离班加罗尔1800公里,坐汽车约需四天。在加尔各答,他们找不到愿意接收德巴西斯的医院。后来,他们听说了谢蒂医生在班加罗尔的医院,听说那里没有病人会被拒绝。他们卖掉自己的土地,以支付手术费用,普拉提玛甚至卖掉了她的出嫁首饰,他们付出了他们拥有的一切。问起他们是否考虑再生一个孩子时,普拉提玛否定了,她将手放在儿子头上:“首先我们必须救活这一个。”
班加罗尔南部的一个大建筑工地,就是桑塔一家如今生活的地方。这里有为印度新中产阶级修建的豪华住宅,永远不会属于他们。“我们的儿子”,普拉提玛说,“却有可能住在像这样的地方。”她望向那些拔地而起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旁边是一间间用波纹板和树枝搭成的小屋,这里就是几百建筑工人的临时住所。他们中的很多都像帮工司瓦凡·桑塔一样,和家人一起暂时生活在这里。孩子们在混凝土搅拌机间玩耍,一个大垃圾坑就是他们的游泳池。高楼建成,小屋就会拆掉,工人们离开,寻找新活。
2013年7月14日早上八点,德巴西斯·桑塔在纳拉亚纳健康城儿童心脏中心接受手术。在妈妈纱丽服中的塑料袋中,藏着他们为手术筹集的6万卢比。在走廊的彩色墙壁上,米老鼠和其他德巴西斯不认识的图像在微笑。第二天,一个外科医生合上了他心室之间隔膜上的那个洞。男孩醒来后,认出了爸爸、妈妈。他的心脏跳动着,一分钟一百次。他渴了,轻轻地呼唤着“妈妈”。
梦,不仅仅在印度发芽
在谢蒂医院门外,是鸣喇叭的汽车、喃喃的祈祷、多音节的闲话、城市小贩的跳蚤市场,有时还传来苹果手机的木琴铃声。班加罗尔最先进的霍苏高速公路连接市中心和电子城市区,电子城里有数十家跨国公司,比如西门子、博世、通用电气和惠普,它们充分利用这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廉价劳动力。印度汽车品牌塔塔纳努(Tata Nano)让它西方的竞争对手们震惊,印度IT巨头印孚瑟斯(Infosys)更是平手起家,占据了世界市场,那么谢蒂医生的医院有何理由不能成功呢?
如今,谢蒂的目光早已投向印度之外,他想将自己的梦想蓝图扩张到非洲、南美,甚至欧洲。来自70个国家的病人占据了班加罗尔医院床位的10%,他们主要来自非洲和中东。谢蒂想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将他的廉价医药出口到很多国家。加勒比海开曼群岛上一个医院正在投入建设,2014年春能够开业,将面向美国病人。谢蒂说:“我们想让美国人看看他们荒谬而低效的卫生体制,看看如今的可能性。”2011年,时任斯洛文尼亚总理博鲁特·帕霍尔带领一支访问代表团来到班加罗尔,讨论在斯洛文尼亚成立分医院的可能性,以服务欧洲病人。此外,谢蒂还和格鲁吉亚、马耳他进行了相关洽谈。
59岁的美国人布里安·纳瓦林斯基于2011年来到班加罗尔,因为很多美国医生对他说,做手术风险太大。一个医生说他最多还能活五年,一家医院给他开出的费用预算有20多万美元。他在网上寻找其他可能性,谢蒂医生的名字一再出现。他得知,只需花费1.9万美元,他就可以继续生存。他坐上了飞机。
助理医生安-劳尔·科林来自法国,她站在谢蒂外科手术室旁,想从他那里学习,她本可以在欧洲的医院工作,但是科林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解决卫生事业中最重要的问题——费用问题的。另一位助理医生麦克肯纳称其“想看到心脏外科的未来”。于是他们也坐上了飞机。
德维·谢蒂是南印度芒格洛尔一个餐馆老板九个孩子中的第八个,14岁时他听说,南非医生克里斯提安·巴纳尔德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年轻的谢蒂也想做到这一点。在印度大学进行医药学习之后,他在伦敦盖伊医院心脏外科工作了六年,英国医疗体系的实用主义原则深深地影响了他,1989年,他带着他最重要的医学理念回到印度:人们无法在经济上承担的治疗,是毫无作用的摆设。
谢蒂的廉价原则在距离班加罗尔三小时车程的城市买索尔新开的医院得到了最极端的实施。这里的医疗费用比班加罗尔更低。一次简单的心脏手术只需1000欧元,谢蒂的目标是降到600欧元。这个有200个床位的医院,在十个月内用预制的建筑部件建成,只有一层,这样可以省去昂贵的地基和电梯费用。病人在有50张床位的大厅中过夜,床位之间只用帘子隔开,只有诊疗室中有空调。病人的家属需要上多个小时的陪护课程,这样他们能够帮助护士做简单的工作,比如换绷带。这样医院所需的护理人员减少了10%。根据这个模式,谢蒂决定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在印度乡村建100个同样的医院,以照顾到医疗条件非常糟糕的农民。
谢蒂认为,大宗医疗能够保证质量,他的医生在大数目的病例基础上锻炼出来的熟练程度,是西方医生无法企及的。就像流水线生产一样,手术室中也有工作分工:实习医生切开皮肤,打开胸腔,做好一切准备之后,主刀医生才出现在手术室中应对手术最棘手的部分。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伟大成就,在实现之前都被认为不可能。” 谢蒂在他的办公室中挂着这样的句子,还挂上特蕾莎修女的照片,他曾给她做过心脏手术。他认为单人病房是一种罪过,认为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主要是需求导向,而不是成本导向的,因此“贵得变态,太过技术化,太奢侈”,因此“没有未来”。
“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来自一个60岁退休、70岁死亡的时代。而如今,活到95岁的人已不鲜见。从长远来看,纳税人的钱不能负担这种可怕的养老结构。”谢蒂说,“他们总是在发明新药片、新疫苗,以及复杂、昂贵的仪器,而我们真正需要的,却是诊疗过程的革新。”如果有人对谢蒂的观念提出批评,比如外科医生的工作时间很长,他表示不理解这种指责:“战争中的士兵也不能五点准时下班回家。”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在谢蒂的医院,每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平均费用是1500欧元,只有印度其他私立医院价格的一半。在德国,这种手术根据其复杂程度费用为1.2万欧元到1.7万欧元不等,在美国甚至达到1.5万欧元到3万欧元。
病人在有50张床位的大厅中过夜,床位之间只用帘子隔开,只有诊疗室中有空调。病人的家属需要上多个小时的陪护课程,这样他们能够帮助护士做简单的工作,比如换绷带,这样医院所需的护理人员减少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