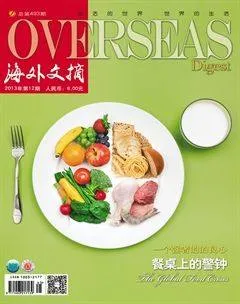一个强者的的良心
2013-12-29杰弗里·杰托曼


卡加梅绝对是上帝对卢旺达的恩赐。他严肃自律,能力超群,是一个斯巴达式的人物,他每晚都要工作到两三点,最常翻阅的杂志是《经济学人》,认真研读国内每一个村庄的发展报告。卡加梅一直试图寻找最好的方式,最有效地分配卢旺达每年接受的国际援助。
因为成功重建卢旺达,保罗·卡加梅成了举世闻名的英雄。但是,要清理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不可能不遭遇道德上的危机。面对《纽约时报》记者杰弗里·杰托曼的拷问,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强者的良心。
从人间地狱到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的官邸坐落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一座山顶上,我搭乘出租车前往。在基加利,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优雅得让我吃惊。尽管卢旺达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基加利绝对是世界上最整洁的城市之一。
在这样一个周六早晨,一队队戴着白手套的市政女工在清扫路面,她们一边劳动一边愉快地哼着歌儿。与很多非洲城市截然不同,基加利的大街上没有随处可见的垃圾,没有挂在篱笆和树梢上迎风飞舞的黑色塑料袋。在这里,看不到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在人行道边睡觉。卢旺达的警察会把流浪汉和小偷小摸者遣送到位于基武湖小岛上的青年康复中心。小岛风光秀美,物产丰富,被卢旺达人戏称为小夏威夷。由于政府严令禁止,基加利根本没有贫民窟。
前一天晚上从餐馆出来时,已过午夜12点,打不到车的我只好步行回酒店,这在其他非洲城市绝对是个危险至极的决定。但卢旺达却是我待过的最安全的地方,其治安之好可媲美苏黎世。很难想像20多年前这里曾发生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3个月内,胡图族人用砍刀和大棒,有组织地杀害了约100万图西族人,受害人数之多甚至超过了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卢旺达人常说,当时的惨烈外人永远难以体会,可如今在这个同样的城市里,连乱穿马路的人都很难找到一个。
一个复杂的领导人
在非洲,甚至在全世界,都找不到一个像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惊人的转变,卡加梅就是这一变革的总指挥。与一些非洲同行相比,卡加梅绝对是上帝对卢旺达的恩赐。他严肃自律,能力超群,是一个斯巴达式的人物,他每晚都要工作到两三点,最常翻阅的杂志是《经济学人》,认真研读国内每一个村庄的发展报告。卡加梅一直试图寻找最好的方式,最有效地分配卢旺达每年接受的国际援助。他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常客,与比尔·盖茨等名流谈笑甚欢。“克林顿全球倡议”颁发给他“全球公民”奖,赞扬他“解放了卢旺达人民的心灵和思想”。
虽然卢旺达仍然十分贫困,这里人们的日均生活费还不到1.5美元,然而与以前相比已有了很大提高。在卡加梅政府的领导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了70%;过去5年内,卢旺达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一个全国性的健康保险项目应运而生,虽然很多经济学家都曾表示,西非国家不可能拥有这样的项目。卡加梅还大力推动女性参政,目前卢旺达议会拥有最高的女性议员比例,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先进的。
然而,卡加梅确实是一位非常复杂的领导人,问题不在于他取得的成果,而在于他采取的手段。他素来拥有残忍、野蛮、冷酷的名声,无情镇压国内叛变,秘密支持邻国刚果的血腥反叛。在不少联合国官员、西方外交官以及逃离卢旺达的异见人士眼中,这个干净整洁、锐意进取的国度里越来越没有自由。在卢旺达,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的影子,就连在家里穿件脏衣服都被明文禁止(卡加梅认为这种行为不卫生,会传播疾病)。很多卢旺达人都告诉我,他们觉得总统无时无刻不在监视自己的生活。
对于很多国家,只要他们能符合美国的利益,例如保证石油供应或遏制穆斯林极端主义,美国在其人权问题上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卢旺达不同,它对于美国没有显著的战略意义。卢旺达是一个身处非洲腹地的弹丸小国,自然资源贫瘠,也没有肆虐的伊斯兰恐怖分子。为什么西方,特别是美国,会这样支持卡加梅,甚至对他的专政视若罔闻呢?一位驻卢旺达的美国外交官告诉我,“卡加梅在非洲这块腐败滋生、‘失败国家’遍地的大陆是一个难得的进步象征。他的出现装点了国际援助的门面。”“每年烧10亿美元进去,你总希望看到好结果。”卡加梅毫无疑问十分残暴,但支持他符合西方各国利益,因为他证明了对非援助不是肉包子打狗,证明只要有对的领导人,贫穷落后、四分五裂的国家就有希望。美国需要一个成功故事,而卡加梅给了他们想要的。
非洲的新加坡
出租车在总统官邸门口停下。卡加梅的助手领我走过金属探测仪,来到一间宽敞的接待室。此前,我看过很多卡加梅的照片,在卢旺达,几乎每幢政府大楼或大公司都会悬挂他的画像。但此刻在这间接待室里他的画像仍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的巨大和逼真。墙壁上,卡加梅表情威严地向下俯视,头微微倾斜,目光如炬。在这逼人的注视下我居然有点坐立不安,以至于当卡加梅的真人悄无声息走进来时被他吓了一大跳,以为画上的人复活了。
但眼前真实的卡加梅并不锋芒毕露,他甚至羞涩地笑了笑,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他穿着蓝色上衣、条纹衬衫和一条宽松的长裤,脚上的拷花皮鞋擦得锃亮。我知道他很高,约有1.88米,但令我吃惊的是他几近病态的瘦,肩骨和腕骨都很突出。
今年55岁的卡加梅在乌干达境内的难民营长大。卡加梅是图西族人,图西族王朝统治卢旺达长达几世纪,直到1959年形势大变。胡图人杀死了成百上千的图西族人,很多人被迫逃离家园,卡加梅一家也在其中。12岁时,卡加梅终于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我们是难民,为什么生活如此悲惨,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卡加梅说,正是在那一刻,他的政治意识觉醒了。高中一毕业,卡加梅就加入了乌干达反对组织。当兵后,他一路晋升,并通过美国国防部培训非洲军人的项目在堪萨斯州里韦沃斯士官学院进修过一段时间。
但卡加梅在培训项目结束前就匆匆回国,并于1990年领导图西反对军进攻卢旺达。他很快成为卢旺达爱国军的领袖,这支军队以推翻胡图政府为己任。1994年4月,胡图族总统的飞机被反对军射下,胡图族极端分子煽动群众屠杀图西族人进行报复,直到卡加梅的军队冲进首都,阻止了大屠杀。图西军队掌权后,卡加梅先后出任国防部长、副总统和总统。根据卢旺达宪法,总统任期为7年,可连任一次,这样算起来卡加梅可以执政到2017年。
卢旺达是非洲最拥挤的地区之一,1100万人口挤在比美国马里兰州还小的一片土地上。大部分卢旺达人是农民,他们的生活全部依赖土地。从莎草沼泽到云雾缭绕的山顶,几乎每一寸土地都为人占有。我问卡加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表示目前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鼓励妇女节育。“无论在学校还是社会,我们都努力倡导妇女说‘不’”,卡加梅皱着眉头,神情十分专注,“我总是告诉女性去做点别的,你们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就算是卡加梅最坚定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在他的治理下,卢旺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卢旺达人的平均寿命由1994年的36岁提升至56岁。疟疾是卢旺达人死亡的头号病因,为了抗击疟疾,卡加梅政府展开了大规模行动,喷洒除蚊药,发放蚊帐。经过这些措施,由疟疾引发的死亡人数从2005到2011年下降了85%。卡加梅在卢旺达建造了数百所新学校,铺设了高速光纤,还明智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地热发电厂等对环境无害的项目。尽管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又身处非洲中心,离海岸线数百英里,卢旺达仍是目前非洲大陆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被称为“非洲的新加坡”。诚然,卢旺达不会成为新加坡那样的工业港口,但卡加梅希望能够通过咖啡、茶叶和大猩猩来打开发展大门。卢旺达拥有世界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山地大猩猩,每年都能吸引众多西方游客。
对“暴君”的采访
采访过程中,一位身着背心的保镖数次走进来,确保一切顺利。厚厚的窗帘挡住了毒辣的太阳,也混淆了屋内的时间。卡加梅继续他的魅力攻势,向我大谈特谈卢旺达农业发展,因此当我提起有人叫他“暴君”时,卡加梅明显脸色一沉。
一位与我交谈过的卢旺达异见人士曾提醒我,见到卡加梅后千万不要被他的平静气质迷惑,他其实非常暴力。大卫·赫芭拉(曾是卡加梅的心腹,于2010年出逃至约翰内斯堡)也给我讲过一起他亲眼目睹的事件。2009年一天,卡加梅命两名手下去他的办公室,其中一名是财政官员,另一名是军队将领。门关上后,卡加梅不知因何事就开始大声训斥这两人,骂完他还没解气,打电话叫来两位持警棍的警卫。卡加梅让这两名官员趴下,开始痛打他们。5分钟后,他打累了,警卫自觉地上前接替他继续打,好像已经是一种习惯。赫芭拉说看到这一幕,他反感到了极点。
很多为卡加梅效劳的人都说曾经挨过他的打。诺博·马拉拉曾是卡加梅的司机,现在逃到了英国。他说卡加梅鞭笞过他两次,一次是因为开错了车,另一次是因为倒车撞到了电线杆。“卡加梅真的需要帮助”,马拉拉说,“我觉得他患上了人格分裂症。”
当我直面卡加梅问起这些事,他突然把身体前倾,离我就二三英尺的距离,以至于我能清楚看见他下巴上的灰白胡须。当我罗列这些证据(包括详细的人名和时间)时,他并没有打断我。出乎我意料,卡加梅没有矢口否认这些体罚,只是给出了2009年那件事他自己的版本。他说他没有打人,只是推了其中一个人一下,他出手过重,那人摔倒在地上。
“我天性如此”,卡加梅说,“我有时挺粗暴,的确会犯这样的错误。”当我对这些细节紧追不舍时,他有点恼火了,“我们真的需要讨论每个人,每个情节吗?打人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手段。”我觉得把“可持续”一词用在这里实在很奇怪,他的关注点好像根本不在打人究竟对不对上,而是殴打下属并不会取得长期效益。
当我问到他2011年在纽约的豪华旅行时,卡加梅更恼火了。那一次,他住在每晚1.5万美元的文华酒店总统套房。卡加梅常自诩为节俭的国家领袖,与很多非洲总统的宫殿相比,他在基加利市中心的住宅相当朴素。当我问到卢旺达人民会不会同意他在纽约一掷千金时,他瞪了我一眼,恼怒道:“请停一下!”
但卡加梅很快冷静下来,他向后靠了靠,恢复了教授似的语调,甚至有几分打趣地说:“不知道我住在集装箱里你是不是会满意。”他不自觉地笑了笑,“战壕和帐篷我都住过,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什么是简朴,不需要。”
我们继续谈下一个话题。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卡加梅为平息种族冲突所采取的举动。卡加梅自信地告诉我,每一个卢旺达人可以自由地表达民族归属,只要不散布仇恨。但在基加利,当我向路人询问他是图西人还是胡图人时,我并没有得到答案。大多数人,包括那位在载我去总统府的途中从生活成本到摇滚音乐无所不谈的出租车司机,都不愿透露他是胡图人还是图西人,只说他们是卢旺达人。我并不想挑起事端,但我从很多卢旺达的异见人士那里听说,胡图人很受压迫。
于是有一天,我特意去到了卢旺达西部地区,希望在远离首都的地方,人们能畅所欲言。我开车行驶了100多公里,路过重重山丘,看到男人们运送一捆捆刚锯下的木头,看到女人们用金属罐挑水,还有赤脚踢着破布球的小孩。每个山丘都被分割成无数小块,每个绿色、棕色的小块上都种满了咖啡豆、玉米、甘蔗和香蕉。这些光着脚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着这块田地过活。
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叫阿尔弗莱德的乡村教师,他邀请我晚上去他家过夜。他的房子很小,没通电也没有自来水,每天得从离家250米的一条水管取水。阿尔弗莱德每天教课10个小时,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教育,卢旺达的学校不得不分上下午两批授课。晚餐是煮香蕉,为了招待我,阿尔弗莱德还特地开了一罐沙丁鱼罐头。他说卡加梅当权后家里的生活好了很多。“我的孩子吃的比我小时候多多了。各个方面都提高了,包括安全、教育、健康。”听完这番赞美,我几乎断定阿尔弗莱德是图西人。然而当我问他的种族时,他笑了:“我们现在都不谈这个,但在过去,我是胡图人。”
“上帝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创造了我”
令卡加梅反对者无比沮丧的是,他的独裁在国际上并不是秘密。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组织发布了大量报告详细公布卡加梅政府在国内的压迫手段。然而很多外交官和分析家却并不反感卡加梅的铁腕行为。一些人甚至告诉我,只有卡加梅这样有能力的强人才能给这片埋伏太多冲突的地区带来希望,才能让医院运转、警察工作,才能让这里的街道不再肮脏。自由在这些地方并不重要,如果连最基本的安全都保证不了,自由就是无稽之谈。这里最重要的是保障稳定,减少人们生理上遭受的伤害,让人的生命不受疟疾、饥荒和其他由贫穷导致的疾病威胁。
尽管如此,美国已经因为卡加梅卷入刚果内战而划下红线。去年,联合国调查人员披露,卡加梅的军队进入刚果,帮助臭名昭著的反政府武装M23。M23谋杀平民,轮奸妇女,给刚果东部地区带来了很多灾难。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谴责卡加梅的军队掠夺刚果资源,并将这些资源运往卢旺达,谋取巨额利益。
卡加梅一直否认参与刚果内战,拒不承认曾派兵进入刚果。采访中我一提起刚果,他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像知道我将要问什么。接下来,他回顾了两个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当时刚果政府曾帮助卢旺达胡图政府打击卡加梅领导的反对武装。卡加梅承认,一些卢旺达士兵在刚果境内作战,但他说那些人都是逃兵。“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士兵逃走了。”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人看到卢旺达军队在刚果作战。然而这种解释根本说不通。像卢旺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上级的命令或默许,政府的军队能说逃就逃?当我提出这种疑惑,卡加梅反问我道:“你是真的不明白吗?那我问你,为什么连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都不能管好边境,还有那么多毒品从墨西哥流入?难道美国政府不想阻止这一切?这种事情都有它自己的复杂性。”
窗帘的缝隙间太阳慢慢西下,卡加梅脸上逐渐流露出倦意,他每晚只睡四到五个小时。他的回答越来越短,停顿越来越长。当采访结束时,他的表情甚至有点忧伤。卡加梅慢慢从椅子上起来,抖抖裤子,准备和我说再见。“我有很多称号”,他说,“有些我接受,有些是不公平的。”最后,在我离开前,他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对我说:“上帝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创造了我。”
[译自美国《纽约时报》]
只有卡加梅这样有能力的强人才能给这片埋伏太多冲突的地区带来希望,才能让医院运转、警察工作,才能让这里的街道不再肮脏。自由在这些地方并不重要,如果连最基本的安全都保证不了,自由就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