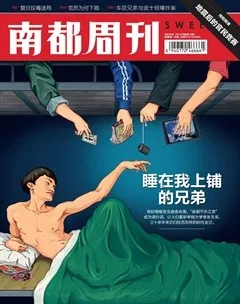“阅后即焚”的生意
2013-12-29洪玮

2011年夏天,美国众议员安东尼·维纳(Anthony Weiner)“手滑”,不小心把本要发给暧昧女网友的不雅照片发到了推特上,尽管他很快就删除了这条推文并号称自己的账号“被黑”,但在社交网络时代,发出去的图文信息绝对是泼出去的水—瞬间截屏四散,媒体报道也随即蜂拥而至。结果可想而知,本来被视为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接班人的安东尼只能被迫辞职。一颗政治新星就此陨落。
安东尼肯定没想到,发生在他身上的这桩倒霉事,却推热了一片新商机—“阅后即焚”类应用,比如Snapchat。这类软件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它们发送的图文信息是“朝生暮死”的—用户拍了照片发送给好友,在几秒钟内会自动删除,再也无法读取。如果安东尼当时用的是这类软件,人生可能就此不同。
现在,Snapchat已经荣登美国App store照片和视频类第一名,把YouTube和Instagram都踩在脚下。在今年4月中旬,Snapchat的每日图片分享数量已经达到了1.5亿张,这一数字在2个月前还是6000万。
这种短暂的、非永久性的数据应用缓解了网络社交时代的隐私担忧,有可能成为社交网络未来的发展方向。
很黄很暴力?你想多了
Snapchat 的想法萌发于2011年初,创始人埃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和鲍比·墨菲(Bobby Murphy)当时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斯皮格尔学的是工程,墨菲读的是计算机。他们制作这个应用的灵感据说是来自于朋友们的各种吐槽:社交网络的无孔不入让原本只是小圈子的私密照片,也能被广泛传播,甚至被搜索引擎永久收录。机缘巧合的是,当他们在做Snapchat测试版的时候,安东尼的艳照事件正在大热。有议员艳照丑闻事件渲染在前,Snapchat在2011年9月正式问世的时候,这款既能分享又能及时销毁的拍照工具自然颇受关注。
与此前最流行的照片分享工具Instagram最大不同的是,用户通过Snapchat分享照片给好友时,可以事先设置照片的有效显示时间(如1-10秒),一旦截至倒计时,这张照片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为防截屏,接收方打开文件时手指必须持续按着屏幕才能观看。当然,如果你有心,还是可以勉强截屏的,不过一旦接收方试图截屏,发送方也会收到警示通知。
其实像安东尼这样的人并不少,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6%的美国成年人曾经向朋友发送过 “富有性暗示意味的照片和视频”,15%成年人曾经收到过这样的东西。因为Snapchat “阅后即焚”的特殊功能,这款应用自诞生后就受到了不少批评,许多人都说它是情色软件—发送色情图片的利器,就连《纽约时报》都一度觉得它伤风败俗。
其实,也不怪外界如此评论,Snapchat在App Store上的原始截图就是身穿比基尼的漂亮MM,上面写着“成人或暗示性主题”等提示。时至今日,你登录美国的App store查看,还能看到许多使用者把试图泡妞或者寻找一夜情的信息穿插在软件评价里。在Tumblr上甚至还有一家名为Snapchat Sluts的网站,专门记录一名男子痴迷性息的趣事。斯皮格尔也坦承,“实话实说,我们的早期营销材料有点业余”。
不过,斯皮格尔也跳出来大声说是大家想多了。尽管他承认安东尼艳照事件对他们有所启发,但开发这款软件的本意并非为情色。他认为,现在的社交媒体特性让用户不得不努力一直塑造自己的完美形象,这反而不真实,有许多年轻群体就喜欢发搞怪照片给朋友,但又不愿意有朝一日被翻旧账,比如在派对里疯狂的照片。Snapchat就可以让用户随心所欲拍下真实的自己,甚至是犯傻的一面,让交流更人性也更自然。
肖恩(Sean Haufler)是一位耶鲁大学的计算机系的学生,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过Snapchat风行的原因, 并被 《福布斯》等主流媒体转载或引用。在这篇文章中,肖恩说自己一开始也觉得这个软件“很黄很暴力”,但细心分析后又发觉这其实是一种更亲密的信息传播方式,因为信息更直接、个人化,有效时间的设置也让用户心理上觉得舒服,而且Snapchat上的图片更像惊喜,让接收方毫无防备,“比如你用普通信息发给朋友一张大头照,觉得很突兀,但是如果是用Snapchat发送就会很自然。”肖恩说。
Facebook抄袭?无损反助力
Snapchat也不是一开始就得到市场认可的。两位创始人用了一个夏天在洛杉矶开发原型,吸引用户,当时几乎所有人,包括一些风投都觉得这个点子没什么前途。直到这个应用在洛杉矶高校间病毒式传播后,事情才发生了改变。
2012年3月,风投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找上门来,这家公司有一个管理总监叫巴瑞(Barry Eggers),他上高中的女儿告诉他,现在校园里最流行三个应用:愤怒的小鸟、Instagram和Snapchat—巴瑞开始对这家公司有了兴趣。
经过仅仅25分钟的谈话后,Lightspeed Venture Partners就决定注资485000美元。Snapchat团队一拿到钱就雇了一个社区经理和两个新的工程师。很快他们又敲定了另一家风投Benchmark Capital的A轮融资1350万美元,Snapchat的估价也涨至7000万美元。Benchmark Capital的投资家米池·拉斯基(Mitch Lasky)随后加入公司董事会,他也是云端游戏服务商Gaikai的早期投资人—Gaikai后来以3.8亿美元的价格被Sony收购。
Snapchat的崛起也让竞争对手感到了威胁。据媒体报道,Facebook就曾经想要收购它,但后者志存高远并没有答应。后来Facebook只好跟风推出了一个各方面都非常像Snapchat的同类产品Poke,扎克伯格甚至还亲自写了几行代码并且献声给这款应用,高调发布24小时内这款应用就登顶App store免费榜榜首,但意外的是Snapchat反而因Poke受到更密集的关注,今年2月它攀爬到了App store免费榜第4,而Poke则回落到70。
事后媒体分析,如今社交网站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储存用户的数据,然后把这些储存了人们行为和兴趣的信息出售,而扎克伯格骨子里也认为所有信息都隐含价值,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用户对Poke的信任度。
现在Snapchat已经可以发送视频,并有了安卓版。虽然它还没有明确的盈利模式,但如此快速的成长也体现了市场对非永久性数据的需求和重视。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自己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信息会被保存到服务器,或者被截屏传播,长期被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盯着看,这多少都让人感到恐惧。
皮尤研究中心去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显示,约半数社交网络用户对其隐私表示担忧,有44%的用户已经开始删除他人在自己档案信息中留下的评论,37%的用户开始把标记有自己姓名的照片删除。
这也验证了两位创始人的判断。尽管一直以来,用户都希望数据保存得越久越好,但非永久性数据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比如我刚生了小孩,一方面想和朋友分享喜悦,又不想自己精疲力尽的样子被保留太久,Snapchat此时就是一个好工具。”
大数据时代之患?被遗忘是权利
现在,市场上提供类似“阅后即毁”服务的公司并不只是Snapchat一家。2011年初,德国的研究团队就开发了一项叫做 “X-pire”的软件为上传社交网络的图片添加失效日期。同样受安东尼艳照事件启发的手机应用Wickr在2012年发布,号称“军事级防泄密”,与Snapchat使用者以年轻人为主不同,它的用户多是名人、政客、记者、律师、银行从业人员等,功能上也较前者更进一步,有加密步骤,且页面设置更稳重,以邮件的方式呈现,可发送能“自毁”的照片、视频、文本和PDF文件,连开发者也无法看到用户发送的信息。试想,你的商业伙伴在这种对话环境里,还能爆出你的什么料呢?
和这批应用同时兴起的是一股“被遗忘权”运动。2012年1月,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维尼·雷丁(Viviane Reding)提交了一项隐私立法提案,其中就包括一项有关“被遗忘权”的条款,其主旨是人们有权利将其在网站上处理数据的意愿收回。当今赫赫有名的大数据研究者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新著《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一书中,号召来场 “互联网遗忘运动”。他指出,“对于人类而言,遗忘一直是常态,而记忆才是例外。然而,由于数字技术与全球网络的发展,这种平衡已经被打破了。如今,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遗忘已经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了常态。”他认为,数字时代人们分享的信息被永远储存,必然会带来许多问题,而人类社会要前进,就需要学会遗忘。
不过,在技术上说,目前的这些软件cQf8agXwCqDrM74/fO8uTA==都并非是完全安全的,比如Snapchat在下载页的软件说明里就提醒用户,它虽然能告知你对方在截屏但无法阻止截屏行为,就算可以阻止截屏,有心人还是可以叫朋友在一边用相机给屏幕拍照;互联网新闻博客mashable也有文章质疑wickr的加密模式有可能崩塌。所以,爆糗有风险,用户需谨慎。
而现在,Snapchat等应用普遍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盈利模式。如果继续做免费App,可能就得引入广告,但这样很可能会造成用户体验降低;如果走收费路线,现在Facebook的Poke却是免费的,收费估计留不住易变心的年轻群体;而且由于这类应用的私密属性,他们又无法提供用户数据给广告商,只能通过推送广告的方式将广告商请进来。在肖恩的那篇文章里,他认为Snapchat可行的盈利模式或许是“在点开快照的时候先放1到3秒的广告”—用户一定满怀期待又不敢分神,生怕照片一闪即逝,在这种全神贯注的情况下放广告“就算时间很短也会很有效”。
不过,现在的Snapchat还是自信满满,在高涨的流量面前暂未打算把自己卖掉,“我不理他们,直到我们撑不下去了。”斯皮格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