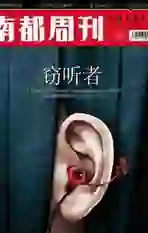我们身边的危险人物
2013-12-29郭巍青
厦门警方证实,陈水总是制造公交车惨案的凶犯。既然如此,从破案的角度可以说,一块心头大石落地。但是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却有很多人倒吸一口凉气,感觉一颗心更加被提起来,悬得慌。
这首先是因为,陈水总的一生异乎寻常地简单清楚。除了在出生日期上由他挑起争议之外,他的六十年(或五十九年)人生历程中,连个错误都没有。在舆论的聚光灯下,迄今也未见有什么重大冤屈,或阴暗的、脱轨的劣迹恶行。可是清楚到这种程度,他的最后疯狂就太难解释。陈水总其人其行,因为太清楚,以致说不清楚。
这样的不清楚及其带来的血光之灾,太令人恐怖。它仅仅是极端个案呢,还是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再次出现?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有风险忧虑。由此来看,《厦门日报》号召“共诛之”,根本就不是严肃的风险应对策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有风险,但风险源头如果又像陈水总一样不可事先预知,那么你诛谁呢?万一恶行真的出现,那也不必诛,因为一切都只会太晚。
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们必须妥协,公交车还是要乘坐的。但是,负责任的政府以及社会应该面对风险,认真反思。而这需要从多种视角,提出各种假设。
我的假设是,厦门公交惨案,提醒我们高度注意城市中的贫困。城市贫困是一种特殊的结构,身陷其中的人,很难获得一种补偿机制以求心理平衡或者解脱,因此可能导致不能预测的个人行为暴力。所谓补偿机制可以是物质性的,比如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种社会地位。它也可以是心理与文化的,比如另外一种评价尺度,另外一种身份认同。
以农民工为例子,可以看得更具体。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很苦很贫穷,那些从事粗重体力活儿的尤其如此。可是,城市与乡村两种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农民工在客观上有一种特殊的便利,即在日常苦难之外,有另一种补偿机制存在。别的不说,一年一度的春节返乡与家庭团聚,除了艰辛,还有欢欣。空间与时间尺度的巨大变换,有一种调节作用,类似于放松、释放、肆意、甚至狂欢。在冷漠艰难的生活环境之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乡(真实的或想象的),是一种补偿机制。
一个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当个保安或城管,月入千把两千,这在城市中,只是茫茫人海中不知名的一员。但是回到偏远的乡下,他可能算是个人物,在大城市的大机构中任职,有了经济,有了见识。换言之,另一种评价尺度的存在,给人在另外一个维度上重建身份与尊严。
从这样的角度回头看陈水总,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处在贫穷的阴影之下。真正糟糕的地方还不是贫穷,而是他穷到连补偿机制都没有。他生于城市,因此没有一个乡下,可供他作为人生中的回旋空间。而在城市中,他被死死地吸附在贫穷这个范畴和实际情景当中。他没有文化,能做的工作当然是低收入的、不稳定的、甚至不合法的。无论是申请低保,还是接受街道的关心与帮助,他的身份永远是穷人,限于能力、机遇或性格,没有更改的可能。
唯一的可能性,来自于厦门市政府的那项政策,即上山下乡人员可以用当年的时间折抵社保缴款。从补偿机制的角度看,这应该是陈水总建立自身主体性的唯一一次机会。他生命中曾经受过的苦,是有价值的,是可以补偿的。一个有基本保障的晚年退休生活,成了他唯一的“家乡”。或许在那里,他将能够放下艰难的谋生与劳作,获得喘息与放松。因此,为了出生年龄问题如此争执,反而容易理解了。也许这就像一张年前返乡的火车票,这时候跟他说晚一点再回去也一样,是没有意义的。
陈水总作为一种类型应该令我们警醒。一个人如果只有城市身份,又只有贫穷身份,那么无论对个人还是城市,都将是巨大风险。然而城镇化正在将所有人都转化为市民,却又不能保证将所有人都转化为足够富裕的市民,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乡村贫穷转化为城市贫穷时,风险的形态和烈度都会变化。
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