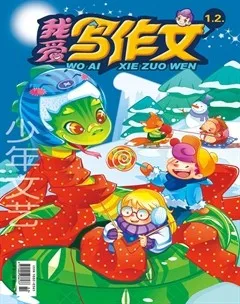火中美味
2013-12-29朱秀坤
儿时,特馋,整天想着吃,春天的茅草芯、初夏的嫩蚕豆、冬日水田里的野荸荠,都是我们的腹中美食。尤其是小时候吃过的那些火中美味最过瘾,最馋人,最香甜可口。
那时每天放学后烧晚饭是我的必修课。檐雨滴答的春天是有些寂寥的,耐住性子坐在灶门口,一把一把机械地往锅塘里填稻草,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借到三歪子那本《格林童话选》。但一阵奇异的香味吸引了我,睁大眼朝红彤彤的锅塘里看,发现火星闪闪的灰烬里竟有点点洁白的花朵,像极了树上的乌桕籽,于是我看到了这世上最轻微的一种爆炸,“啪——”“啪——”敢情是稻草上未脱尽的一小撮稻谷在火光里炸成了爆米花呀。顿时我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顾不得烫,连同灰烬抢了一小把出来,拈上一颗,又一颗,送进嘴里,呀!香,甜,酥,微微的脆,眨眼间已化在了舌尖。从此我爱上了烧晚饭,只为那最小最香的爆米花。后来,烧到黄豆秸时,我欣喜地发现竟也有些豆粒留在豆荚里,需迅速从火中抢救,否则就成了灰,空余阵阵豆香了。有时也会将豆粒剥出来,聚少成多,夹些火灰盖上去,一会儿便听到“砰——”“砰——”的炸裂声,可爱的黄豆散发出好闻的焦香味,吃在口中,又香又脆又过瘾,和爆米花完全不同。
春末夏初,豌豆花开得如火如荼,正是小麦灌浆时。放学途中或打猪草时,我们会摘些墨绿色的麦穗,将那青嫩的麦芒轻轻摩挲在同伴的脸上逗着玩,痒痒的,有趣。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试着用火来烤那青麦穗,没想竟洋溢出扑鼻的清香,等麦芒烧去,迫不及待地剥掉麦壳,取出烤熟的麦仁嚼起来。韧、软、清,还有微微的甜在味蕾间飘浮,不同凡俗的香!
到了秋天,最常烧烤的便是玉米棒,直接从地里掰回来,扔进锅塘便成。等到晚饭烧好,我的烤玉米也好了。用火钳夹出来,一层层剥开,最后就是个白胖子,连水红的缨子还在。一波波玉米的清香在灶间弥散开来,你想拂去根本不可能,只能乖乖地被它俘虏。一粒粒玉米籽啃起来,实在是香极了。有时我也会抓一把花生在火里烤,却总捡不干净,有些根本夹不出来,在烈火中献生了。不过,烤花生尤其是烤嫩花生,其香与美又不是烤玉米可以比拟的。最让人心仪的还是烤山芋,可以从硕果累累的秋天一直烤到冰天雪地。当我坐在让灶火烤得暖洋洋的锅塘前烧晚饭时,我总不忘扔一只大山芋进去,好聆听着窗外推磨般怒吼的西北风,等待山芋早些被烤熟,然后吹开腾腾热气,剥去黑乎乎的山芋皮。当我美美地享受糖分充足甜美诱人的烤山芋时,那种幸福与满足会从齿颊流淌出来,通过喉管,直达心灵。
白雪皑皑的冬月,似乎就是我们的烧烤季节。不在锅塘里,而是在母亲为我们装好火灰的脚炉里。蚕豆、黄豆、白果、花生、瓜子,有什么烤什么,篱笆上摘两颗枯去的老扁豆、老豇豆,也能烤。直接丢进脚炉就成,一会儿就熟,等到炉眼里冒出一缕青烟,赶紧揭开炉盖,用筷子抢出来。更让人兴奋的是,几个小伙伴一人一只脚炉,我们不为暖脚,只为了好这一口,仿佛一人一个烧烤摊,然后相互交换烤熟的吃食,咀嚼,品评,一个个俨然美食家,那种得意与炫耀,真让人开心。
记得我还在煤油灯上烤过吃食。先是白果,用来玩跳白果游戏的,赢多了,便忍不住用了母亲的缝衣针,戳上去,在灯焰上烧。就在我快不耐烦时,猛听得“砰——”一声,竟如山崩地裂一般,灯焰顿时小了半截,那白果壳随炸裂声飞走半片,剩下半片船篷样的拥裹着我手里的银杏仁,香,糯,微微有些苦,去掉里面的心,更美。还烤过粉丝——谁烤过粉丝吃啊!也是无聊透了,陪母亲在一朋友家里拉家常,母亲和那位好姐妹谈得起劲,哪里肯走?夜黑得泼墨似的,我可不敢独自回家。正好墙上挂了一包粉丝,我抽出一根在煤油灯上烤,一会儿粉丝膨胀开来,熟了,我放在嘴里嚼,咦,蛮好吃的。再烤,再吃,那粉丝越烤越短,一根吃完了,再抽,再烤,后来听她们谈得精彩,我入了神,仍将手指往前送,呀!赶紧缩回,手上已燎出了泡,才知一段粉丝已烤完了。
那时烤过的也不光是五谷杂粮,还有些小荤腥,吃过烤河蚌,连蚌壳都未劈开——手无寸铁也劈不开呀。好在用火烤一烤,河蚌也就乖乖地开了口,倒去一肚子腥味浓重的汤汤水水,我们照样吃得心满意足。最美味的还要算黄鳝,在稻田里捉上一两条,够不上一盘菜,干脆抹些盐,放锅塘里烤,烤出来的黄鳝会弯成大半个圆,虽吃得一嘴的黑灰,但那种野鱼的鲜与香却是今天很难尝到的。
这些——如今的孩子到哪里寻找呢?
发稿/沙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