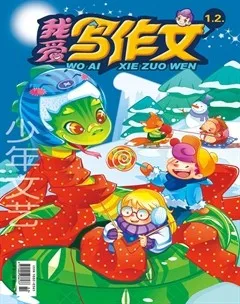严冬的甜蜜
2013-12-29宫凤华
严炸炒米
寒的冬天是乡村的一段空白。出太阳的日子,常见炸炒米的老汉挑着一副担子,晃悠悠地来到村子的空场上。“炸炒米喽——炸炒米喽——”炸炒米的搁下担子,支好炭炉,便亮开大嗓门来回叫喊。
炸炒米的老汉很少说话。别人在一旁说笑,他也不答腔,一脸严肃。不大会儿,老汉看看表,立起,将葫芦状的炒米锅扳起来,把顶端套进一个圆锥形的网袋中——袋口是用废弃的轮胎做的,上面有小孔。他左脚踩到上面,左手拿着扳手套到容器的“耳朵”上,右手抓住摇柄,高喝一声“响——呶”,左手用力一扳,“嘭”的一声巨响,容器盖便被冲开了,一股浓烟腾空而起,瞬间把我们淹没。
我们蹦跳着,一头扎进白雾里,拼命地吮吸着热乎乎香喷喷的炒米香,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惬意流遍全身。在我们的欢呼声中,寒冷的空气变得温暖起来。捧把炒米一尝,啧,挺甜哩!回家用绳子把袋口扎紧,以防炒米发软。
第二天一起床泡碗炒米,拈点糖,呼啦啦几口就扒下肚,身上暖烘烘的。晚上煮饭炖蛋,再加进几把炒米,味道真香。倘若家里来客,煮几个荷包蛋,撒上炒米,丢点蒜花,或来一碗京果粉泡炒米,保准让客人赞不绝口。
熬炒米糖的那个晚上,我们不停地吸溜着鼻子,拼命饱吸着那浓郁的甜香。冬天的寒冷在泛着昏黄灯光的茅草屋里化作灶膛里旺旺的火苗,化作我们嚼着炒米糖时脸上绽放的朵朵红晕。
过年之前家家准炸上几次炒米,用来熬炒米糖和花生糖。爷爷和奶奶熬的炒米糖最香,里面掺些姜末、橘子皮、红枣,脆香爽口,我们小嘴咬得咯嘣咯嘣响。
换棉糖
小时候,我们拖着鼻涕,穿着开裆裤,在小河里捉泥鳅,在竹林里掏鸟窝。只要村头歪脖子老榆树下传来糖担子叮叮当当的铜锣声,我们便一阵风似的,齐刷刷地拥向糖担子。
挑糖担子的老人戴着油光光的粽色雷锋帽,满脸皱纹,犹如核桃壳,穿着对襟布褂,腰间系着褪了色的蓝布带,显得干练而淳朴。
我们如一只只小鸭子,伸长脖子,望着箩筐上面的棉花糖,挤眉弄眼,不住地咽口水。那麦芽糖装在一个圆形的铁盒子里,像夏天奶奶摊的大面饼。切糖用的是一个小铁凿和一根小铁棒,轻轻一敲,糖便分开了。那弯月形的铁凿在他手掌上抛耍、摆弄,锋利的刀口上还粘着糖。
终于,禁不住糖的诱惑,我们悄悄潜回家,找来甲鱼壳、牙膏皮、胶鞋底、塑料膜、废铁、鸡毛等,来换麦芽糖或糊状的棉花糖。棉花糖用细小的麦秆儿绞,我们只用舌头舔。嘴角上涂了糖,像搽了口红。
每次,捧着一小块粉扑扑的糖,先翕动鼻翼,再用舌尖轻舔,绝不一下子塞进嘴里。除了换糖,我们还换一些小物件,糖担子前面的四个方盒子几乎是个百宝箱,针线、皮筋、鱼钩、铅笔……一应俱全。
那样的冬天,严寒被一阵阵甜蜜冲散,只剩下等待和享用。
发稿/沙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