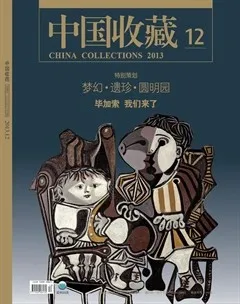古代小贩不怕城管
2013-12-29潘博成







古代有城管吗?难说。但古代肯定有很多走街窜巷、随地摆摊的小商小贩。他们地位卑微、辛苦营生,却能用琳琅满目的商品给他人尤其是孩童带来欢乐;他们微不足道、难登大雅之堂,却用最简单的方式诠释出古人与天地环境之间的相连相生。
在摄影术还不曾存在的年月,画笔便成为了记载万千行业的主要工具,尽管它是否逼真、是否可靠,并不容易被证实。由于中国画与生俱来的特性,在写实与写意、咏物与抒志、个体与场面之间相得益彰,从而能甚为活泼地显示出都市空间下,各个行业与其从业者的大小故事。
在山水花鸟铺天盖地的中国画领域,与小商小贩相关的作品相对而言甚是少见,其中得以传世者自然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在古代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士农工商的四民排序一向被严格遵守,位居末位的商人们,在韩非子《五蠹》中是“社会蛀虫”;在汉高祖朝代,不得骑马,不得着丝绸,世代不得为官;即便在开明昌盛的大唐时代,商人及其子弟也与科举无缘……更何况,一向讲究风雅别致的古代文人骚客,心之所向恐怕多为山高水长和鸟鸣虫语的清雅浪漫意境,即便是人物画,也多选择仕女、儒士和贵人达官者为多。但总归还是有不安分者,徐扬、计盛、李嵩,还有更多的无名氏——正是他们别出心裁地尝试让小商小贩走进画卷当中,也许夸张,也许写实,也许带有想像,但无论如何,当时的“小人物”因为画笔而得以传世,让后人一窥究竟,实属一桩乐事。
末等的行业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特色,即便是从商者,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古文载,“商”者乃行商运输之人,“贾”者为开店贩售之人,那么,“货郎”是谁?便是那些边挑担子、边吆喝,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小商贩。他们本钱卑微,既无法做大买卖,又不能开个店面,便只能选择当“小贩”了。
那么,小贩长得是什么模样呢?历代画家中,恐怕与货郎接触最多者,当属钱塘人士李嵩了。可能是因为出身贫寒,他对于货郎的艺术解读相当到位和精准,以至于其“货郎”形象成为了传世经典。李嵩笔下那位挑着重担、面露微笑的年迈老翁几乎成为不少人对货郎的经典记忆。但其实不然,只要稍加琢磨,更多的货郎往往并不年长,甚至还带着几分青涩和稚嫩,这才算得上是货郎主力军。而之所以老翁会成为货郎代名词,恐怕与惯用故事手法关系密切,悬念后文自会揭晓。当然,释读货郎,亦可由其衣着打扮入手,虽然到了宋代以后,货郎的社会地位微微改善,但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并未发生变化。简朴、实用和粗糙基本可以将货郎服饰予以概括了。无论是李嵩,亦或是苏汉臣,还是计盛,他们笔下的货郎都是以粗布做衣,身上或蒲扇别于腰间,或披风挂于脖颈,尽显商贩的务实色彩。
货郎卖什么?这是个相当有趣的议题。“琳琅满目”应该是最能诠释这个问题的词语了。团扇、水粉、胭脂,针线、布料,油盐酱醋……几乎无所不包。传为苏汉臣所绘的《货郎图》便比较生动地反映了此场景。“简易货架”上,各种大小罐碟箱碗,就像当下所谓的“便利店”一样,似乎可以找到生活需要的所有物品。而《清明上河图》则能够跳出个体,在群体角度一窥究竟。吆喝的小贩,贩售内容多之又多,草药、编织品、肉食、茶饮;更有不少小贩以提供服务为目的,补鞋、修面、看相、算命,可谓应有尽有。不夸张地说,小商小贩实现了那时商贸的昌荣——至少在画作观感上确实如此。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的存在,小贩总是能够成功营造出一种丰富与饱满的生活风格,在画中与现实中均是如此。
既然有品种多样的商品,当然得考虑怎么卖的问题。这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讨论小贩主题画作非常有趣的切入口。与《姑苏繁华图》里面的小贩相似,扁担是许多商贩的首选装备。李嵩作品中的老者也是刚刚放下沉重的扁担,开始向周遭的幼童与妇女贩售商品。但千万不要认为扁担是货郎们的惟一工具,且看计盛笔下的明代货郎,其货郎架之精致美观,甚至令人迷惑,这真的是货郎吗?一人半高度的货郎架,不仅造型优雅,边角间还有写意纹饰,架子顶部悬挂着若干鸟笼,为数不少的小鸟或栖息笼中,或停于帐中,原来这是一架属于“鸟语”的货郎架!由此自然不难推测这位货郎的经营业务了。
作为人物画的一类,显然小商小贩并不能创造多少艺文雅趣,但它的精髓在于对某种社会群体的真实现场的临摹。这种意念在中国画的传统语境中其实并不多见,故也显得更为有趣与生动。
孩子的最爱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天地总是合二为一、不分彼此的。当天地相接时,便有了环境的整体,而小商小贩无不栖息于这个空间当中。因此,解读画卷中的小商小贩,不仅要看人物、看细节,更要以小商贩为中心,看周遭、看环境,看那个属于他们的天与地。
一旦这样,小贩的故事力将鲜活跃然纸上,其中的对话可能会有很多。首先,回应前文的“货郎老翁论”。货郎画得传神者,十之八九也擅长画孩童。换言之,货郎所到之处,孩童常常会出现。这便是所谓的“货郎图”中最为经典的天地场景了:货郎或向孩童兜售着商品,或与孩童嬉戏欢乐,或仅仅与孩童言语数句。孩童则可能百般撒娇,祈求玩具;可能逗得货郎哈哈大笑;又可能真的掏出铜板买东西。
再想想,如此场景在哪里见过呢?没错!这与其乐融融的家庭写照确有几分神似——慈祥的老者与嬉皮的小童,永远是中华文化语境中和谐温情的一幕。即便到了商业意味浓厚的《货郎图》中,仍旧如此。那几位调皮捣蛋的小童,恐怕正是让李嵩作品得以千古传世、让那位货郎成为大家心目中货郎“标准像”的文化背景吧。摇着货郎鼓的老翁,面带慈祥和蔼的微笑,似乎正在为周遭某一位小孩挑选商品,而前方的两位小童早已欢乐得连嘴都合不拢了,是父母给了几个铜板,让他们来买玩具吗?还是因为小孩看中了哪一款新货品呢?镜头来远点,不是还有一位小孩子正奔跑着过来吗?货郎仿佛有神奇的魔力,所到之处,不管是一个村口,还是某个巷尾,货郎鼓的“乒乓声”总能将小孩子接二连三地吸引过来。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那真的是商贩与买者的关系吗?怎么总觉得里面附着了一点温情,乃至亲情呢?在苏汉臣的《杂技戏孩图》中,我们也能够找到类似感受。尽管卖艺者算不算得上是小商贩,还存有争议,但借助这样一组情境说明问题,却是有力的。两位孩童眼睛渴望地看着卖艺者,一定是卖艺者刚才表演过什么精彩节目吧,才让两个小孩如此痴迷,卖艺者身上叮咚作响的表演器具,自然成为了孩子们不断“回头”的有力吸引。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货郎都如此热情。旧传为苏汉臣所作的另一幅《货郎图》中,便表现了略显不同的两位货郎,他们艰难地拉拽着小车,而孩童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不知道斜眼凝视的货郎到底在想些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恐怕对这群调皮捣蛋的孩童没有多少好感。他兴许只是兴匆匆地赶着路,苦苦寻觅着愿意买东西的顾客,而对这些嬉戏的孩子实在提不起兴趣,甚至观者可以想像,他的神情是否在述说着某种不悦与惆怅呢?
从个体的描绘到环境的营造,当小商贩遇见中国画时、当那个时代可能最卑微的小人物遭遇高雅艺术与文人情怀时,难免被浓墨重彩地渲染上了几分惟有文人骚客才有的人文情怀,尽管这无法确定,但在货郎与孩童这对关系中,不同表达手法的确带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思考与想像空间——那些货郎其实开心吗?真的如此喜爱与孩子嬉戏吗?
社会的点缀
如果说围绕货郎个体只是一个小环境,那么诸如《清明上河图》一类的卷轴,则为我们理解大环境提供了可能。不少读者一定有过疑惑,那些年,有“城管”吗?虽然在画卷上并不能找到确切线索。但历史文献告诉大家,宋代所谓的“街道司”便可理解为是“城管”。他们肩负着维护街道秩序和管理商贩等职能。在《唐律》中甚至还有“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的“违规处理条例”。由此可以大胆设想,《清明上河图》中人来人往、小贩如云的景象,确有几分“美化”之意。这可能是解读商贩与传统都市之间关系时,需要加以注意的环境细节。
在虹桥附近,如果稍微仔细观察,会发现桥面两侧挤满了各色小贩,或搭起帐篷,或架着竹栏,亦或者只是依靠着竹篓席地而坐,美味佳肴、农具刀剪、日用百货都成为小商贩们的销售对象。熙熙攘攘的画面,极容易令人联想起吵杂的吆喝声与叫卖声,仿佛观者即将步入虹桥,看身边两侧各色商贩的点点滴滴。这便非常好地呈现了大环境的空间效果,小商与小贩之间的竞争对话,顾客与小贩之间的攀谈议价,小贩与虹桥、汴河与道路的关系,如此种种,都因为图卷而变得可观可感,虽然需要来点想像力,为人物配上旁白,但画面感已经为我们洞察诸多商贩如何生存于一个社会环境创造了再好不过的范本。
但如果展开清院本《清明上河图》,虹桥一段却是截然不同的天地景象。桥面两侧竟然是连栋成排、整齐划一的“商铺”。商铺有的井井有条,有的略显杂乱,但总体感觉是原本吵杂喧闹的传统都会,似乎在无形中被清代宫廷画师们“现代化”处置了,原本乡土气息浓厚的热闹劲儿似乎变得有点萧条,乍看下去甚至有点“民俗村”的味道。
这样的画面让人容易联想到曾经在圆明园发生的故事。那时候,清帝专门在园内兴建了一条市井街,里面不乏吆喝的小贩、热情的商家,甚至小偷和卖艺者都一应俱全,当然他们都是宫女太监饰演的。皇帝则通过这样的虚拟场景,体验着畅游民间的快感,想像着民间小商小贩如何做买卖……故此不难理解,以规制协调著称的清宫画师能将喧闹的街市变得如此条理整洁。
但如果从文化和商业角度分析,事情就变得意趣盎然了。习惯于满街叫卖的宋代小商贩,到了清代居然如此“老实乖巧”?查阅史书会发现,一方面,用当下时髦的话说,这是“城市管理”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于,画家对于小贩的艺术处理,正在从个体走向整体粗线式的大写,这也是为何在明清以后,再难见到特写化的、以货郎为主题的人物风俗画的重要原因。
天、地、人是一组富有中国韵味的排列组合。个体的人总是神情丰富、动作细腻,故事力往往能够跳出画面。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则或为个体表达创造了舞台,或只是把镜头摇向了整体,在大场面上寻求精彩。
货郎,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在现实社会,抑或是绘画艺术中,显然都算不上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角色,但他可以被记住、足以被传世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比山水风月优秀多少、经典几多,而在于他的出现与存在为后世还原了老百姓的生活史、提供了从中国画中寻觅更多普罗大众气息的可能。大历史下的小人物,若能站在绘画的空间看,其实更精彩,难道不是吗?
从个体的描绘到环境的营造,当小商贩遇见中国画时、当那个时代可能最卑微的小人物遭遇高雅艺术与文人情怀时,难免被浓墨重彩地渲染上了几分惟有文人骚客才有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