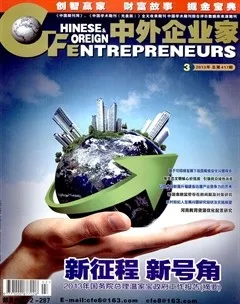论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缺失及其改革方向
2013-12-29唐丽宁
摘要:户籍制度将中国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对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流动作出严格限制。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户籍制度已大幅度松动,但仍然存在若干缺失之处。要真正实现宪法规定的迁徒自由,就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实行户籍制度的改革。
关键词:户籍制度;缺失;改革;方向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5-0251-02
一、引言
作为临时宪法文件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迁徙自由。1954年宪法起草的过程中,最初对于迁徙自由的问题并没有加以规定,但最后还是在宪法中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内容。如同其他的宪法条款一样,20世纪50年代,迁徙自由被虚化,并未真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一项实有权利。尤其是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实施之后,中国公民被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个部分,他们之间的前夕流通成为不可能;即使是在同类户口内部,人们也被固定于其所属的基层政权组织或单位,迁徙自由根本就不存在。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其他制度的变革,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二、现行户籍制度的缺失
公民权利领域的“法不禁止即自由”本应成为法治社会中牢不可破的根本原则之一。若根据这一原则,只要宪法没有对公民迁徙自由作出限制,那么它就应当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考诸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迁徙自由并未在宪法中被明确表述。因此,从法理上说,应当认为迁徙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然而,由于我国长期的人治传统,对法治原则中的这一关键内容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再加上很多普法材料中不恰当的灌输“权利由法律授予”的观念,在当代中国形成了一种奇怪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凡是宪法和法律中没有规定的权利,就不是公民的权利。基于这种观念,“我国公民在法律上没有迁徙自由”就成为一个普遍的误解。有的研究者在与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各种迁徙现象比较之后,还得出了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处于“法律上的无权与事实上的有权”相矛盾的状态。这一表述存在如下几方面的错误:首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阙如,不能成为否定迁徙自由的根据;其次,权利本就是一个规范概念,只要有权就是法律上的权利,不存在所谓“事实上的权利”。
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是公民迁徙自由成立的必要条件。但宪法和法律的明文规定必然有助于迁徙自由的保护;从相反的角度看,宪法和法律的不合理规定则又会对迁徙自由的保护形成阻碍甚至造成伤害。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户籍制度是与迁徙自由有着密切关系的一项制度。很遗憾的是,户籍制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成为迁徙自由的障碍,为了管理的方便以及社会的变态稳定,迁徙自由自始就成为户籍制度的牺牲品。直至今日,尽管户籍制度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修改或在不再具有实效,但中国的户籍管制仍然位列迁徙自由最大的障碍之一。
有的研究者认为,现行户籍制度在诸多方面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阻碍作用。具体而言包括:一是限制了人的基本自由,阻碍了民族独立、自治品格的形成。迁徙自由是人的自由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在许多时候要靠迁徙自由才能实现。二是形成、确认并保护了公民身份的不平等。平等和自由都是重要的人权,人们所追求的平等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种现实。三是严重影响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四是分割城乡,阻碍了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即国家的整合。
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在近三十年来一直在或缓慢或快速的发生着变化。在最初建立时,户籍制度的确对中国公民的迁徙自由作出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在这种限制之下,除非得到特定国家机关的批准并符合某些实体条件,否则决不允许在不同地域之间进行流动。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政治控制的放松以及经济体制的变革,户籍制度对迁徙自由的限制程度也就不再如以往那么严格了。时至今日,除非依据法律被限制人身自由,人们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当然,这种不受限制的自由是仅就“迁徙”这一“行为”而言的,至于迁徙之结果,则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不平等:首先,在就业方面,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之后,在就业方面受到诸多限制,有些城市就规定特定的行业不能雇佣农村居民。其次,在教育方面,农村居民无法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优质教育资源不能在进城农民和城市市民之间进行平等的分配。更为不合理的是,僵化的教育管理体制还不时的干扰、限制乃至消灭农民工自办的“子弟学校”。再次,在社会保障方面,进城农民不能和城市市民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某些福利项目只能由城市市民享有。除了这三个方面之外,在其他的诸多方面,进城农民都无法与城市市民享受平等的待遇。当然,这种不平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一方面,有人认为不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因此在中国的所有领土上,公民都应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担同等的义务,并获得法律和政府的平等对待。公民在不同地区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事实说明宪法上规定的平等权并未得到认真对待。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平等和区别对待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须臾不可分离。所谓宪法上的平等,并不是说所有公民在所有领域都受到同等对待。而是说符合相同条件的公民在相同的范围内享受同等的对待。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并未对城市的建立和发展作出同等贡献,因此,在不同领域享受不同待遇本就是合理的。它更符合平等原则的实质:同样情况同样对待。试想,如果为城市纳税三十年的城市原住居民和刚进入城市,纳税不超过一年的新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那么对于城市原住居民也是不平等的。
尽管对这种不平等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从结果上来说,它的确影响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对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比如在某些一线城市,对外来人口的迁入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制。如此一来,本市企业如果要招聘一名非常适合自己单位外地员工,为了解决其户口,就要付m十分昂贵的额外成本;如果企业不愿意付出这个成本,那么该员工或许考虑到作为一名“外地人”在该城市所可能遇到的生活网扰,或许就不再考虑到该企业工作。如此一来,本来对企业和员工都有利的一次雇佣行为,却因为户籍壁垒的存在而宣告失败。这就是户籍壁垒影响人力资源配置的典型情况。时至今日,这种壁垒仍然存在,相应的,对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影响也依然存在。至于对中国统一市场秩序之构建,户籍制度的阻碍作用可谓相当明显,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前文所述的对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影响。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
户籍制度对公民“迁徙行为”的自由之限制已近于不存在。只要个人有意愿并且经济能力允许,即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目的地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前往该目的地。所以,当代户籍制度之改革重点自然就不应仍然囿于传统论述而强调对“迁徙自由权”的所谓宪法确认或法律确认。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否给予这种确认已经不影响公民迁徙行为之自由。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某些城市在特殊时期——比如大型运动会或展览会期间——仍然会给予户籍的区别决定是否采取特殊措施。这种对迁徙自由的限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借用了户籍制度这一区分标准,但其实质上并不是户籍制度在作祟,而是一种公权力的滥用。即使没有户籍制度的存在,这种权力滥用仍然会找出其他的标准为借口。所以,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户籍制度是否被改革或废除,而在于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行政程序和救济程序,从而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控制。
在农民进城这个问题上,当代户籍制度亟须解决的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在微观方面,它要实现进城农民和城市市民之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在平等原则的规范下取消对进城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其次,在宏观方面,它要实现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统一市场的形成,进而为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建设奠定基础。
首先,确认迁徙自由的宪法地位。从法理上而言,公民迁徙自由的存在并不以宪法是否规定为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迁徙自由入宪就没有意义。迁徙自由入宪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确认公民拥有迁徙自由,而是限制法律及其下位规范性文件对迁徙自由的克减。为达成此目的,进入宪法的迁徙自由条款并不需要详细规定迁徙自由的内容,而是应当将重点放在对立法机关的限制之上。应当明确规定法律可以限制迁徙自由的条件,限制的程度,不当限制的法律后果等。
其次,以宪法规定为基础,实现对户籍制度的重新整理。户籍的意义仅仅是登记一个人的居住信息,它仅仅具有公示效果。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享受某些权利的依据,但它绝不应成为将公民固定在某个地区并禁止其迁徙的根据。由此,就必须实现户籍制度立法目的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向。诚如王鹰所言,要实现迁徙自由的非治安化(王鹰认为,所谓非治安化就是不把迁徙自由和户政管理狭隘地作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治安问题实施国家警察行政管理。在指导思想上须特别强调,迁徙自由涉及国家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公民的迁徙自由是实行市场经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确立并实现迁徙自由是中国完成一体化进而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重要的制度性安排。以确立迁徙自由权为核心的户政管理改革是迫切的,而传统的变革和社会的转型又是渐进的)。
再次,必须消除现行户籍制度已经造成的不合理现象。其重点在于实现进城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平等。当然,这种平等是建立在合理分类基础上的,并不是要实现二者之间完全的均等。对于某些由本市居民负担支出的公共福利项目,进城农民不能享有也是正常的。这个问题不是某个特定城市可以解决的,它需要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做到全国范围内福利项目的自由转移支付,那么进城农民就可以在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在任何城市享受基本的福利项目。即使如此,仍然可能存在一些特殊的福利项目,外地人是不能享有的,这些项目产生于该城市的特殊性,其他的城市或农村没有这种特殊性,也就没有这种福利项目。以江苏省苏州市为例,苏州园林全国文明,门票价格向来不菲。但苏州市民以及持有暂住证的外地居民可以凭证件办理优惠卡,以极低的价格多次游览苏州园林。这种福利项目就是基于苏州市的特殊情况而产生的,因此也无法向外地居民推广。
最后,放宽入籍限制。应当允许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自由选择加入任何城市的户籍,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不仅限于城市居民,亦应包括农民。如果能够实现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自由转换,那么所谓的城乡差别也就不会存在。人力资源也可以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城乡之间的经济壁垒也自然就可以打破。城市企业在招聘时,也就不会仅仅因为户籍的限制而放弃自己中意的应聘者。如此一来,统一的人力市场就可以建立起来(早在2001年,全国人大代表吴明辉就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建议尽快研究、制定适合在祖国大陆地区实施的《户籍法》,并建议《户籍法》应该包括以下内容:公民拥有依法迁徙入籍的自由;取得入籍居住资格的基本条件是,在拟人籍地有稳定的住所、或有稳定的工作、或有直系亲属、监护人承担赡养、抚养、监护的义务;取得某地户籍后,公民平等地享有租(购)住宅、求职、工作、受教育、婚姻生育、参与公共政治社会生活、休憩等权利。全国各类地区不再设立类似红印、蓝印之类的差别性户籍。认为这样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发展;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各类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发展。参见《江淮晨报》2001年3月9日。。
(责任编辑: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