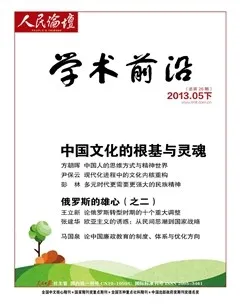多元时代需要更强大的民族精神
2013-12-29彭林
摘要 民族的复兴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领,需要找回本位文化的价值,在两千多年中国文明的长河中,礼起到了最为核心的作用,对政治、文化、经济、风俗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不及于礼乐文明。通过对历史与人文的溯源考察,揭示以礼乐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从学理上阐释古代中国何以走上礼乐治国的道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礼 乐 中国文化 传统 多元文化
周公制礼作乐:历史性的伟大选择
我们先回顾中华文明从远古到上古时代的基本进程。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开始出现。中国人在北方的农业区最早成功栽种了小米,在南方的水田农业区最早培育成功了大米。经过数千年的交流与互补,到距今4000年左右,融汇为灿烂的夏代青铜文明。从夏朝到商朝的一千年中,中国依然是农业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谋求粮食等物质生活资料。到商代末期,社会物质生活已相当富足,青铜文明臻于极盛。至此,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此后只有量变,再无质变。
但是,商代富裕的物质生活失去了理性精神的引领,贵族们酒池肉林,骄奢淫逸,滑入了腐败的深渊。其深层的原因是,殷人政治文化的特点是迷信鬼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以为只要殷勤祭祀,祭品丰厚,就能得到天佑神助,任何人奈何不得。纣王在覆灭的前夜,依然笃信“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牧野之战,殷商王朝一朝覆灭,作为西周新政权主要设计者的周公,不能不受到巨大震动,“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殷”(《尚书·召诰》),必需吸取它们的前车之鉴,方能求得长治久安。
周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把商朝的国家机器当作一份巨额资产来接管,按既有的治国模式运作,“以暴易暴”,以新的暴政替代旧的暴政;二是吸取商亡的教训,革除旧弊,提出新的治国理念与模式。周公选择了后者。从《尚书》收录的周公的诸多训诫看,周公新政的主要理念如下:
民本。民众是立国之本,不可轻忽。武王在率师渡孟津时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上天是尊重民意的,民众要想做到的事,上天必定会顺从。周公要求执政者体恤小民“稼穑之艰难”,要保惠庶民,不可欺侮,他引古语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要把小民的感受作为反观自己为政得失的镜鉴。中国民本主义思潮由此而起,并迅速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意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这种思想在古希腊的产生和流传,比中国至少晚了五六个世纪。
明德。在《尚书》中,周公反复提及“明德”,意思是昌明执政者个人的德性与治国理民的德政。周公“勤用明德”(《梓材》),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他说,“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陈》),至德之治发出的馨香可以上感神明,供桌上的黍稷不香,光明的德性才有真香。纣王不明其德,所以为上天所灭;周文王有明德,所以才为上天所立。能否长治久安,不在天命,而在我之德,“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太甲》)。《诗·大雅·文王》说“自求多福”,要把命运寄托在自己身上,周人高度的道德觉醒,由此可见。
勤政。《尚书》中的《无逸》一篇,周公以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周文王等四位“迪哲”为例,向成王阐述勤政之道。周公说,殷代统治者并非一开始就昏庸无道,恰恰相反,中宗、高宗、祖甲都懂得“治民祗懼,不敢荒宁”的道理,治民都有敬畏之心,政事无大小,都能恭敬从事,不敢荒淫,因而都能长久地享有国祚: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而祖甲以下的殷王,“惟耽乐之从”,所以,“罔或克寿”,都是短命的君王,在位超不过十年。周文王也是成天忙于政务,达到“不遑暇食”的地步,故在位五十年。所以勤政与否,事关国运的兴衰与国祚的长短。
禁酒。《尚书》的《酒诰》篇,可以视为周公的“禁酒令”。周公之弟康叔受封于殷商旧地卫国,当地民众久受纣王影响,嗜酒成风。周公告诫康叔,纣王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酗酒,“腥闻在上”,使得上天都闻到了他们的酒腥;为此他要求康叔“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许沉湎于酒,不仅不敢,而且没有这种闲暇。只有祭祀时可以少量饮酒,但不能醉。对酒醉误事者要杀无赦。
克商之后不久,周武王即去世,当时天下未安,成王年幼,不能亲政。周公受命于危难之际,摄政当国,“一年救乱,二年伐商,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归政成王”(《尚书大传》)。周公平定天下之后,乃归政于成王,自己退隐,为防止人去政息,周公制定了体现道德理性原则的礼乐制度,史称“制礼作乐”。
殷周鼎革之际,周公用理性的方式完成政权更迭,制定了以礼乐为纲纪的典章法则,使道德成为治国理民的强大基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抉择。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鉴于纣王失德亡国的教训,周人“深知夫一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殷周制度论》)真是不刊之论!
周公之后,经过孔子、孟子的推阐与弘扬,以道德立身、立国,主张“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相信道德的力量,恪守正义的信念,“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这一思想原则成为中国人的文化信仰,造就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礼乐文明是周代社会的纲纪
周公制礼作乐,深入人心,影响极为深远。春秋末年,王纲解纽,天下大乱,但是,读《左传》可知,政治精英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周公制作的“先君之礼”与“古之制”,他们将礼视为与“天经”、“地义”等同的概念,是经邦治国、安身立命的大经大法,如: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左传·文公十五年》)
礼以顺时。(《左传·成公十六年》)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
礼,政之舆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礼,身之干也。(《左传·成公十三年》)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
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礼是依道德理性要求制定之法则,其价值在于将原本属于抽象范畴与概念的道德理性,转换为视而可识、触之可及的社会现实,使社会纲纪真正树立。礼,即理;非礼,即非理。两者为表里,几乎通用不别。
孔子与其后的七十子之徒将礼与人格的确立相联系,礼被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是修身厚德的基础。道德仁义再好,不借由礼的践行,则终究为虚言浮词。自孔子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孔门弟子相继阐发,以礼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如: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
孟子把“仁义礼智”四端作为人性本善的理由,礼居其一,无礼者谓之非人。诗礼传家,以礼为修身之宝,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理念,世世传承。
读历代史书,以礼为治国纲纪的思想可谓贯穿始终。欧阳修《新唐书》的《礼志》,比较“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之治的得失,断然将礼治作为最重要的判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卷第一句话就是“天子之职,莫重于礼”,全书以礼为准绳,评论为政得失。其后的顾炎武,曾国藩,梁启超等也无不如此。
钱穆说:“梁任公以中国重礼治与西方重法治相对,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中国知识分子》)钱先生论礼之说极多,限于篇幅,不再赘引。
礼贯穿于中国文化的五个层面
中国文化中的“礼”,并非仅指礼貌、礼节,或者仪式、礼仪,它的内容涵盖一切,在西方语言中没有对等的词汇可以翻译,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相当。这是中国之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特殊现象现象。大较而言,“礼”自上至下包括五大方面:
政治理想。大凡一位政治家,或者一个政党,为给社会指明终极的发展目标,都会描绘理想社会的蓝图,柏拉图的《理想国》即其例。这类文献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属于政治学范畴。中国不然,在中国它属于“礼”的范畴。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其最高表述乃是《礼记·礼运》篇。孔子阐述的大同世界的学说,直到近代依然不衰,成为鼓舞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孙中山生平题词最多的,乃是“天下为公”四字,但凡有孙中山故居、遗迹之处,几乎都可见到。
天人关系。天地化生万物,人仰赖万物而存。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还是自然界的一员?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万物为前提,还是应该与万物共存共荣?这类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属于礼的范畴。《礼记》有《月令》篇,记一年十二个月每月的天象、物候与当行之令等。其中,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禽兽生存的措施,是重要内容之一。如春天不可伐幼树、不得掏鸟窝、不得捕杀怀孕的母兽,等等。这些表达中国人理性处理天人关系的理念,都是以礼的形式被规定下来,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则。
官民关系。如何处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在西方也属于政治学的基本课题,中国则同样属于礼的范围。儒家反对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治民之道,主张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民之道。儒家经典《周礼》一书全面展开这一理念,官政、吏治、民政、教育、市场、税收、军政、司法、营造,等等,上至官府的管理,下至民众的生计与教化,无一可以逸出于“礼”之外。
人际关系。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人只有结成群体,方能战胜严酷的自然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但人人都有自身的利益,若人人争利,则彼此残杀即随之而起。儒家提倡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人们彼此尊重、互相谦让,为此而制定了一整套交际的礼仪规范,人人遵行,则社会和谐。
修身养心。从身与心两大方面不断砥砺、切磋、琢磨,成为内外兼修、身心俱佳的君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大写的人,甚至成圣成贤,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目标。《礼记》说“致礼以治躬”,躬就是身,学习与履行“礼”的规范,可以使人的行为举止温文尔雅,彬彬然有君子之风;“致乐以治心”,心是一身之主,常听德音雅乐,润物细无声,可以引导人心走向和顺的境界。礼乐相将,则人人可成为君子。
礼的范围如此广大,所以钱穆先生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须礼。礼之和合范围大,故中国人极重礼。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又说,“中国政治是一个礼治主义的。倘使我们说西方政治是法治主义,最高是法律,那么中国政治最高是‘礼’,中国传统政治理想是礼治。”(《中国史学名著》)
礼乐文明的学理
在《礼记·经解》中,孔子提及用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教化民众的理念,其中说到礼教与乐教。礼与乐为何可以教民,这是一个有着很深理论底蕴,也非常高妙的治国理念。
大凡一位思想家或政治家在推出自己的学说时,总要寻找人类在心理或生理方面的共同特征。这一特征寻找得越是正确,则其学说越具有普世价值,越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儒家认为,万物“莫不有道”。 “[不]由其道,虽尧求之弗得也”(《郭店楚墓竹简·六德》)。
儒家认为,人类最大的共同点,是具有相同的人性,“四海之内,其性一也”。(《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无论地位高下、家庭贫富,人性皆同,荀子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人性来自生命,生命来自天,《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中庸》将两句合并为一句:“天命之谓性”,意思一样,都是说人性与生俱来,不学而有,不教而能,谁都无法排斥,只能因势利导,因而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治理民众,必须从承认并且尊重人性这一前提出发,所以《中庸》说“率性之谓道”,遵循常人之性去治民,则庶几近于道。
“性”深藏于人的体内,一旦受到外物的刺激,便会外露为“喜怒哀乐”,转化为尽人皆知的“情”。人是一种情感极为丰富的动物,人每天从早到晚,甚至终其一生,都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人非圣贤,自己的情绪很难自发地达到处处“中正”的境地,或大喜大悲,或狂躁暴怒,或消极颓废,总之,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如果情绪把握不好,轻则言行失当,重则引发恶性事件。治国的基础是治民,治民的要谛是在身与心两方面,在身而言,则是言谈举止是否有教养;在心而言,则是内在心态是否平和安顺。就个人修身而言,也不外乎这两者。因此,无论从政府治民的角度,还是从自我的修为而言,都是要求人人向身心双修(或者说内外兼修)的方向努力。而礼乐,正是为消除这两方面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
礼缘情而作,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制作的行为规范,“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礼生于情”(《郭店楚简·语丛二》),《中庸》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一,大旨是在喜怒哀乐“未发”与“已发”之间立意,教导人们喜怒哀乐之情要得到理性的制约,要“发而皆中节”,要正确拿捏住自己的情感。
举例来说,父母亲逝世,子女内心的悲伤势必会表现在情感上,但程度不等,有两种极端的表现:一种是毫不伤心,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照样饮酒吃肉,歌舞娱乐;另一种是过度悲伤,不吃不喝,捶胸顿足,嚎啕痛哭,结果丧事尚未办完,自己就已去世。前者不孝,愧为人子,理当谴责;但后者亦未必就是,子女不能理性控制自己的情感,“以死伤生”,因为死者而伤害生者,这是死者所不希望看到的。前者属于悲情不足,后者则是悲情太过,过犹不及,都不符合礼的要求。为此,丧礼作了许多理性的措施,例如亲人刚去世的三天,子女悲痛欲绝,不吃不喝,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此后再不吃,就有性命之虞,所以丧礼规定,此时邻居一定要强迫孝子喝粥,为了家庭的未来,一定要节哀顺变;又如子女孝心不足,亲死不痛,也有解决之道。丧礼规定,亲人死,孝子要居住在简陋的倚庐(丧棚)中,身穿丧服,不得茹荤饮酒,意在时刻提示子女:自己正在丧期之中!父母生前百般慈爱,此时不应无情无义。以此把他们内心的亲情提升到应有的高度。这些安排的深意在于,降低贤者过度的哀情,提升不孝之子低陷的亲情,使两者都能及于“中“的境地,正如《礼记·丧服四制》所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
人在生活中,每天要与父母、师长、上司、配偶、朋友等不同身份的人交往,人们不应该用对待父母的方式去对待朋友,也不可以用对待朋友的方式去对待尊长,既不能太谄媚,也不能太随便,要把分寸拿捏好。要做到既得体又典雅,就需要通过礼来学习与体会,习之既久,则君子风范宛然而生。
通过礼来规范自身言行,并非困难之事,难点是在对心的涵养与调适。心为一身之主,心不正,外面做的再好,也只是假象,没有实际意义。端正内心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通过读书明理,懂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的道理,使心归于中正;二是听德音雅乐,使心灵净化和谐。音乐生于人心。心为外物所感,就会发出感叹之声;如果觉得这样表达还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情感,就会歌咏;如果觉得这样还不足,就会手舞足蹈。人心相同,所以音乐打动人心,最快、最深、最有力,所以儒家十分重视音乐,将它用于教化。
《乐记》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记述儒家音乐理论的专著,内涵极其丰富,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将后世所谓的“音乐”划分成声、音、乐三个层次:“声”,是其中最低的层次,没有旋律、没有审美情趣,是人类生物本能的表现,但凡是有听觉器官的,不管是人还是禽兽,都能感知。“音”,是经过文饰的情感之声,它往往与歌者的言,嗟叹、咏歌、手舞、足蹈等言语、体态相配合,成为一种复杂的表达体系。《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行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但是,音有好有坏,良莠不齐。如靡靡之音,足以让人萎靡不振,沉溺不起,是亡国之音。宣扬暴力的音,则会让人疯狂,于人于国都不利。因此,对“音”要进行汰选,只有那些主题健康中正、节奏庄重舒缓、风格典雅平和、富于道德内涵的音,才配称之为“乐”,所以《乐记》说“德音之谓乐”。乐是音的最高层次,《乐记》说:“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唯有君子真正懂得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吕氏春秋·大乐》)郭店楚简《语丛三》提出一个命题:“乐,服德者之所乐也。”《五行》也说:“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玉振之。”将乐与德相提并论,认为乐是有德者之乐。乐能够从根本上左右民众的心志的走向,润物细无声,于悄然之中淳化民性。因此《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礼乐教化,可以使人从根本上向善,内外皆化,德性充盈,所以《郭店竹简·尊德义》说:“乐,内也。礼,外也。礼乐,共也。”“德者且莫大乎礼乐。”
多元文化与礼乐教化
近些年来,“多元文化”成为最流行的词语。不少人认为,一国之内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本位文化只是多元选择之一。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所谓“多元文化”,有如下两层意思:
从世界文明的总体结构而言,人类文明是多元文明。由于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不同,故各国文化无不具有区域特点。历史上形成的阿拉伯民族、印第安民族、亚洲民族、欧洲民族、非洲民族,彼此之间的差异,除了体质、肤色和生存环境之外,主要是文化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各种异质文明犹如百花园里的花朵,异纷呈彩,相互映衬。不同质的文化,各有千秋,互有优长,正是由于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明呈现出多姿多彩、缤纷灿烂的气象。
20世纪60年代重提“多元文明”的本意,恰恰是要尊重并保护各国的本位文化。某些西方大国在推行军事霸权主义、经济霸权主义的同时,妄图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试图用他们的文化来统一全球的文化。 他们在“经济全球化”的旗号下,利用高科技手段和强势媒体,大力冲击世界各国的异质文化。不少经济落后的弱势民族无力抵挡势,他们的话语权越来越少,他们的历史正在被遗忘,他们的文化也越来越边缘化。经济全球化有可能带来文化全球化,从而导致某些文明的消亡。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称:“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不少经济欠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已经沦落为美国的附庸,彻底丧失了自我,这是非常危险的前景。
最早意识到这种危险的是法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电影市场的60%被美国所占据,某些西欧国家这一比例高达80%~90%。这一态势犹如“铁罐”撞击“陶罐”,西欧本土电影溃不成军,市场所剩无几。法国人历来以法兰西文化的伟大和优秀而自豪,如今不仅本国电影严重萎缩,而且国民的价值观也随着美国电影的进入而悄然改变,长此以往,后果堪虞。在美法两国关于关贸总协定的开放服务市场的谈判中,美国强调文化产品与其它商品应该等同对待,而法国则极力加以反对,认为文化产品虽然有商品的属性,但同时又有精神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内涵,因此,文化不是普通商品,它不能从属于商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法国人同仇敌忾,把文化的单一化和文化产品的标准化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敌人来加以反对,提出了“捍卫文化的多样性”的口号,积极抵捍卫本土文化,认为无论哪种文化都应该被保留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尊重其它文化,是人类伦理的核心支柱之一”,其含义是尊重文化最根本的异质性,尊重身份特征的差异。
法国的主张得到世界各国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指出:“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他们与外国文化并驾齐驱。”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联合提议,就文化多样性起草一个国际公约,得到了60多个会员国的支持。可见,“多元文化”的提出,是各国希冀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为自己的本位文化寻求一席之地,在国际交往中保有自己文化身份。细想,当今的大国参与国际交往的程度都不输于我们,但他们哪国不是极力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
反观近年国内出现的所谓“多元文化”思潮,恰恰违背了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初衷。他们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用美国文化取代我们的本位文化,把中华文化接到美国文化的轨道上。这种在文化上自我殖民的做法不仅理论上不同,在实践上则是极其有害。
世界政治,只有多元格局才是最稳定的。世界经济的格局也是如此,欧盟、东盟等之类的区域性的经济共同体越来越多,正是为保护自身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应对之策。单极的世界经济体系,只能造成一霸独大,无法导向世界的和谐与发展。
我们不能用抬高某种文化、排斥其它文化的办法来发展本位文化。好比黄梅戏与越剧,属于不同的戏种,没有优劣之分,它们的共存,有利于促进戏曲的繁荣。如果硬要用某一个戏种去统一其它所有的戏种,戏剧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因此,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处,有利于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和整体提升。各民族人民在创造自己独特的本位文化的同时,也是在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就是这个道理。
百年以来,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礼乐文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一个时期内,“礼教吃人”和“克己复礼”就是复辟万恶的奴隶制”曾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人人谈“礼”色变,以“礼”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已无礼可言,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人提倡西方礼仪,甚至提出要将西方商务礼仪当为中小学生应知应会的民族礼仪加以推广。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将从根本上发生变异。
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本位文化的根。1914年,梁启超在与清华学生座谈时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严复先生曾经提出国民的“国性”问题。“国性”即民族的文化个性,是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积淀起来的,是一国、一种族赖以凝聚的内核,它的理论形态载在民族经典之中。早期的清华,派出国的多是年纪尚小的中学生,校长曹云祥认为,学生年幼即出国,最大的问题是“不谙国情,且易丧失国性”。
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是人类在21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民族的复兴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领,需要找回本位文化的价值,因此,文化的复兴是第一位的。在两千多年古代中国文明的长河中,礼起到了最为核心的作用,对政治、文化、经济、风俗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不及于礼乐文明,它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理应从中吸收有益的养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然需要借鉴世界一切民族的文化财富,就更没有理由拒绝本国的宝贵财富。《庄子·逍遥游》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则膠,水浅而舟大也。”在坳堂之上倒一杯水,就只能浮起几根芥草,放个杯子就搁浅了,原因是“水浅而舟大”,中华民族是一艘即将扬帆远航的巨轮,只有五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才能承载起它。
没有强大的本位文化,而只有七拼八凑的“多元文化”的民族,只能是一盘散沙,是失去了文化身份的民族,无论其经济一时有多发达,终将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责 编∕凌肖汉
A Stronger National Spirit Is Needed in an Era of Diversity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Rites and Music
Peng Lin
Abstract: The revival of a nation needs to be guided by its national spirit, with the value of its specific culture re-identified. Over the more than 2000 years o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rites have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producing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politics, culture, economy and customs. When studying Chinese culture, one must get involved in the civilization of rites and music. It is certain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vestigate the origins of history and human culture, reveal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at takes the rites and music as its core, and academically interpret how ancient China went on the road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with rites and music.
Keywords: Rites, music,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s, diverse cultures
【作者简介】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研究方向:先秦史、历史文献学、经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等。
主要著作:《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