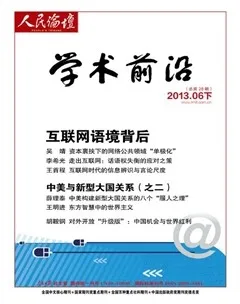“公共空间”内外和“时间节点”前后
2013-12-29王首程
【作者简介】
王首程,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络通信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电视传播、媒介经营管理、舆情研究。
主要著作:《会议管理》、《文学欣赏》等。
摘要 网络言论信息传播如果不妥善管理,对社会和他人都会造成伤害。这就要求管理者区分新旧场景,以减少场景混淆带给他人的伤害,并同时防止夸大网络言论的现实伤害;区分混沌前后的时间节点,在保持法律威摄的同时,保护言论自由,最大限度发挥网络的功能;区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严管公共空间,宽管圈子空间,保护私人空间,营造宽严有序的交流场域。这样才能让社会大众更放心、安全地享受网络时代的信息资源。
关键词 场域性质 时间节点 公共空间 私人空间 网络信息
互联网上一天的信息量足以刻满1.68亿张DVD。庞大的信息流中蕴含着人类的知识、智慧、经验,是用户宝贵的学习资源。但是,其中也有些谣言信息以及侵犯他人名誉、泄露个人或组织隐私的内容,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了伤害。
面对当前我国网络言论信息传播的现状,有人抱怨管理不严,法律惩戒力度不够;也有人不满微博实名,批评网络删帖侵害了言论自由。用户每天都在增加,批评每天都在继续,我们对于互联网管理的认识和对策,也到了亟需出新的时候。
区分新旧场景,以减少场景混淆带给他人的伤害,并同时防止夸大网络言论的现实伤害
网上的“乱象”和电子媒介营造的新场景密切相关。场景变了,人们在新场景中的行为也要随之变化,如果不变,错乱就难以避免。1985年,美国传播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在埃尔文·戈夫曼的拟剧论和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媒介情境论的理论框架(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埃尔文·戈夫曼的“拟剧论”把社会描述成一出戏剧,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人们会作出不同的行为。例如,一名警官在上班期间严格执法,下班以后则可能喝得烂醉如泥。本来喝酒是他的私事,公众可以关注他的公职行为而不应该苛求他的私生活作风。但是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各种不同的场景混淆在了一起,现在一名醉酒的警官形象可能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进而引发社会对警察作风的抨击。①
在此首先想讨论的是,是否应该曝光那位喝酒的警官,媒体的行为对那位警官是否公平?现在的情形是,舆论往往只关注警官喝醉酒是不是事实,却很少去顾及警察下班之后在自己的私人空间的权利以及他的私生活应该享有的保护。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梅罗维茨当年所说的电子媒介主要是指电视,几乎没有涉及到网络。在网络媒介日益成为最为普及的受众终端的今天,有必要对梅罗维茨的研究作一个延伸——如果今天依然不能阻止那名醉酒的警官形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那么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再来作个推测:一位知名人士骂人和被骂,如果是发生在电子媒体出现之前的旧场景中,首先报刊媒体不会让他们的粗话曝光,谩骂和争执只能在俩人或一群人中间进行。最有可能的结果是被他人劝开,也不排除俩人经过一番交流后化解矛盾成了朋友,很少有机会演变成公共事件。而现在,生活中的人物没变,生活的内容没变,生活的情节却被网络媒介营造的新场景混淆了。结果,人们在旧场景中的私密行为,今天都有可能进入新场景,成为网络直播的内容。此时再读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不同感官的延伸”等著名论断,或能有顿悟般的认同。遗憾的是,麦氏没有告诉人们应该如何避开那双“延伸”的眼睛和“延伸”的肢体,以保护个体的空间不受侵犯,这成了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了提醒人们“避开”,必须要让每一位用户清楚:网络媒体在今天已经引起人的感官变化,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意识和行为。这样的情形比梅洛维茨所强调的“电子媒介让人们从旧场景迈入了新场景,人们的行为也随着场景的改变而改变”要明显得多。梅洛维茨所处的时代,媒体是点状分布的,是不联网的单机,今天的网络数字媒体是持续传播的信息网链,是全国、全球联网的系统,对行为的放大能力无法控制,导致的后果甚至无法估量。
为了避免侵害他人,也为了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以及个体生活原有的乐趣,每个人都需要完成新旧场景行为定位的转换——调整那些不适合在今天的新场景中呈现的行为。每一位传播者都必须清楚混淆场景可能带来的后果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完成这样的转变最可靠的力量是通过教育的努力使个体获得自觉,而不是滥用外来的强制力。
其次,在新场景中,我们对网络言论导致的现实伤害的评价也需要建立新的指标。如果沿用旧的经验,不仅容易降低媒介技术带给我们的快乐,还有可能夸大网络不当言论的现实伤害。
笔者在一项关于微博评论的个案研究中发现,微博评论中的一些观点是评论者基于此前的记忆而非当前的事实形成的。网民对公众人物一般只有单一的社会角色记忆,而没有生活中的形象记忆,因而对社会公众人物的认识是不完整的。当发现某位官员周末出现在海滨浴场时,网民便可能由于所见和自己所有的记忆反差过大,把眼前的景物当作爆炸性新闻通过微博、论坛加以传播。教育努力追求的目标首先就是让传播者意识到他并非是在监督公权力的运行,而可能是在侵害私人空间的权利;教育努力的另一个目标是让社会受众懂得“爆炸性新闻”的发布者有可能会混淆场景,因此需要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对其发布的内容进行辨别和求证,而不是即刻被“爆炸性新闻”所点燃。
通过观察发现,微博发布量最大的时间段是晚上8点到11点,这也是舆情最容易发酵的时段。此时传播者的话语表达已经离开了办公室规范化的交流场景,进入了私密化的个性场景。在个性场景中发言,感性大于客观,随意多过理性。据此又可推断,微博中的评论跟帖并非就是网民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理性表达,相反,多数评论内容不仅有情绪化倾向,而且有调侃、娱乐以及率性、随意的特征。即便是那些嘲讽性的尖刻表达,也带有一定的娱乐成分。
用娱乐的话语形式表达严肃的社会性话题内容,也是场景的混淆现象,和人的娱乐本性在微博空间得到了发掘和张扬有关,也应该和微博评论的即时性(发言者理性思考的时间不足)以及微博的文本长度特征有一定的关系。
认识上述混淆场景现象,认识微博对人的娱乐本性的发掘意义,认识微博话语形式对思想表达的制约,对准确判断微博评论中的言论,尤其是一些“尖刻”言论的真实语义,具有重要的提示意义。如果网络言论管理法规缺乏上述认识的支持,则有可能导致所出台的管理措施压制言论自由,加大心理焦虑以及人际关系的紧张程度,甚至会对社会发展的主流形成误判。
区分混沌前后的时间节点,在保持法律威慑的同时,保护言论自由,最大限度发挥网络的功能
有这样一个常见的现象:一些此前被视为网络谣言的消息却在不久以后成为被证实的事件。这使得网络言论伤害的法律约束常常陷入困境。笔者认为区分混沌期前后的时间节点,有助于摆脱上述困境。具体有三层意思:
一是在真相不明、事实不清楚的信息“混沌”期,在保持法律威慑的同时,对网络言论的责任主体应予警示为主,而不轻易处罚。譬如,2011年3月15日,有谣言称日本核辐射会污染海水导致此后生产的盐无法食用,且吃含碘的食盐能够帮助人们预防辐射,我国部分地区的市场上由此出现了食盐抢购潮。该事件于3月16日晚先从浙江、江苏、福建、上海、广东等省市传开,之后蔓延到重庆、成都。随后,国家发改委发出紧急通知,中国盐业总公司发布消息告知国内食盐储备充足无需抢购囤积;北京市疾控中心重申我国环境空气未受到日本核泄漏污染,居民不需要补碘;有关专家也出面解释我国井盐、湖盐充足,即使没有海盐也不会出现食用盐短缺……事实逐渐由“混沌”转为清晰。在“混沌”转为清晰之前,对由于恐慌而听信了谣言或在求证过程中加上了自己的“合理推论”传播了谣言的,一般情况下应以批评、警示为主。
二是在涉及公共利害的突发事件中,责任主体理应及时公开真相。如遇责任主体效率低下、工作失误或有意隐匿信息,此时,强大的舆论压力客观上能够帮助责任主体转变观念和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并有可能倒逼责任主体尽早公开真相,从而维护公共利益。因此,在事态“混沌”期内,对网上“过激”的言论一般应当适度宽容。
2013年5月17日,《广州日报》报道了该市第一季度18批米及米制品中有8批镉超标的消息,但是有关部门没有公开究竟是哪些牌子、哪些企业生产的米或米制品镉超标。报纸出版后,法律学者徐昕在当天8时55分发出新浪微博提出质疑。13 时59分,广州知名网友“厦门浪”率先在微博上猛烈围击广州食药监局。22时30分,新华社中国网事加入质疑队伍。5月18日0时3分,南方成希发微博称:“广州食药监局今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回应人民关注的焦点问题。”8时,中国之声追问:“有毒大米的品牌却以‘不便’为由秘而不发。不便的潜台词,是不愿和不敢。是对自己的调查没信心?还是留下公关的空间?是利益在作怪,还是权利在作乱?为违法者保密,践踏公众知情权,伤害政府公信力,更会让食品安全监管患上‘软骨病’。”16时14分,人民日报加入到追问行列。22时46分,中国之声报道“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镉超标大米品牌厂家批次名单”,舆论的要求终于得到满足。5月19日8时48分,“厦门浪”发布微博:“约束了政府部门权力寻租,自由裁度权的空间,只有把食品安全的问题,真正敞开给人民来监管,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至此事件基本平息。其间微博上出现了许多质问、辱骂,甚至粗口,尽管无根据的质问有可能对他人的名誉构成侵害,辱骂、粗口更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也应该看到过激言论是在特殊背景下出现的,并迫使有关部门公布了本应公开的信息,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是在“混沌期”过后,如果还有继续传播谣言、暴露隐私、进行人身攻击的言论,则应果断应对。例如,在2013年5月北京京温商城坠楼事件中,有人在真相已经清楚的情况下,继续利用互联网散布、传播京温商城安徽女青年“离奇”死亡谣言,并引发了严重后果。对此,就应该果断惩处。对于在真相清晰的情况下依然不改错误的报道口径、继续传播谣言的新闻媒体和媒体微博,则应按照出版管理法规及时从严处理。譬如今年1月,广州市民政局局长在全市民政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中透露广州将建第二“银河公墓”,此消息一出,如何“死得公平”立即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5月1日,《小康》杂志刊出《广州新公墓建设引争议》一文,5月7日上午9点,“广州拟投6亿元建造‘革命公墓’ 据称只埋党员干部”的言论开始在网上流传,并迅速形成流瀑。5月9日下午16时30分,广州市民政局通过官方微博澄清:“广州市福山公墓不存在‘只埋干部’说法。”中国新闻网5月9日19 时49分以《广州民政局:“投6亿建公墓只埋干部”说法失实》为题作了报道。报道说:针对互联网上疯传的“广州拟投6亿建公墓只埋干部”一事,广州市民政局9日回应称,广州拟投6亿的福山公墓项目目前规划有4栋骨灰堂、广州市遗体捐献者纪念广场及公众墓区、烈士墓区、荣誉墓区、艺术墓区、壁葬墓区等,不存在“只埋干部”的说法。②光明网等媒体也纷纷作了报道。主流媒体的及时报道使“混沌”立即转向了清晰。
在事态“混沌期”内,受众应以静观、慎动为原则。专家、学者则应积极提供社会服务,帮助澄清真相。主流媒体则要正视数字媒体引发的新的分工格局,发挥好证实平台的作用。其间,要特别注意管理好官方微博和记者、编辑的微博。媒体微博和采编人员的微博是媒体影响力在互联网上的延伸,必须和媒体的立场、态度保持高度一致,并应制止采编人员将主媒体尚未使用或决定不用的内容发在个人的微博上。
区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严管公共空间,宽管圈子空间,保护私人空间,营造宽严有序的交流场域
腾讯微信平台有“朋友圈”功能,有些用户的“朋友圈”很大,人数很多。那么,“朋友圈”到底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
如果这个问题一时还难以断言,不妨换个角度:用户小张通过微信向密友传了一段文字,或一张图片、一段语音、一节视频,但所传的讯息仅仅是在他和密友之间流动。这时可以获得第一个结论:微信这样的公共平台,荷载的并不一定都是公共讯息,也可以是私人讯息。也可以这样说:公共空间里也可以有私人领地。在私人领地,只要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讯息,都应该允许其自由流动。有些讯息虽然是法律禁止的、道德不提倡的,但只要信息传播的范围始终没有超出他们两人之间,法律制裁不了他们,也不受道德的公开谴责。
如果是在“朋友圈”中呢?讯息可以自由交流吗?譬如一批素食主义者聚集在一个圈子里——不仅是微信圈子,也可以是QQ圈子、微博圈子,甚至是现实中的圈子——以激烈的言辞声讨肯德基速成鸡的罪过。这样的圈子是否应该被禁止呢?不应该。因为他们虽然是在公开场合斥责别人,但是公开不是公共,他们并未把谈论的内容带入公共空间。在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媒体终端能够提供新的分享方式,以满足某些人的信仰和追求的时候,管理者应该尽量满足他们。当然,如果有人把所讨论的内容带出了圈子,甚至用来攻击其他公共空间人,就应该被禁止并应按相关法规加以处罚。
至此,我们又可获得一个结论:公开场合未必就是公共领域。只要他们手中有自媒体提供的分享渠道,只要保证在公开场合传播的讯息始终在“圈子”内流动,而不被带入到圈子外面去,这样的传播不损害公共利益,就没有必要禁止。
自媒体提供新闻,并不因此必然进入公共领域。里奥·西特拉希拉威茨强调:信息保留在某个狭窄受限制的团体内,它应该被视为隐私,即使这个团体相当大。一旦这个信息跨越太多的社交圈,那么它就不再是隐私了;如果受限于一个特定社交圈的信息,被某个人带出这个圈子,在这个时候法律可以追究他的责任。
至于在微博以及网络论坛,情况就有了不同。微博有私信功能,通过微博私信交流,信息依然在“圈子”里,微博又是基于关注与被关注的方式进行的定制化传播,不喜欢谁的言论,可以取消对他的关注,就有可能不再受到他所传播的内容的“侵扰”。但是,有时候你所关注的用户会在和粉丝的互动中带出许多你不希望见到的内容。所以还不能把微博看成就是自己的“圈子”,它更多的还是公共平台。对公共空间言论的评价,只能以公共利益为准则。
总之,管理者既要追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也要保护私人领地的言论自由。为此,区分公共空间、“圈子”空间、私人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网络用户也需要积累区分公开场合、公共空间以及私人领地的知识和经验。
注释
参见谢佳沥:“从媒介情境理论看社交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 人民网-传媒频道: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4110/213990/15920933.html,2011年10月17日。
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5-09/4803639.shtml。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