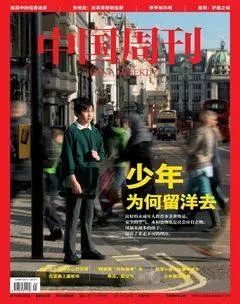被折腾的“小母牛”
2013-12-29彭波


五年之前的汶川地震,将国际NGO在中国的存在推向了前台。其中,就有一家总部在美国同时在成都设有办事处的NGO组织“国际小母牛”。
在众多的公益项目中,国际小母牛有着与众不同的“礼品传递”帮扶模式:向穷人捐赠牲畜并传授技术,穷人在摆脱饥饿和贫困后,则要承诺将获捐赠牲畜产下的第一代幼仔,以及自己学会的技术,像礼物一样,传递给其他需要帮助的穷人。
与很多本土的公益组织相比,小母牛中国办事处可以算是公益界的“贵公子”,每年它都可以从美国总部获得上亿元的运作资金,如此“财力”令许多草根组织艳羡不已。
但谁能想到,这个国际“贵公子”在中国的旅行,曲折得有些离奇。
落地中国
1984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第六个年头,四川省畜牧局通过中国科协时任负责人、数学家华罗庚引荐,与美国温洛克国际畜牧研究中心达成了一个技术支持项目。虽然项目由于国情差异最终搁浅,但温洛克却把四川省畜牧局介绍给了国际小母牛组织。
双方相谈甚欢,1985年10月,国际小母牛组织将158只英国高产奶山羊和200只美国优质种兔运抵四川雅安、简阳和大邑县,正式开始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的运作。
“那些白净乖巧的美国兔子后来的表现非常惊人,得到捐助的大邑县成为了闻名的商品兔生产基地”,陈太勇是当时迎接这批兔子的人员之一,现在是小母牛中国办事处的主任。
有了第一次成功合作,1989年,四川省畜牧局负责人应邀去美国国际小母牛组织总部访问,同意建立专门的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办公室,挂靠在四川省畜牧局内。但美国人并没有想到,这个中国办公室并没有像它的异国兄弟一样自由自在地做慈善。
彼时的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办,只有一间办公室。当年的陈太勇还是个小年轻儿,因为有了大邑白兔的成功,正胸怀壮志。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有了项目办之后,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竟变成了参加畜牧局的外事活动,隔三差五就会被抽调出去参加会议或者带外宾旅游,手中的小母牛项目只好一拖再拖。而在可以分身做项目的时候,他又会惊讶地发现,国际小母牛组织提供的一些经费和设备居然被畜牧局挪用。最令他不解的是,中国的小母牛项目并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一旦确定目标就予以执行,而是不断徘徊在畜牧局内部的争执中。
于是,陈太勇和他的同伴们渐渐失去斗志,“面对半途而废或者变来变去的项目,我们开始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那些来自海外的善心”。
之后,美国总部开始不满于中国项目办的执行效果,敦促项目办进行单独注册。
9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允许外资办企业,获得负责管理外资的省外经委批文即可登记注册。小母牛项目办的资金来自国外,自然属于外经委管理的范围,但由于彼时它的身份是四川省畜牧局的一个编外机构,如果单独注册,就要脱离省畜牧局,才能去外经委获得登记批文。
在中国,这两个部门关注的重点非常不同,外经委关注外资来源和项目是否合法,畜牧局则关注自己的管辖权限。被踢了几次皮球的小母牛,只好让美国总部给四川省外经委和畜牧局各写了一封信才达到目的,陈太勇还记得其中一段:“小母牛项目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同政府的关系相处很不错。如果单独注册机构,捐赠者会更加放心。但是,在实质上,我们还是在政府的领导下,本着尊重政府、给当地发展带来很大利益的目的开展活动。”
几番周折,1992年4月份,小母牛项目办正式注册成功,并搬出畜牧局。可好景不长,畜牧局领导班子调整,项目办又重新搬回畜牧局。国际小母牛组织总部开始对此失去耐心,要求中国小母牛项目办去广东或江苏等改革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探讨注册。很快,小母牛与南京市外经委取得联系,国际小母牛组织陆续拨入40万美元项目资金作为注册资本,但南京市外经委只同意小母牛注册为一家经营性公司。
“这样的话,虽然解决了单独注册的问题,但经营性公司必须有经营业务,还要定期提交税务报告和年度报表,否则就要被罚款,而中国小母牛只是一个非营利机构。”
一家公益组织,却要承担经营使命,其后果常常是因为没有按时上缴税务报表被罚款。与此同时,中国小母牛组织在与政府合作伙伴、捐助机构和新闻媒体等打交道时,往往要对这个带有经营性的身份进行很多解释,工作的进展非常缓慢。
漫长的注册
就在此时,失去小母牛的四川方面开始后悔,又竭力邀请小母牛项目再回到四川注册,并一路大开绿灯。终于在1997年,经四川省外经委批准,小母牛中国项目办以外资公司驻华办事处的名义在四川省工商局注册为美国国际小母牛组织成都办事处。
“我本来以为这之后就一帆风顺了”,没想到2002年,小母牛成都办事处在年审时没有通过。审批部门告诉陈太勇,最近有关部门准备出台政策,将小母牛这类国际民间组织的注册和年审改由民政部门审批。但由于相关政策条例还没有出台,具体怎么操作还不清楚。
“没法不着急,审批部门和工商管理局是两个系统,对工商来说,如果小母牛组织成都办超过六个月得不到主管单位的批文就属违规。”陈太勇开始多方奔走,努力的结果是小母牛仍由四川省外经委审批。
但在2005年10月,当成都小母牛项目办再次向已经更名为四川省商务厅的省外经委申请延期时, 却被告知:“我们无权再为像国际小母牛组织这样的非企业性质的国际民间组织审批注册。”而四川省民政厅则称,国际民间机构必须去民政部登记,并寻求部级机构作为主管或挂靠单位。
随后三年多时间里,小母牛组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注册之路,但都因为相关政策没有出台而失败。由于没有延续注册,中国小母牛组织开始面临银行账户延续,房产汽车等财产登记和年审的麻烦,员工招聘和雇用更是不便,最难以启齿的是“与项目伙伴单位签订协议却没有有效公章”。
最后,是一位民政部门的“高人”给陈太勇支了招,他建议中国小母牛不要一味地去追求以国际NGO的身份注册,“既然小母牛的首代是中国人,项目办又没有外籍员工,你们就注册成一家本土非盈利机构”。
陈太勇对于这个“高见”心情很忐忑,他知道如此注册新机构的名字将不能出现“小母牛”,因为在这个圈子里,谁都知道小母牛是国际NGO。可是,不用小母牛的名字,国际小母牛组织能不能同意就是个问题,而总部一旦撤资,中国小母牛将失去几乎是全部的资金来源。
不过,出乎陈太勇意料的是,美国总部很快同意了中国小母牛的改名请求,并把这视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而中国小母牛也终于在各种妥协之后,在2008年11月26日,正式注册为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意在用海内外筹集的资源惠及贫困家庭。
有了正式的身份后,小母牛在中国的发展开始理顺脚步。2011年,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受到了上海市民政局邀请,在上海成立了海惠社区民生发展促进中心,并参加上海对口援助新疆行动之中,“如果没有这个正式注册的身份,国际NGO是绝对没有可能参与敏感少数民族地区项目的。在中国,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太重要”。
妥协中的坚持
在国际小母牛的项目中,除去“礼品传递”式的帮扶捐赠,以社区为基础,用参与式项目管理方式开展社区建设也是工作任务之一。国际小母牛帮助过的社区和农村遍布全球,但这一工作在中国的开展却相对较晚。
变化始于2005年,国家扶贫办开始提倡新农村建设,鼓励公益机构参与其中。彼时的中国小母牛办事处尽管尚未解决身份问题,但却接受了美国总部的建议试水偏远农村的社区建设。陈太勇觉得是因为小母牛在四川多年的口碑才促成了最早的社区项目,否则一个身份不明的公益组织要想涉足这一块,“一定会非常困难,更不用说还是来自美国的小母牛”。
小母牛开展的社区建设,先是成立由15-25户农户组成的互助组,设立组长、副组长和出纳各一名。不同的是,在其他国家,互助组的组长很多是普通村民,但在中国,组长一般是村里的村长,“中国很特殊,所以互助组也要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
但即便如此,小母牛在社区项目上还是遭遇了一些“中国式”的问题,陈太勇就曾遇到一个不太讲理的县级官员,一定要求小母牛将扶贫项目安排到他自家亲戚所在的社区,否则就不予批准。陈太勇很无奈,只好一趟一趟去找这个官员做工作,不仅详细讲述了国际小母牛的帮扶原则,还要对比两个社区的贫困程度,几番苦口婆心才拿到项目审批。
而在四川剑阁的灾区项目上,由于小母牛筹集到了比较多的善款,剑阁县一个部门领导主动提出与小母牛合作,项目运行一度很顺利。但之后进行的领导更迭,却几乎毁了这个项目。原因是新任领导认为这是上任领导的“政绩”,并不多么上心。陈太勇只好选择了放弃。
陈太勇很羡慕其他国家的小母牛组织,他们从未有注册的烦恼,也不会遇到难缠的官员,即便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尼泊尔,小母牛组建的互助组和运行的项目也不会被政府直接干预。
当然,也有令陈太勇自豪的事情,在许多成立了互助组的乡村,村民的意识被唤醒,甚至有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举动。在四川山区的一个乡村,村民们想要修建暗渠替代经常被山洪掩埋的明渠,解决村里的用水问题。但政府由于之前已经帮着修了明渠不愿再拨款,互助组就撰写了详细的计划书,表明村民愿意集资和向小母牛申请部分资金,但剩余部分希望政府能够扶持。令村民有点意外的是,相关政府部门看后竟同意了这份计划书。
陈太勇把这个故事看做一次“村民”的胜利,但他仍然很谨慎,“就是一次有效的沟通而已,千万不能让政府感觉小母牛是在推动民主”。
有特色的痛
最近几天,往返于新疆和成都之间的陈太勇,又多了一个心事,他听闻小母牛美国总部将停止对海惠的资金支持,如果这事儿成真,小母牛将从公益界的“贵公子”变成“失血的贫儿”。
陈太勇认真地询问了总部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因为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美国总部认为中国企业和中国富裕阶层有能力帮助贫困地区,而海惠在多年发展后已经在大陆拥有良好的口碑,可以自我筹集善款保证项目运行。显然,美国人并不能深刻地了解中国公益和他们的不同。
从落地中国开始,中国小母牛办事处在资金上就对国际小母牛组织总部和香港分会非常依赖,不仅是由于获得正式注册较晚,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非官办的慈善组织并不具有公募资格。解决注册之后的小母牛,或许有了更多的公信力和优秀的项目,却并不意味着可以离开总部独立生存。陈太勇说,因为海惠目前的项目遍布全国,一旦失去支持会产生大量的问题,“尤其是和政府之间的,怎能让我不失眠?!”
而与“据说的撤资”相比,每一笔善款都要纳税的痛苦是陈太勇更想要吐槽的话题。在中国的公益圈,凡是民办公益组织,哪怕得到正式注册,也要缴纳税款。对海惠来说,它所获得的每一笔善款都要缴纳5%的税,年底更要缴纳17%的增值税。
2011年,当海惠与招商局基金会第一次合作时就忽视了税的问题,第一笔200多万元的善款,要缴纳十多万的税,招商局基金会不得已又对善款进行了追加。陈太勇很心疼那十多万块钱,如果帮助一个农户买牲畜的预算是5000块钱,这笔税款将令20多个农户失去帮扶的机会。
六十多年前,丹·威斯特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农民,后来是他创建了特色的“礼品传递”式的小母牛公益。但他恐怕不会想到,那只去往中国的“小母牛”,会遇到如此多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