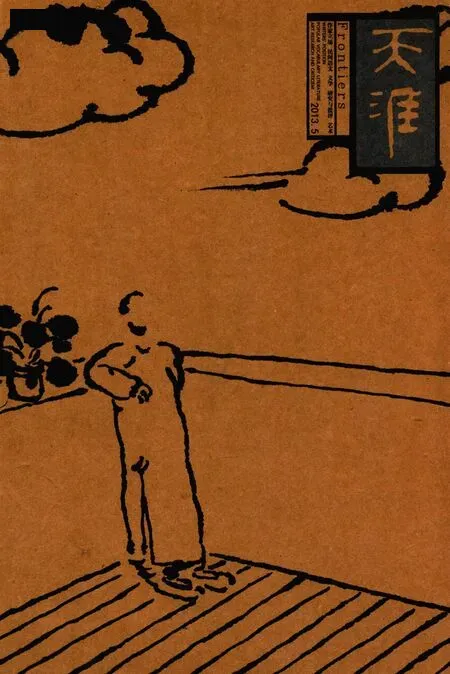红杨梅 青杨梅
2013-12-20樊健军
樊健军
黑马又在甩动尾巴,只要它的尾巴有所动作就暗示它有企图。元宝太熟悉了它的臭德性,它就是个厚脸皮的流氓、无赖。黑马真就昂着头,一步一步朝白马靠了过去。它全然没将元宝的愤怒放在眼里。黑马嗅了嗅白马的嘴,又用脑袋蹭了蹭白马的脑袋。黑马的讨好白马照单接收了,并且回赠了同样亲热的礼节,碰了碰黑马的嘴,蹭了蹭黑马的脑袋。这是元宝不能容忍的事实,心窝里像是让马踹了一脚,火嚓嚓地痛。他阻止不了黑马,那家伙太剽悍了,一不小心就会上它的当吃它的亏。有过一次,他试图将白马和黑马分开,黑马突然尥起后蹄,如果不是闪避及时,险些让它踢折了腰。总有一天我会宰了它,他恨恨地想。
元宝转脸朝向黑马的主人,巴望他尽快将它牵过去,给它套上鞍。黑马的主人叫铁叔,此刻双腿交叉,背靠竹坯而立,有一嘴没一嘴吸着烟。村子四面环山,山上多半长了毛竹,有人将毛竹砍下山,加工成做筷子用的竹坯,雇马帮驮到山外。元宝巴望着铁叔,铁叔却锁定另一个方向。那是个死角,刚巧让一堆竹坯挡住了。元宝直起身,才发觉是他娘在那里忙活。铁叔的目光全落在元宝娘身上。铁叔。元宝朝偷窥者叫了一声。哎,什么事?铁叔将烟头丢在脚下,用脚掌摁灭了,才转过头,朝向元宝。黑炭头。元宝狠狠地朝黑马做了一个手势,他本想骂它该死的畜牲,临到嘴边才改了口。铁叔朝元宝做了个鬼脸,站着没动。这间隙,黑马绕到了白马臀后,瞧那架势,试图跳到白马的背上。铁叔仍旧不动。元宝这才狠了心,操起一根竹竿,朝黑马奔过去,对准它的臀部戳了一竹竿,黑马遭遇突然袭击,长啸一声蹦走了,那神情不像落荒而逃,倒像一个得意的胜利者。你小子不要命了。铁叔心痛黑马,跳过来夺走了竹竿。
铁叔终于给黑马套上了鞍,元宝也将竹坯搬到了白马的马鞍上。一阵忙碌之后,他们出发了。这些年马帮败落了,仅剩五匹马在坚持。走在头里的就是铁叔的黑马,骨架粗蛮,毛色放亮,野着性子,一般人近不得它。它仗着自己的威武成了领袖,昂首阔步,只允许它的主人驾驭它。元宝瞧不惯它不可一世的模样,又拿它没奈何。紧随黑马之后的是匹棕色的母马,块头相对小巧,像个小媳妇,蹑着细步,亦步亦趋。它与黑马属于同一个主人。几步之后是匹棕色的公马,身架次于黑马,毛色发暗,步调有些迟缓。公马身后是匹年轻的母马,活泼好动,左争右抢,怎么也越不过棕色的公马。它经常打着响鼻以示不满。落在最后的是元宝的白马,炫目的毛色,诱人的身段,步调却很从容,不疾不缓,慢慢地,就同马队落下一截距离。它的主人着急,绷紧缰绳拽着它,拽了几步,只要缰绳松劲白马立刻就会放慢脚步。
赶马的有四个人,除了铁叔、元宝、元宝娘,还有细爷,细爷是棕色公马和年轻母马的主人。细爷正是享清福的时候,吃喝不愁,身子骨硬朗,偏偏闲不住,从别人手中接过两匹马,年长的马是爷爷,年轻的马是孙女。加上他,三个活物,夹在马队中间晃晃悠悠。细爷赶马属于即兴,想赶一票就赶一票,不想赶就马放南山。赶马的脚力钱多半买了酒喝。马队有了细爷就多了许多乐子,细爷赶马腰里别着酒葫芦,走几步喝口酒,喝到半醺,就嘴无遮拦,什么话儿都会说,什么山歌都敢唱。有些话说得元宝脸红耳热,有些歌唱得元宝都不敢听下去了,可谁也堵不住细爷的嘴。更离谱的,细爷有时喝醉了,就倒在路边睡觉,连马也不管了。元宝帮着将细爷的马赶过山,回来的时候细爷有时还在呼呼大睡。铁叔呢,不同于细爷,他是马帮的头,他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他的性子比他的黑马粗野,旁人的话说了白说,他的老娘才是他的神,她说一他不敢说二,她说往东他不敢往西。村子里的人都跑到山外讨生活了,他留在山里头就是为了照顾老娘。元宝赶马类似铁叔,完全为了生活,一天不赶马一天就没有收入。元宝想过不赶马,同村子里其他人一样到城里去打工,他娘不让,他也放心不下他娘。两年前,元宝爹在山里头扛木头,失脚坠到崖下身亡了,留下元宝和元宝娘。元宝娘是个哑巴,张嘴说不出半句话,只会啊啊叫嚷。元宝不想她掺和到马队中来,元宝娘却固执得很,捉住缰绳死不放手,逼得急了,张嘴能咬人。元宝几次劝说她不要跟着他,她就拿手势比划着,末了,只有元宝红着脸让步。你娘同你说什么鬼话?铁叔对元宝娘的手势很感兴趣。你才说鬼话,有精神就管住你的马。元宝瞪了铁叔一眼,没话来回答他。元宝娘的手势就是赶紧挣钱,挣够了钱,就给元宝娶老婆,生孙子。这小子,八成是你娘要给你娶女人了。铁叔却不恼,反而放肆地笑了。
村子前面的山是座矮山,上山十几里,下山也是十几里。路途不算太远,可山势陡峭,道路崎岖,每匹马的负重不少于三四百斤,所以马队行动缓慢。元宝的脚步放得更慢,元宝家只有一匹马,每次赶马他都背上一袋竹坯,马让他娘牵着。元宝不想靠得他们太近,细爷除了散发一身浓烈的酒气外,不时还冒出一股腐臭的气息。这两种气味混合在一起,连马臊气也压不住。只要元宝闻见了,就会恶心,反胃,有时会呕吐。好多次,他都想越过细爷,抢到细爷前头去。元宝又见不得铁叔的盛气凌人,他就像座山,压得元宝透不过气来。铁叔从来没将元宝当作成年人,眼睛里有藏不住的蔑视,张嘴小子闭嘴小子,在他眼里元宝就是个小屁孩。元宝恨不得一拳打倒他。他的恨藏在心里,不能让铁叔察觉。就算铁叔捆绑双手站在他跟前,元宝也干不倒他。元宝暂时只有回避他,能躲多远算多远。元宝最后的位置就定在白马的脚后跟了。元宝驮着竹坯,埋着头,一步一步往山上爬。偶尔抬起头,就见着了白马的臀部,白马的臀部不像是马的臀部,倒像一个女人成熟的臀部,妖娆得很,走一步扭摆一步,走着走着,元宝的身体里跟着有什么东西扭摆起来。那东西在身体内极不安分,妄图想窜出来。元宝拼命憋着它,不让它跑出来。元宝的身体因此热烘烘的,汗在汹涌。他想让身体冷却下来,却怎么也冷却不了。他只有放慢脚步,渐渐地,同白马拉开距离。
出发后黑马追逐白马的事情还在闹腾着元宝,所以他走得比往常更慢一些,有意让自己掉队。走一走,歇一歇,马队已经没影了,可他不着急。他们会等待他。每次赶马,马队都会在山顶歇上一阵,人喘口气马也要喘口气。马是畜牲,畜牲是人的财产,马要是死了,财产没了不算,赚钱的工具也没了,这不划算。山顶有一块平地,翻山的人都习惯站一站,望一望。往山下看,房屋不过脚边的一块石头,人就成了蚂蚁。马队这会儿肯定歇在平地上。他们在做什么,元宝也能猜个大概,细爷抱着酒葫芦喝酒,喝一口咂巴几下嘴,喝一口又咂巴几下嘴,好像喝的是参汤,不知多么滋润。铁叔站在平地边缘,向着山下,一手叉腰,一边吸着烟。元宝娘在照看马,它们逮住空隙,在平地边缘寻找一些绿色。三番五次的啃食,边缘的绿色已经少得可怜了。平地的北边是片杨梅林,马们就钻进杨梅林里寻找食物。有时他们也不让它们随便走动,就将它们拴在几根短木桩上。杨梅树都是野生的,一棵挨着一棵,树叶密密匝匝。三月的时候,杨梅树会开出一串串花絮,清香飘浮,野蜂飞舞。收了花絮,杨梅树就结了丁点小的杨梅,青青的,慢慢长大,由青而红,到成熟时杨梅也不见有多大,比一颗粗一些的黄豆大不了多少。红荡荡的,瞧着诱人,摘一颗扔进嘴里,酸得腮帮子都撕裂了。而且没多少果肉,硬邦邦的,硌牙。村子里的人都叫它铁子杨梅。只有渴极了,才摘一颗放进嘴里,也只能吮一吮,将核吐掉。
元宝从来没有进去过杨梅林。元宝爹不让,元宝娘更不让,村子里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不让小孩子跑进杨梅林,生怕他们跑进去就出不来了。小时候,元宝爹讲过一个故事,杨梅林里吊死过一个姑娘,让人发现时她乌紫着脸,舌头溜得好长。她为何死的,元宝爹没说,只说她是村子里长得极漂亮的一个姑娘,多少人盯着她呢。还没说亲就死了,可惜啊。元宝爹还慨叹过。元宝想,他爹说不定也盯过她,只不过没有盯到手。元宝每次从山顶上经过,都察觉杨梅林阴森森的,吹出来的风会起鸡皮疙瘩。有几次他壮着胆想走进去,临到林子边又收住了脚步。赶马时,元宝趁着热闹有过一次试图走进去,没走几步就让元宝娘堵住了。有时候,元宝娘却抛下他们,独自进了杨梅林。从林子里出来时,元宝娘有时脸彤红,有时脸煞白,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有一次,元宝娘在林子里待的时间特别长,铁叔努努嘴,让元宝去叫她娘。元宝。元宝往林子里走时细爷在身后唤他,元宝又收住了脚步。这犹豫间,元宝娘就从林子里钻出来了,白着脸,边走边捂着肚子。再瞧瞧铁叔,他的嘴角挂着一抹不易觉察的坏笑。
元宝爬上山顶时他们正在往马鞍上搬竹坯。歇息时他们会将竹坯卸下来,让马们轻松一会儿。黑马的鞍上码好了竹坯,黑马驮着竹坯赖在白马身边,见了元宝黑马打了一声响鼻,似乎对早上的事情耿耿于怀。细爷可能赶着马下山了,不见了人影。元宝娘捉着缰绳在手,见了元宝就啊啊叫着。铁叔正往白马背上搬竹坯,斜里觑了元宝一眼。元宝娘埋怨元宝走得太慢了,他们都要下山了。元宝没有搭理他娘,元宝娘急了,转过头啊啊叫着,要铁叔将刚刚搬上马背的竹坯卸下来,她等着同元宝一块下山。铁叔不但没卸竹坯,反而将地上的两袋竹坯全部搬到了马鞍上。元宝娘跳过去阻止时,铁叔的手一划拉碰在了她的胸口上。这只是个瞬间,铁叔好像无意碰到了元宝娘的胸部,元宝娘的脸腾地红了,后退了一步。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元宝的眼睛。元宝娘瞪了一眼铁叔,又转眼瞧瞧元宝,元宝却死死盯着铁叔,铁叔谁也不看,像个没事人一样解开缰绳,牵着马,吹着口哨,头也不回下山了。
这一趟马赶过来,元宝的情绪莫名其妙坏了,见了谁都没有好脸色。回到家,将马拴进马棚,元宝就缩到了屋子里。元宝娘问他晚饭下面条还是煮稀饭,他也没回答她。他仰着头,躺在床铺上。他的眼前有马影在不停地跑动,黑马、白马、棕色马,黑马涎着脸一步一步靠近白马,白马在躲避,黑马越发放肆了,将白马挤到了马棚的角落。黑马同白马原本不住在一个草棚里,铁叔住后山,马牵来牵去不方便,就将马寄住在元宝家的马棚里。元宝本来不答应,铁叔绕过他同元宝娘说妥了,将草棚重新翻盖了。娘答应了的事情,元宝不好再说什么。马只是一个借口,他隐隐觉得铁叔还藏着其他目的。什么目的,他并不知晓,只知道铁叔上他家的次数多了起来,到马棚里瞧瞧他的马,在元宝家坐一坐,喝杯茶。如果碰巧,就在他家吃顿饭。有时会同元宝娘开个玩笑,元宝娘因此面红耳赤,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别的出格的事情。有一天,元宝给马打草回来,铁叔正在他家的屋子里。元宝丢下草捆走进屋子时,正巧碰见了铁叔将娘逼在墙角里,铁叔左手拿了一张百元的票子,另一只手朝元宝娘的腰里摸了去。那只手捋着袖子,五指叉开,张牙舞爪的。元宝娘涨红了脸,啊啊叫着,摇摆着双手。她已经无路可退了。元宝打了声咳嗽,铁叔才收回了手。
元宝这才看透了,铁叔像马蝇一样盯上了他娘。元宝娘虽然是个哑巴,可在元宝眼里,村子里没有哪个女人比他娘齐整,俊俏。快四十岁的女人,元宝娘依旧细皮嫩肉,从脸上看三十岁不到,腰肢比马鞭还柔软。有时候,元宝甚至偷偷地想,将来一定要娶一个像娘一样的女人,当然不能是哑巴。他并不是嫌弃娘是哑巴,而是哑巴有话没法说,打手势费劲,而且很多话说不明白。元宝撞破了铁叔的歪心眼后很后悔,那天就该一刀砍了他的狗爪子,让他离娘远一点。爹不在了,只有元宝来保护娘。他得提防着铁叔,别让他靠近娘。晚上的时候,元宝睡得格外灵醒了,只要稍有动静,他的耳朵就竖了起来。原本元宝娘晚上要起来给马添草料,现在元宝接管了,黑灯瞎火的,他不想让娘出来。元宝添草料,添着添着就来气了,每次走进马棚黑马都昂着头,那神情比铁叔还傲慢。得想个法子教训教训它,他想。他想过少给它两把料,或者给它一些粗料,可是他娘对他做的事情似乎不放心,每次添料后她都要察看一遍,他很担心娘会识破他的诡计。有一次,他挖了一条竹根,缠了布条,做成马鞭。他提着马鞭,想趁黑马猝不及防抽它几鞭子。等他靠近黑马时,猛然回头,发现他娘就在马棚外边站着。元宝握着鞭子的手就软了。
元宝接连憋闷了好多天,每次赶马,黑马和白马的故事都在重演,谁也无法将它们分开。除非元宝不赶马了。况且黑马和白马同在一个马棚里,虽然隔着栏杆,可黑马总是不死心,身子越不过栏杆,它的脑袋就从栏杆中钻过去同白马亲热。元宝迁怒于白马,不要脸,用马鞭抽了白马几鞭子。白马挨了抽,却不明白哪儿错了。黑马靠近它时,白马依旧热情呼应。元宝没奈何,只有远远避着,每次赶马都掉队。有细爷在,他不担心铁叔会对娘怎么样。细爷同铁叔娘是一辈人,铁叔敢在细爷跟前撒野,细爷只要对铁叔娘说几句,铁叔就会被他娘骂个狗血淋头。可黑马和白马的事元宝没法同铁叔娘去说,铁叔对元宝娘的事更不能开口,牵涉到娘呢,这个道理元宝懂。元宝只能烂在肚子里。细爷却以为元宝有心思了,就取笑他,元宝长大了,元宝想女人了。细爷的话说得正儿八经,又不像是玩笑。细爷还同元宝娘比划着手势,元宝长大了,要给元宝娶老婆了,元宝娘要抱孙子了。元宝娘望望元宝,嘴上啊啊附和着,脸上笑开了花。元宝对着细爷干瞪眼,细爷却不惧他,该说还说,该笑还笑,元宝只好不理睬细爷了。
有一次,元宝终于忍不住,在山顶的平地上抽了黑马一鞭子。黑马正靠着白马,挨了鞭子却不惊,反而尥起了蹄子。它气愤元宝坏了它的好事。元宝往旁边闪开,黑马倒向他蹦了过来,又尥起了蹄子。后来如果不是铁叔制服黑马,元宝非挨上它一脚不可。元宝丢了面子,并不灰心,暗暗拿定主意,一定得教训它一顿,给它点颜色瞧瞧。铁叔察觉了元宝眼里的愤怒,好多天都将黑马牵了回去,元宝的阴谋落了空。等他的愤怒渐渐平息了,铁叔才将黑马赶回马棚里。
元宝警觉着,铁叔对娘似乎贼心不死。有元宝在,就绝不可能让铁叔靠近娘一步。事情就这么僵持着。细爷有几天不赶马,元宝就死死地粘着他娘,不让娘离开他。瞧铁叔,好像并不在意元宝的举动,有几次还吼起了山歌,爬上山坡唱山歌呀,我唱山歌没人和哟,高山打雷平地雨呀,娇莲不见泪满箩哟。铁叔的山歌调子越唱越高,边唱边拿眼睛瞅着元宝娘,铁叔的眼睛就像狗舌头上上下下将元宝娘舔了个遍。后来的一天,细爷给元宝出了道难题,细爷许是喝多了酒,跌到路坎下,将脚扭伤了。细爷不能赶马了,将两匹马托付给元宝,一匹马的脚力钱给细爷当酒钱,另一匹马的力资给元宝当工资。细爷说马不赶就懒了。这事他答应得痛快,既帮了细爷的忙,也不亏待自己。多了两匹马,元宝有些手忙脚乱,特别是那匹年轻的母马,蹦蹦跳跳,只会给他惹麻烦。一会儿险些将棕色的公马挤下道,一会儿竹坯让路边的藤条缠住了。他还不能用鞭子抽它,否则它就跳得更欢了。这马不长记性,就算惩罚它了,过一天它就会忘得一干二净,该怎样还怎样,完全依着它的性子。元宝只有紧紧拽着它的缰绳。这样一来,他就没法看护他娘了,好几次因为母马捣蛋,落下了一大截路程。他急忙赶上山顶,他娘坐在木桩上歇息,铁叔抽着烟,朝向他的来路,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元宝才松了一口气。
事情后来还是越出了元宝的预想。那一天,元宝不知吃坏了什么东西,走了不到两里路,肚子就咕咕叫个不停,肚子一叫他就忙着往树林子里钻,等他出来时两匹马都不见了影踪。棕色的公马老实得很,慢慢腾腾爬向了山顶,母马反倒往回走了。元宝将母马拽回来,急着往山上赶,赶了没几里路,肚子又咕咕叫了。他摁着肚子想不理睬它,走了不到半里路,憋不住了,终于又钻进了树林。折腾几次,元宝爬上山顶时平地上不见了铁叔和他娘,几匹马拴在木桩上。黑马见了他,打了个示威的响鼻。元宝脑子里嗡地响了一声,像被黑马踢了一脚。他什么也没想,朝杨梅林扑了过去。可没冲进去几步远,就遇着了铁叔。铁叔并没有被他的凶相吓住,横着身子堵在了路中间。我娘呢?元宝仍旧往林子里冲,但他被铁叔挡住了。元宝不罢休,朝铁叔撞了过去,铁叔双手一拱一掀,元宝噔噔噔退后了几步。元宝的脸铁青了,挥起马鞭,劈头盖脑朝铁叔抽了过去。铁叔侧身避过,捉住元宝的胳膊,将他摔了个狗吃屎。元宝爬起来,还想动粗,元宝娘从林子里跑了出来,啊啊叫喊着,将元宝拦腰抱住了。元宝挣扎着,就是没法挣脱。挣扎得累了,元宝就坐到地上,呜呜地哭了。元宝的内心像有什么坍塌了,满地狼藉。元宝娘绞着手,可怜巴巴瞧着他,不知他怎么了,也不知该怎么办。后来元宝娘跟着坐到了地上,抱着自己的脑袋,揪着自己的头发,呜呜咽咽哭了。
那天晚上,元宝怎么也无法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突然有只手扼着了他的脖子,越扼越死,只差一口气就憋晕了。元宝从梦中惊醒后爬起来,操了刀,直奔马棚。日你奶奶的,我要砍了他。元宝在内心凶神恶煞地咆哮。马棚空空荡荡的,黑马不在,只有白马孤独地守在一个角落。元宝的一腔怒火找不到燃烧的对象,一刀砍在了马棚的柱子上,马棚蓬隆一声响,白马吓了一跳,不安地打了个响鼻。接着又是几刀,马棚的一角垮塌了,茅草沙沙地撒到了地上。元宝还不解恨,又奔向了马棚的另一角。元宝娘听到响动爬起来,抱住了元宝,元宝发了狠,元宝娘让他硬拽着跑了几步,靠近了另一根柱子。又是几刀,柱子立刻折断了,马棚的一端全塌了。元宝娘阻拦不了元宝,双腿一软,朝元宝跪下了。白马受了惊吓,从马棚里跳了出来,朝黑暗里奔了去。元宝这才扔了刀。
暴风骤雨过后,元宝的内心并没有平静,暗暗谋划着,该怎样报复一下黑马和铁叔。他的眼睛里像是藏了一把阴郁的火,让铁叔有了警惕。铁叔拘束了黑马,不让它随便靠近白马。有几次元宝操了竹竿,想趁铁叔不防备偷袭他,可铁叔的后脑勺像长了眼睛,元宝的手刚碰到竹竿,他就转过身向着元宝。元宝娘也像是窥破了元宝的阴谋,每次赶马她都亘在他和铁叔的中间,不让他靠近铁叔。有一次,元宝终于逮着了机会,铁叔立在土坎边撒尿,那匹棕色的母马紧随其后。元宝挥起马鞭,狠狠地抽了母马一鞭,母马的性情温顺,从来不挨鞭子,母马挨了抽猛地往前蹿过去,刚巧撞着了铁叔,铁叔跌落到了土坎下。幸好土坎不陡,铁叔不过摔了一身泥,并没有伤筋动骨。这次偷袭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元宝的信心,只要留心,不愁放不倒铁叔。
半个月后,元宝策划了一场阴谋,在下山的路上设了个陷阱。那天,铁叔牵着黑马像往日一样走在前头,平静了半个月,他也放松了对元宝的警惕。元宝生怕他娘跟得太紧迫,故意说眼睛进了沙子,让他娘帮他吹吹眼睛。就在他们停住的间隙,轰隆一声响,铁叔连同黑马跌下了路,轰轰隆隆朝山坡下滚动,翻了一个滚,又翻了一个滚,才让一棵松树阻住了。元宝娘惊昏了,好半天才醒过神,呜哇一声,连滚带爬滑向了铁叔。铁叔卡在树底下,左右动弹不得。元宝娘忙乱了好半天,铁叔依旧没挪动半步。铁叔龇牙咧嘴的,肯定哪儿摔坏了。元宝娘急得哇哇叫着,招手让元宝去帮忙。元宝站着没动,不知道该不该去帮忙。他的内心有个声音在欢呼,声音就像山风一样呼啸着。他又有些忐忑,是不是太过分了,万一铁叔真摔坏了,那是他活该?罪有应得?元宝娘在树底下跺着脚,指着元宝。她在骂元宝。元宝依旧不动,血往脸上涌,给他的脸上蒙了一层红。元宝娘叫不动元宝,捶胸顿足嚎啕起来,边哭边做着手势。元宝瞅清楚了娘的手势,脑袋嗡嗡地跟着嚎啕了一声。元宝娘的手势说,元宝是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元宝爹摔死在山崖下,就是铁叔套了黑马将元宝爹驮回来的。如果不是铁叔,元宝爹的尸体恐怕都找不到,说不定烂在山上了,让老鸹啄了,让老鼠食了。这是元宝不知道的,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他就在空白中滚下了路,同他娘一块将铁叔抬到了马背上。铁叔摔折了一条腿,黑马比铁叔更惨,废了两条腿,再也站不起来了。
铁叔至少要在床上躺大半年才能下地,腿会不会瘸还不知道。元宝不过撬动了路边的一块石头,并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元宝背着娘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小时候元宝调皮了,做了错事,元宝爹就会拧着他耳朵。现在没人拧他耳朵了,他只有自己扇自己嘴巴。嘴巴挨了巴掌,嘴角渗了血,还肿了。元宝娘问元宝怎么了,元宝说摔了一跤,嘴巴碰在石头上了。她埋怨他,走路都不小心,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她捉了一只鸡,用手巾包了二十个鸡蛋,让他去看望铁叔。元宝接了鸡和蛋,去了铁叔家。铁叔躺在竹椅上晒太阳,见了他也不说话。铁叔的女人给他搬了椅子,泡了茶。元宝接了茶,却不敢坐。铁叔的眼睛里有种光亮,照得见元宝的内心。元宝有些慌乱,借口要给马割草,茶也未喝就走了。赶马时盯着脚下,别踩失脚了。铁叔提醒他。元宝假装没听见,飞快地脱离了铁叔的视线。
山路上突然冷冷清清了。细爷的脚扭伤后走路一瘸一拐的,不愿凑热闹了。铁叔一时半会上不了路,况且黑马废了,还少了马匹。幸好剩下的竹坯并不多,误不了别人什么事。山路上只剩下元宝和三匹马。元宝娘没有跟着去,元宝威胁过她,如果她跟着去他就不赶马了。元宝娘不放心,哇哇叮嘱他,叫他路上小心些。元宝一个人赶马就自由了,想休息就休息,想休息多久就休息多久。在山顶上歇息的时候,他几次动了念头进杨梅林,都没有进去。有一次返回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进了杨梅林。过了杨梅收获的季节,树上只剩下密不透风的叶子。林子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地上是浅浅的草,可能阳光不充足,草怎么也长不茂盛。山风吹过,林子里有窸窸窣窣的响动,像有人蹑着脚步在走。环顾四周,却什么人也没有。元宝吮了一下鼻子,山风像是送来了一股什么气味。它顺着呼吸道迅速进入他的身体,一直侵入到他的肺腑。他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味道,有些潮湿又有些腐败,闻到仔细处好像又消散了,什么气味也没有了。他在林子里静立了一会儿,太阳落山了,林子里慢慢暗了下来。山顶冷得快,元宝感觉了凉意,移动脚步时打了个寒战,手臂上突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不敢停留了,赶紧出了林子。好像有脚步声跟着他,他走一步身后的人也走一步,一步一步跟着他出了林子。脚步声紧跟着他。他不敢回头,牵着马,匆匆忙忙跑下了山。
若干年后,元宝同山外的一个女人一起翻山进村。山外的女人走惯了平地,不习惯山路陡峭,爬上山顶时早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就坐在山顶的平地上休息。山村早没人赶马了,多半的人早搬到了山外,系马的木桩都腐朽了。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杨梅树的叶子间藏了星星点点的红。女人突然来了精神,嚷嚷着要摘杨梅。元宝就依了她,领她进了林子。女人踮起脚,攀住了一枝杨梅。一颗杨梅还没摘到手,元宝拦腰将她抱住了。坏蛋,你干什么嘛。女人假意挣扎着。元宝不听她说的话,将她放倒在草地上。它们都看见了。女人嚷嚷着。谁?元宝吃了一惊。你瞧,那些杨梅,红着眼睛呢。女人还在挣扎。别管它们,就让它们看着。元宝不再理会女人的话,将自己的事情勇猛地进行下去。完事后,女人整理了衣衫,嘟囔着说口渴,元宝说回家喝茶吧。你给我摘杨梅。女人要求元宝。杨梅酸呢。元宝不愿意。酸就酸,我就喜欢酸东西。女人撅着嘴坚持要。酸掉了牙可别怪我。元宝就摘了几颗杨梅给女人。女人接过,扔了一颗在嘴里,才嚼动了一口,就夸张地叫了起来,妈呀,真酸。女人将杨梅核吐在了地上。你看,后悔了吧。元宝责怪她。我不后悔。女人又往嘴里扔了一颗杨梅。她是喜欢酸还是真不怕酸,元宝弄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