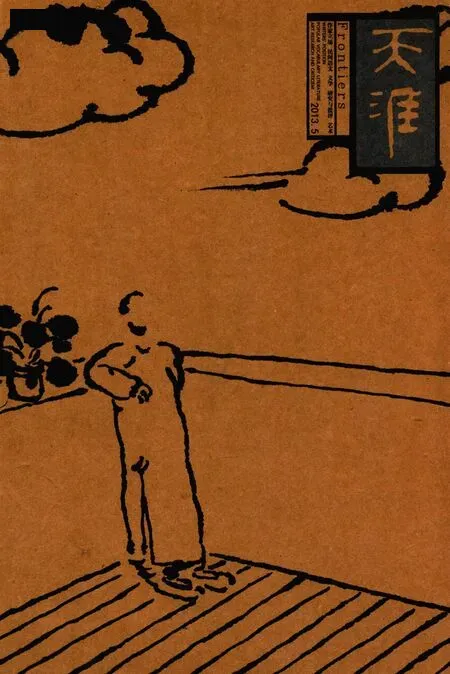历史可以这样假设吗?
2013-12-20朱也旷
朱也旷
如果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高一点或者矮一点,那么历史就会变个模样,这个著名的说法据说也适用于美国的建国时刻。在讲了一些美国的有利条件后,历史学家朱学勤说:“甚至当历史召唤,需要写独立宣言时,只好杰斐逊在场;当历史第二次召唤,需要制定1787年宪法,汉密尔顿在场,杰斐逊在法国。如果这两个人出场次序颠倒,那就既不会有《独立宣言》(或者会是另一个样子),也不会有1787年宪法。”(见《两次革命,两个政治传统——朱学勤谈美国、法国革命》,《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2月25日)。这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接着说:“如果考虑到这么多因素,有句话政治不正确,但确实说出一些东西:上帝参与了美利坚建国的过程,让她有这么多的幸运条件。”
朱学勤先生是知识界的翘楚,他的文章启发了很多人。现在,对于美国建国初期的一些事,他不过随口一说,我却要长篇大论地去反驳他。这样做,对先生是不公平的。但我确要写一篇文章,因为在他的随口一说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即我们可不可以对历史做假设,这种假设有没有意义。
历史学家是逆向的预言家,即从结果中去寻找原因。这种逆向预言是否可靠,本质上是无法检验的。这就导致人们对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有时候历史学家也喜欢做一些有趣的假设,以进一步显示他们的预言能力。当他们倒拨时间的指针,改变历史上的某些条件或因素时,他们的预言看似言之凿凿,其实更不靠谱,至少不比经济学家靠谱。经济学家发表预测意见时,有时候还要依靠精心设计的模型。模型意味着对现实的简化,而被简化掉的常常不是无关宏旨的。这就是经济学不靠谱的根源所在。但模型一旦确立,数学工具就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经济学有时候看上去像科学,原因就在于此。历史学家通常既提不出模型,也无微积分之类的数学工具来保证从模型获取结果的准确性,历史学很少能与科学沾上边,原因也在于此。所谓的数理史学的昙花一现,说明历史学依然是一门人文学科。顺便说一句,在最近出版的《公天下》中,吴稼祥引用了一些物理学公式,这些公式只能在比喻的意义上被使用。
让汉密尔顿来起草《独立宣言》,杰斐逊来起草美国宪法,这个主意听上去不错。汉密尔顿是金融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奇才,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走工业化道路;而杰斐逊长于写锦绣文章,主张小政府以及保护农民利益。这两个人的出场次序如果颠倒,肯定会对历史进程有影响。但问题是,这样的假设有多大的合理性呢?
1776年6月,大陆议会授权一个五人小组起草《独立宣言》,此时汉密尔顿只有十九岁(最多二十一岁,历史学家对他的出生年份尚有争议),还是纽约国王学院的一名学生,根本不具备足够的政治声望。在五人小组中,亚当斯、富兰克林、杰斐逊的地位尤为重要。宣言的第一稿由杰斐逊单独起草,这个建议来自约翰·亚当斯。在独立运动中,亚当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年前推举大陆军总司令时,正是亚当斯的建议发挥了作用。《独立宣言》如果换个人起草,肯定会有不同,但是否会有很大的不同呢?
实际上,现在这个版本就是换人之后的结果。至于那个被换的人,却不是乳臭未干的汉密尔顿,而是颇有才干的理查德·亨利·李。按照尹宣的说法,李的妻子恰巧病了,他只得回弗吉尼亚老家去照顾她,于是错失了这个历史机会。《独立宣言》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这之前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宣言、请愿书和告人民书。它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体现的是殖民地人民当时的情绪和政治意愿。这样说,倒有几分决定论的蛮横,但有一个证据恰恰可以给这个观点以一定的支持:文本分析表明,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曾从梅森的《弗吉尼亚人权宣言》中借用了大部分内容。
1787年宪法并不是美国的第一部宪法,六年前通过的《邦联条例》才是第一部宪法。之所以会有第二次制宪,是因为《邦联条例》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所致。这个松散的条例对于当时的十三个州几乎毫无约束力,每个州形同一个独立的国家。解决这些问题——麦迪逊罗列了十一条——在相当程度上已是当时政治精英的共识,而推动制宪的关键人物正是麦迪逊,一位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人物。他的巧妙策略和经过长期思考的宪法理念,在关节点上发挥了作用,从而影响了费城会议的进程。麦迪逊也因此被一些人称为美国的宪法之父。不过他自己倒是不情愿当这个“之父”,认为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汉密尔顿虽然跟麦迪逊一样,赞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他的极端的联邦主义观点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反对。如果杰斐逊参加了费城会议,会导致一个非常不同的宪法吗?这个可能微乎其微。但杰斐逊的参加,确有可能使权利法案被写入宪法,而不是以修正案的形式出现。总体上说,费城制宪会议可以被视为温和的联邦主义者的胜利。正如极端的联邦主义者不会成功一样,它的对立面也很难取得成功。斯托林在一部研究宪法反对者的专著中指出,反联邦主义者在后来的宪法辩论及表决中失败了,“不是因为他们是不那么聪明的辩论者或不那么娴熟的政治家,而是因为他们的论点较弱”。这个结论如果成立,就有理由认为,即便杰斐逊成为像帕特里克·亨利那样激进的反联邦主义者,他能否走得更远,也是颇有疑问的。
从第一届大陆议会的呈交英王请愿书到第二届大陆议会的《独立宣言》,从松散的《邦联条例》到具有凝聚力且强调权力制衡的《合众国宪法》,从第一任总统的产生到权力向新总统的和平移交,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件可以被视为展示人类自组织能力的少有的范例。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许多至今令人难忘的人物。这些杰出人物并不是上帝恩赐的,而是美国人民选择的。其中有一个人,朱学勤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一直没有提及。这个人也许没有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汉密尔顿、麦迪逊、威尔逊、莫里斯那样的聪明才智,在整个制宪期间,他总是保持审慎的沉默,没有发表任何激动人心的演说。但这个人其实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重要。没有他的参与,任何重要的政治活动都不可能成功。显然,他才是合众国建国的最大的初始条件。
但这个人同样不是上帝恩赐的,而是由美国人民自己选择的。1775年6月,他被推举为大陆军总司令。在他的带领下,大陆军打了一些胜仗,更多的是撤退和败仗。他的坚韧不拔以及正确的战略,最终使得英国人坐到谈判桌边,签署了放弃殖民统治的《巴黎和约》。独立战争胜利后,他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凯撒或克伦威尔。如果他打算这么做(这个假设倒是合理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很可能就将完全改写了。但他主动交出权力,成为退休将军。在两届总统任期结束时,他又主动提出不再连任,成为退休总统。这个人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乔治·华盛顿。
就军事才能而言,华盛顿不是最突出的。就人格而言,他也有一些人类的弱点,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完美。正如费边·马克西穆斯的智慧易于被同时代的罗马人低估一样,乔治·华盛顿的智慧也易于被同时代的美国人低估。杰斐逊认为他“既没有博学深邃的思想,也没有雄辩流畅的言辞”,亚当斯的评价则更严厉。事实上,正是这个既不会舌灿莲花,也不会妙手著文章的人,引领这个新生国家绕过了无数的暗礁险滩。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相比,美国人多么会选择自己的领袖,从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美国人整天把上帝保佑美利坚挂在嘴边,其实他们一直努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相形之下,中国人虽然不信上帝,却整天盼望有一个救星或者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拯救自己。这种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自然是盼不来的。盼不来,一些人便自怨自艾,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幸的、受诅咒的民族。
但上帝的确参与了美利坚的建国过程,不是以朱学勤先生以为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在那些著名的建国元勋中,你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信仰或不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人。华盛顿认为,“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没有宗教原则,国家的道德就不可能建立”。理查德·亨利·李的表达则更准确,“无神论者可以尽其所好来编制理性之网,但是所有时代的经验都表明,宗教是道德的守卫者”。成年后的富兰克林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在制宪会议陷入僵局时,恰恰是他向那些吵得不可开交的代表们提议向上帝祈祷,就像签署《独立宣言》的人们所做的那样。
如果再往前看,我们还可以发现,那些最初向北美大陆移民的人,那些登上“五月花”号的人,除了浪荡子、失意者和底层人士外,受迫害的清教徒占有很大的比例。简言之,他们要么无所信仰,要么信仰加尔文的神学。当自组织现象在他们中间发生时(这是很自然的),加尔文主义便成为一个核心,且是唯一的核心,这正是四十一名成年男子在船上签署《五月花号公约》时的情形。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据此认为,约翰·加尔文才是美国的真正的创始人。这个观点可能就连很多美国人也觉得怪异,但它无疑能促使人往事情的源头上回溯。这是今天的巨人彼时尚处于胚胎状态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从一开始就没有缺席过,尽管他从未干预过任何事情的进程,更谈不上刻意安排重要人物的出场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