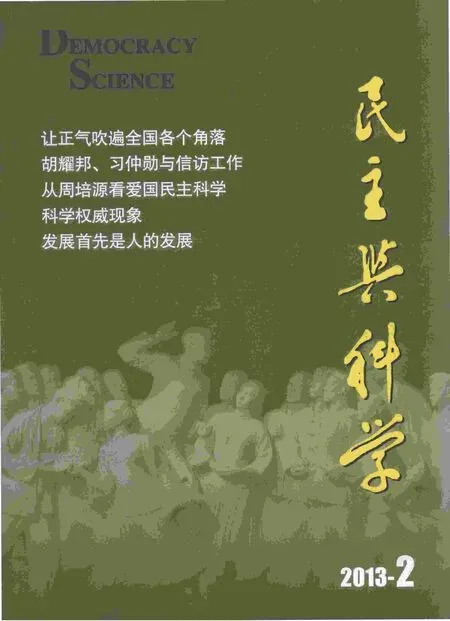所谓“文人法学”——《文人法学》一书代序
2013-12-19林来梵
■林来梵
作为一介法律学人,随着年岁渐长,思虑渐深,这几年越来越深入体悟到:在当今中国,欲推行法治主义,必先有人去践行法治启蒙,否则,法治国家的构想终究会化为泡影。有鉴于此,平时闲来也写一些轻松的学术随笔,或发表于博客与报章,或暂藏于私人文档,隔了一些年头,便会蓄了一些篇什,可以裒辑成册,斗胆拿来付梓。这本小书就是继《剩余的断想》之后又一册同样类型的覆瓿之作。
本书的书名《文人法学》,源之于2007年在《法学家茶座》第13辑上发表过的一篇拙文的题目。那篇文章开宗明义便指出:环顾当今中国法学界,似乎可以套用《共产党宣言》的首句,说:
“一个幽灵,文人法学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这不完全是笑谈。笔者较早之前就观察到,在当下我国法学界,实际上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文人法学”的流风,其代表性的学人,可首推朱苏力、贺卫方、冯象、许章润、舒国滢等数位学者,还有一批年轻的学者或学子追随其后,在“暗夜里穿越”(套用强世功评苏力语),以致聚成了一定的群落,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即使还不足以构成一种流派,至少也称得上一种品流了。
说到这“文人法学”,其标志性的倾向,至少可初步归纳出如下几种特色:
其一,擅长以流丽的语言、猎奇的视角,甚至精妙的隐喻,克服了法学枯燥生硬的本色。比如朱苏力教授,本身就是写诗出身的,自言“一度想当诗人”,从来文辞优美,音韵丰沛,近年来更干脆挺进“法学与文学”的领域,其总体的研究个性,在此方面颇有典范意义。
其二,虽然没有排斥理性思维,甚至还暗含了“理性的阴谋”,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能巧妙地诉诸情感的运用,借以催发其文字作品的感染力,与受众(特别是年轻学人或学子)的情感多发性倾向之间,恰好形成了某种密切的共鸣关系。不言而喻,贺卫方教授的魔力,便在部分上得益于此。
其三,偶尔也表现出对法学学科、尤其是对其中的部门法学本身的某种轻慢的、多少有点儿“陪你玩玩”的态度,却在一种萧散简远的风格中纵横捭阖,暗含机锋,明显具有超越性或反思性的思维倾向。冯象教授或许即可谓此方面的代表。
本来,无论是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实践功能方面,法学都拥有许多卓越的优长之处,而历经磨砺的现代法学尤其如此,但无可否认,法学也有刻板、琐细、甚至为当代日本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先生所指出的那种狭隘的特征,正因如此,法学本身也就成为一门容易逼使内部学人走向叛逆的学问。而在法学的叛逆者之中,历史上也就不乏有人在其他领域里取得了震铄古今的成就,马克思、歌德、卡夫卡均是这样的人物。所不同的是,他们叛逆的程度和类型也有所不同,其中既有马克思、歌德那样的全面反叛,也有卡夫卡式的叛逆,即虽为稻梁谋而继续留在法学阵营之内,但却热衷于其他的志业。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文人法学”也是对正统法学的一种叛逆者,只不过仅属于一种接近于卡夫卡式的叛逆,而且情节更加轻微。它在一定程度上乃生发于当代中国部分法律学人对本国传统人文学问的那种挥之不去的乡愁,为此在一定范围内也可能是属于我国法治尚未成熟时期传统的“人文”与纯正的“法学”之间的一种中间过渡形态,但无论如何,它也恰好应合了前述的法治启蒙主义这一时代课题。
其实,即使从西方的知识谱系上来看,法学与人文学科本来也就具有一种无法割裂的血脉关系。君不见,在中世纪的罗马,早期的法(律)学即曾被作为修辞学的一种类别,后来注释学派转而借鉴了同时代经院神学的各种圣经解释的技法,用以解释《罗马法大全》,由此形成了作为传统法学的主要方法——法解释学的雏形,并随着近世初期之后罗马法在欧陆的广泛继受,而为西方近代法学所承袭与发展,乃至在德国流的法学传统中,法学还被称为“法教义学”,但说到底,现代人们已经承认,这种法学其实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还是属于一种“理解的学问”。无怪乎德国现代法学家Hal lerbach曾剀切地指出:法学本来就是“人文科学的学问,因为它面对的对象正是人类及某种人类精神的具象化,即以‘语言创作’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人之作品’”。如此说来,如何发掘与提炼法律之中的人文精神,或以人文精神去反哺、滋养甚或反思法律本身,也是现代法学应予高度关注的主题。从这一点而言,“文人法学”也具有合法生存的价值。
当然,或许在部分人看来,“文人”一词也有一些负面的色彩,记得钱钟书先生就曾经在不无解嘲的意味上引用过“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之类的旧说。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文人法学”本身所可能带有的局限,它毕竟不是纯然意义上的正统法学,如果不去有效地控制个体化的激情,处理好规范之中的价值问题,而将其演绎到极致,也可能成为法学的异端。
然而,我们之所以还要将上述那种法学流风称为“文人法学”,则是因为,作为当代中国法学的一种品流,它颇似中国古代的“文人画”一样,其作品的内容、样式或风格之中,往往也寄托了“志于道”而“游于艺”的志趣,寄托了传统文人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为此也可谓是最具有中国本色的一种法学,甚至也有可能为当今正面临着种种困境的中国法学,提供一处“诗意地栖居”的佳境。
笔者虽不敢妄称“文人法学”的典型代表,但作为当今中国的一介法律学人,一向也难以拂拭中国传统文人的某种情怀。而裒辑在此的篇什,尽管只是一些浅易的小文,卑之无甚高论,但多少也颇具“文人法学”的风味。为此,谨将这册小书冠名为“文人法学”,并将旧作《文人法学》一文纳入此篇加以修订,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