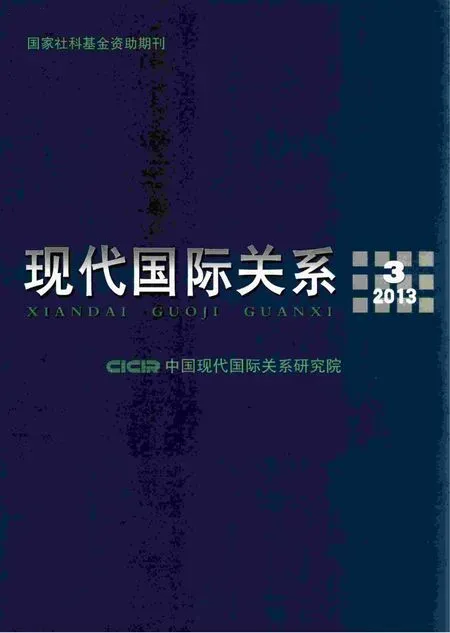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发展趋势
2013-12-18方金英
方金英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发生一起“暴力执法”事件:大学毕业生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在赖以谋生的摊位被取缔后自焚。布瓦齐齐浑身着火的照片很快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由此引发的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全国。10天内,统治突尼斯23年之久的本·阿里政权垮台。2011年1月25日,埃及爆发要求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的抗议活动。之后,动荡波冲击到也门、利比亚、巴林、沙特、叙利亚等国,迄今中东大变局尘埃远未落定。正如黎巴嫩政治分析家塔拉尔·阿特里希(Talal Atrissi)所预言,“我们正在向未知迈进。接下来,我们将见证各国内部各派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较量博弈引发的冲突、破坏、杀戮可能会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①Anthony Shadid,“In Arab summer,momentum hits uncertainty”,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ugust 26,2011.本文拟探讨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影响。
一
自近代西方世俗主义、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等政治思潮东渐阿拉伯世界以来,为实现民族富强和宗教复兴,阿拉伯世界出现过两次民族觉醒。其间,效仿西方世俗现代化和回归传统伊斯兰的路线斗争始终未绝,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的较量此消彼长。
第一次阿拉伯觉醒始于20世纪上半叶,历时一个世纪,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阿拉伯世界西化、世俗化揭开序幕。近代后期,在欧洲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侵略东方国家的过程中,处于东西方之间的阿拉伯国家首当其冲地成为欧洲殖民主义的重要目标。从英国统治下的埃及、科威特、巴勒斯坦等,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统治下的北非,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纷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伴随着殖民者的洋枪洋炮以及一批批穆斯林青年赴西方学习深造,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对阿拉伯世界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高举的旗帜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
许多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都受过西方现代教育,受到民主、立宪政府、议会政治、人权和民族主义等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所以,二战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相继独立的国家大行其道。传统伊斯兰政治理念基于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的政治忠诚和团结,现代民族主义则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而是立足于共同的语言、地域、种族和历史。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世界范围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中东地区承继历史的宗教与民族“二合一”忠诚让位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渐行渐远的复杂关系。
第二阶段:阿拉伯世界缓慢走上伊斯兰复兴之路。1967年阿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大败的惨痛经历、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反攻又以失败告终、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等,使阿拉伯世界逐渐陷入深刻的生存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和宗教信仰认同危机。在此驱动下,从1970年代起,伊斯兰教开始从被民族主义边缘化、被压制的状况中走向复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产生巨大威力,“伊斯兰认同”开始横扫阿拉伯世界。1981年埃及伊斯兰圣战者暗杀萨达特总统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兴起后,对“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成为198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主流心理状态,各国掀起镇压、取缔伊斯兰政党浪潮。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力推“民主改造”计划,阿拉伯国家被迫实行政府主导的有限改革,非暴力的伊斯兰政治、社会运动开始寻求通过争取选票以获得权力。在埃及、摩洛哥、土耳其、科威特、巴林、沙特、伊朗等国,伊斯兰政党及其候选人以主要反对派身份出现,在各种选举中击败世俗对手而胜出。在伊拉克2005年下半年的普选中,宗教性什叶派联盟获得275个席位中的128个;在2006年1月巴勒斯坦地区选举中,哈马斯以绝对优势击败世俗执政党法塔赫;在埃及2005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赢得1/5议席;在土耳其2002年11月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取得压倒性胜利,赢得议会多数席位363席;在沙特2005年选举中,温和伊斯兰主义者赢得麦加和麦地那两地市议会的全部席位。①[美]约翰·L·埃斯波西托和达丽亚·莫格海德著,晏琼英、王宇洁、李维建译:《谁代表伊斯兰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73页。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的法雷斯·布雷扎特(Fares Braizat)断言,“如今,伊斯兰分子来了,这种新型民族主义将是宗教民族主义”。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主义浮出水面。②Michael Slackman,“For more Arabs,Islam is the answer”,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ugust 21,2006.
第二次阿拉伯觉醒始于“阿拉伯之春”。这是一次伊斯兰民粹主义(Islamic populism)的回归。“阿拉伯之春”的发起者是一群满怀激情、勇敢无畏的年轻人,既不反西方、也不亲西方,既不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分子、也不是世俗主义者,他们表达的是呼唤民主和自由、摆脱家族统治、举行多党选举、增加就业机会的诉求。伊斯兰分子与同胞们一起参与到和平革命中,连部分伊斯兰激进分子也认识到应该给民主进程一个机会。埃及“伊斯兰组织”成员加马尔·赫拉里(Gamal El Helali)说,“过去,我们坚信使用暴力是实现变革的唯一途径,这次革命打开了和平变革之门。”约旦研究激进伊斯兰问题的专家马尔万·谢哈德赫(Marwan Shehadeh)说,“现在出现一种新认识,即抗议、示威等平民行动比武力、开战更有效。”③Michael Slackman and Mona El-Naggar,“The people’s radical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September 10-11,2011.随着革命的深入,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崛起,它们在突尼斯、摩洛哥、埃及通过大选上台执政,在也门、利比亚、叙利亚成为一支权重势力。
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打败发动“阿拉伯之春”的世俗青年运动和自由派政党,取得了选战胜利。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有关国家执政当局与世俗派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的冲突大于同伊斯兰分子的冲突。世俗派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派同政府在政治立场上相去甚远,其成员常遭安全部门监控甚至逮捕,其活动经常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在埃及,自由派组织举行政治集会的一切努力都被穆巴拉克政权扑灭,因为自由派被西方视为取代现政权的必然选择,而伊斯兰分子与政府之间不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只有权力之争。因此,在一些中东国家,尽管极权政府严厉对待伊斯兰分子,伊斯兰分子仍比世俗派、自由派享有更大的政治空间,甚至获准有限度地参加公职竞选。在埃及,萨达特1970年掌权后,即允许伊斯兰分子在大学校园公开活动,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由此得到迅速发展;他还通过宪法修正案,宣称“沙里亚法”是法律的“主要源泉”,埃及日趋伊斯兰化。穆巴拉克时期,埃及进一步伊斯兰化,伊斯兰政党能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在2005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获得共454个议席中的88个议席,但世俗派、自由派政党没有获准参选。④Hala Mustafa and Augustus Richard Norton,“Stalled Reform:The Case of Egypt”,Current History,January 2007.其二,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积累了组织经验,具有社会基础。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全境建立庞大的慈善网络,一向植根于草根穆斯林中。埃及有8100万人口,其中2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①Vivian Salama,“No Dictators Allowed”,Newsweek,December 10,2012.在众多政治势力中唯有穆斯林兄弟会身体力行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如每月为寡妇提供15美元救济,因而具有广泛影响力。而世俗派、自由派几乎无所作为。②Anthony Shadid,“Turning revolt to an advantag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tober 19,2011.其三,阿拉伯世界民众具有深厚的宗教感情。伊斯兰政党坚决捍卫伊斯兰社会、文化、宗教传统,明确表达真正的国民认同。突尼斯“复兴运动”执委会成员兼发言人阿布达拉·朱阿里(Abdallah Zouari)指出,突尼斯1100万人口中,98%为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情感根深蒂固”。③Scott Sayare,“Revived Islamist party’s muscle provokes worries in Tunisi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16,2011.其四,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为政坛新手,没有污点。政治分析家莫尼尔·菲拉姆(Mounir Ferram)指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突尼斯“复兴运动”、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等政党“都是政坛新手,没有欺骗过人民,表达民众真正要变革的呼声”。④Souad Mekhennet and Maia De La Baume,“Moroccans set moderate Islamists on path to lead”,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28,2011.因此,这些组织在“阿拉伯之春”中能够迅速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随着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的崛起,具有宗教威信、能够动员草根民众的新伊斯兰权力精英已在中东国家形成。他们因长期同世俗独裁政权进行血腥抗争刚刚走上政治前台,目前大都声称接受世俗国家原则,同时拥抱伊斯兰价值观。突尼斯“复兴运动”领袖拉奇德·加努西面对世俗派挑战,质问“为什么我们必然会走到阿富汗塔利班或沙特道路上?还有其他成功的伊斯兰模式可以效仿,如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尼模式,这些国家将伊斯兰与现代性相结合”。利比亚伊斯兰领导人阿里·萨拉比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支持多元主义和正义。利比亚人民有权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伊斯兰分子与世俗派关系牢固。”⑤“Islamists ready to share power in democratic Libya”,http://www.tribuneonline.org/commentary/20110916com7.html.(上网时间:2013年1月25日)这昭示了中东伊斯兰政治发展的前景,即如何让伊斯兰清规戒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是新伊斯兰权力精英面临的严峻考验。
二
由于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的崛起,中东地区无论是地区层面还是国别层面都在上演一场日益激烈的政治和宗教权力斗争。
首先,世俗派与伊斯兰分子之争。这一斗争由来已久,长远看将聚焦于发展道路和地区主导权之争,并且仍是中东冲突的主线之一。自20世纪40年代起,世俗派与伊斯兰分子之争甚或暴力冲突始终是阿拉伯政治的一个特点。从1970年代起,中东地区民众日益提出民主化诉求,伊斯兰分子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到2006年,在6个阿拉伯国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3/4民众支持民主,但存在着“伊斯兰民主”与“世俗民主”的立场分歧。21世纪头10年,随着各国经济下行和政权违背政治改革诺言,甚至世俗派内部也产生广泛而深切的不满,伊斯兰分子与世俗派的分歧开始缩小,甚至在抗议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和反集权统治等问题上协调行动。在“阿拉伯之春”初期,两者的分歧几近消弭,双方携手推翻了旧政权。目前,西化的世俗精英作为一方政治力量,大谈的是民主与人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教合一,因而脱离了他们声称所代表的穆斯林大众,没有从伊斯兰传统中汲取营养,影响力大不如前。伊斯兰分子作为另一方政治力量,则是坚决捍卫伊斯兰社会、文化、宗教传统;努力建立庞大的慈善网络,向需要帮助的民众施以援手;他们通过代价沉重的长期反独裁统治斗争获得了权力,拥有执政合法性。但他们处境困难:既要坚守伊斯兰信仰,又在民主进程、经济政策、对以关系等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⑥Tariq Ramadan,“Waiting for an Arab Spring of idea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tober 1,2012.
形势表明,伊斯兰政党不能独大。许多人认为,突尼斯和埃及的大选宣告“伊斯兰浪潮”的到来,但选举结果显示伊斯兰分子并未横扫整个中东政坛。在2011年的选举中,突尼斯“复兴运动”政党只赢得37%的选票。在埃及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自由与正义党”主导的“埃及民主同盟”(Democratic Alliance of Egypt)与“萨拉菲派”政党“光明党”(Al Nour)主导的伊斯兰阵营分获 37.5%和27.8%的选票;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当选为埃及总统,他只赢得51.73%的选票。同时,阿拉伯民众在宗教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国际共和党研究所(IRI)2011年3月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8%的突尼斯人主张宗教立国,44%的人主张建立世俗国家。同年8月,丹麦-埃及对话研究所(DEDI)和金字塔政治战略研究中心(ACPSS)的联合民意调查显示,44%的埃及人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46%的埃及人主张建立世俗国家。①Ellen Lust,Gamal Soltan,and Jakob Wichmann,“After the Arab Spring:Islamism,Secularism,and Democracy”,Current History,December 2012.
其次,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这仍将是未来中东冲突的主因与核心。“阿拉伯之春”后,伊朗与沙特关系的不确定性、脆弱性以及公开冲突的潜在性是海湾地区自两伊战争以来未曾见过的:双方对外政策转向激进,军备竞赛加剧,伊朗更是雄心勃勃地实施核发展计划,国内政治的外溢性增强;两国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博弈愈演愈烈。由此可以预见,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新月”(Shiite crescent)与以沙特为核心的“萨拉菲派新月”(Salafi crescent)两大新月地带的相互竞争,将释放出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东新一轮暴力冲突波。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穆斯林人口占90%,其中约84%为逊尼派,16%为什叶派。②Borna Zguric,“Challenges for democracy in countries affected by the‘Arab Spring’”,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Vol.23,No.4,October 2012.“什叶派新月”是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中东地区坚决反以色列、反西方势力在伊朗支持下缔结的政治、意识形态同盟。“什叶派新月”地带事实上始于1979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先后出现两伊战争、黎巴嫩真主党、海湾地区什叶派穆斯林政治化。专事海外隐蔽行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在“什叶派新月”地带影响很大,其职责主要是在代理人战争中向反对伊朗战略对手的团体提供培训和后勤保障,如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族反政府武装。过去10年里,“圣城旅”在伊拉克向各类反叛势力提供武器和军事教官,以便向驻伊拉克国际联军发动军事行动。
“萨拉菲派新月”地带出现于“阿拉伯之春”后,得到沙特的大力支持,覆盖从海湾君主国到地中海东部诸国再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在埃及,“萨拉菲派”政党异军突起,“光明党”等6个“萨拉菲派”团体在2012年1月大选中获得27.8%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突尼斯,“复兴运动”党魁拉希德·加努西在2012年11月明确表示,萨拉菲分子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民兵武装。他向“萨拉菲派”势力保证,政府要实施“沙里亚法”。③Souhir Stephenson,“Tunisia,a sad year later”,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1,2012.在阿尔及利亚、巴林、科威特、利比亚、也门以及巴勒斯坦,在沙特瓦哈比派大力支持下,“萨拉菲派”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治党派。沙特人不全是瓦哈比分子,“萨拉菲派”也不全是瓦哈比分子。不过,瓦哈比分子从根本上讲都是“萨拉菲派”。④Robin Wright,“The widening Salafi crescent”,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ugust 20,2012.
叙利亚沦为“什叶派新月”与“萨拉菲派新月”两大教派阵营厮杀的新疆场。联合国调查团在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坦承,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政治变革战已演变成一场“公开的教派”之战,将来自中东和北非的各路人马拖入厮杀疆场。叙利亚内战反映了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教派争夺。
境外“什叶派新月”势力大举介入叙利亚内战。目前,来自伊朗、黎巴嫩、伊拉克的什叶派携手力挺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伊朗向巴沙尔政权提供财政援助、外交支持、反游击战和骚乱控制培训以及武器装备;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巴沙尔政权提供“情报和顾问支持”。⑤Shaul Bakhash,“Iran’s Deeping Internal Crisis”,Current History,December 2012.黎巴嫩真主党2011年3月派出数千名战士奔赴叙利亚,充当巴沙尔政权进行城市战的战略、战术顾问。2013年1月,真主党进一步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派出真主党训练精良的特种部队帮助保卫巴沙尔政权。真主党还从黎巴嫩利塔尼河南部及贝卡谷地的什叶派村庄征召数千名后备役战士,以备叙利亚战场之急需。①Daniel Nisman and Daniel Brode,“Will Syrian bleed Hezbollah dry?”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anuary 31,2013.伊拉克什叶派参加叙利亚内战人数2012年10月以来不断增加。许多伊拉克什叶派日益将叙利亚内战——逊尼派多数反抗什叶派少数(阿拉维派)领导的政权——视同于为什叶派信仰的未来而战,将捍卫巴沙尔政权当成其“神圣职责”的一部分。②Yasir Ghazi and Tim Arango,“Syrian battles lure Iraqi fighter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tober 29,2012.
“萨拉菲派新月”的终极目标是使伊朗的影响边缘化。沙特一直向反巴沙尔势力提供武器和训练。沙特和卡塔尔同属萨拉菲派,“基地”组织等伊斯兰“圣战”势力也属于萨拉菲派。沙特的立场和政策使“圣战”势力渔翁得利,绝大部分武器援助落到了“圣战”势力而非西方支持的世俗反对派手中。③David E.Sanger,“Jihadists in Syria get arms sent to rebel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tober 16,2012.逊尼派穆斯林中许多人与“圣战”势力有联系。“美索不达米亚‘基地’组织”(Al Qaeda in Mesopotamia)分支“胜利阵线”(Al Nusra Front)在叙利亚反政府势力中起着关键作用。该组织成员人数虽少,但有勇有谋,重点袭击军事工事和油田重地。“胜利阵线”2012年初在大马士革、阿勒颇针对政府大楼发动自杀式袭击行动,造成众多平民的伤亡。境外资金越来越多地流入“胜利阵线”手中,使其能换取更多的武器、吸引更多的作战人员。该组织成员充满战斗热情,将叙利亚视为实现梦想之地。④Tim Arango,Anne Barnard and Hwaida Saad,“Qaeda offshoot plays vital role in Syria rebels’fight”,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ember 8-9,2012.
也门可能成为伊朗与沙特之间代理人战争的又一战场。也门两大政治团体——以胡塞族反政府武装为首的一派与以“伊斯兰改革集团”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也门西北部主要受胡塞族反政府武装控制。胡塞族是什叶派穆斯林,占也门总人口的1/4,聚居在也门-沙特边境,与伊朗互为盟友。2011年末以来,伊朗加大对胡塞族反政府武装的政治支持和武器援助,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向其提供Ak-47步枪、火箭弹等武器和数百万美元现金。也门主要逊尼派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改革集团”(al-Islah)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也门分支,得到沙特的支持。相应地,伊朗日益加大力度支持该党以外的也门政治势力以及南部地区分离主义势力。也门北部逊尼派部落领导人担心,伊朗与沙特在也门爆发一场代理人冲突的可能性上升,“我们甚至已不再称呼他们‘胡塞族’,而是‘伊朗的随从’”。⑤Eric Schmitt and Robert F.Worth,“U.S.says Iran is using arms and cash to expand influence in Yeme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rch 16,2012.
其三,逊尼派内部温和伊斯兰势力与保守的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博弈。它将决定未来中东政治伊斯兰的绿色深浅度。目前,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势力日益上升,它们力倡伊斯兰属性的民主价值观,认为伊斯兰教可以与时俱进,支持民主与宗教共存。⑥Richard Dearlove,“Violent Islamism has failed”,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November 5-6,2011.以“萨拉菲派”为代表之保守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也在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兴起,主张建立神权国家。⑦Anthony Shadid and David D.Kirkpatick,“Arab world turns to defining role of Islam”,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October 1-2,2011.它们认为,穆斯林民族国家、民主、妇女权利等是当今伊斯兰世界诸多问题的根源;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穆斯林就必须回归穆罕默德时代的生活方式,遵照《古兰经》过着朴素、纯洁、相互负责任的生活。“萨拉菲派”反对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教是通往美好现代生活大门”的理念,坚信“现代性与伊斯兰教真谛背道而驰”。⑧“The Salafi threat”,http://www.globaljihad.net/view_page.asp?id=2228.(上网时间:2013年1月25日)
“萨拉菲派”对民众的吸引力与穆斯林兄弟会迥异。穆斯林兄弟会由一群令人尊敬、取得瞩目成就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主导,常以恩赐态度对待选民,并称自己一直替穷人做事,但极少将自己当成穷人。在埃及,“萨拉菲派”主要由宗教人士组成,在诸多政党里唯有“萨拉菲派”候选人践行民粹主义。塞得港“萨拉菲派”第一候选人阿拉·巴黑伊(Alaa El Bahaei)说,“其他党派高高在上,而我们生活在草根民众中。”“光明党”主要发言人谢赫沙班·达尔维什(Sheik Shaaban Darwish)公开向民众喊话:“同胞们,我们‘光明党’创建者是草根民众的一部分。”许多选民,包括一些不认同“萨拉菲派”极端行为方式的人都表示,他们有明确的理由相信谢赫们理解他们的看法。这些谢赫们同穆斯林兄弟会一样,始终如一地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包括向穷人提供食品、药品。塞得港一所学校的员工叶海亚·赛义德说,“他们为人民服务,人们理所当然就认为,如果他们进入议会,会做更多善事。”塞得港以自由主义著称,但“萨拉菲派”超越自由派,赢得当地20%的选票。正是这种新型宗教民粹主义推动“光明党”及其盟友在2012年1月埃及第一轮议会选举中超越自由派,获得27.8%的选票,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竞争对手或潜在伙伴。①David D.Kirkpatrick,“Egyptian conservatives take populist tack”,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ember 12,2011.
“萨拉菲派”是最反西方、反民主的伊斯兰民粹主义势力,利用穆斯林民众情绪,妖魔化西方,反对民主变革,是影响阿拉伯社会稳定的重大消极因素。在埃及西奈半岛,萨拉菲分子发动恐怖行动反对埃及在西奈的主权。在加沙,萨拉菲分子向以色列发动火箭弹袭击。在突尼斯,萨拉菲分子充当“卫道士”,四处横行滋事,如袭击外国使馆、纵火焚烧警察局、洗劫艺术馆等。在利比亚班加西,2012年9月11日,“萨拉菲派”组织杀害美国驻利大使等4名美国外交官。利比亚萨拉菲分子甚至摧毁了当地苏菲派清真寺和圣陵。②“The Salafi threat”,http://www.globaljihad.net/view_page.asp?id=2228.(上网时间:2013年1月25日)
三
中东地区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的崛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未来中东国家政治形势和整个地区局势因此将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变化。
一是大变局后的过渡期注定动荡。中东分析家和学者大多认为,政治变革从来就是一个缓慢、混乱甚至充斥暴力的过程;期待历经数十年独裁统治的国家短时间内实现顺利过渡,那就太天真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东项目主任乔恩·阿特曼指出,“我们匆匆武断地下结论说,所有的过渡都应该顺利,那就太没有历史意识了。阿拉伯世界的过渡至少需要10年时间。”总部在伦敦的泛阿拉伯报纸《生活报》(Al Hayat)华盛顿站负责人乔伊斯·卡拉姆说,这些国家正“从一人专制或军人独裁向平民权力过渡,现在还很难得出结论”。③Anne Barnard,“Aftermath of the Arab Spring”,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February 2-3,2013.
中东地区政商领袖及许多西方人指出,大变局后各国政治稳定取决于经济发展。严酷的现实是:各国大搞贸易壁垒,不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中东地区无法形成自己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具有全球地位的国际金融机构,没有创新或教育中心,不易接受外国企业。其结果是,中东地区始终没有成为外国企业的重要投资场所,从而与全球经济隔绝,直至进一步远离经济全球化。譬如,2006-2011年,埃及吸引的外资只有50亿-100亿美元;突尼斯一年吸引外资不到20亿美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阿拉伯问题的拉什德·哈利迪坦言,如果不能保障社会正义和快速的经济成长,“阿拉伯之春”将走向失败。④Zachary Karabell,“Economic insularity imperils change in Arab world”,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6,2011.
阿拉伯世界存在“青年人口暴增现象”,失业问题严重。2010年,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30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60%左右。这支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惟有通过大量投资创造就业才能吸纳消化,才能使年轻人投身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成为“正资产”,否则就可能成为一支社会动荡力量。2010年,年轻人失业率在中东为25%,在北非为24%。这些人在看不到机会、无力掌控自己人生、无法从国家发展中受益时,就容易失去归属感,以致与社会脱节,走上极端主义和与政府对抗的道路。⑤Najib Razak,“The challenge of Muslim youth”,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ember 15-16,2012.对这些人而言,政治伊斯兰不能提供解决办法,就业的重要性超越信仰。
但是,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在埃及,革命重创了经济:终止了新的外国投资,破坏了旅游业,年经济增长率从革命前的5%降到2%以下,外汇储备缩水25%,许多普通民众反而丢掉饭碗。革命推动民众要求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而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却因革命受到削弱。埃及因此一直处于动荡之中。⑥David D.Kirkpatrick and Dina Salah Amer,“Egyptian revolution faces an economic test”,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ne 11-12,2011.在突尼斯,革命近两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失业率从13%上升到18%,75万人没有工作。一家小型出版公司老板卡利姆·本·斯迈尔指出,“在突尼斯这样的国家里,失业大军就好似一支军队。”而闹革命的“复兴运动”根本没有经济规划。相反,民众则持速成心态,“如同刚结婚一个月后就想有一个蓝眼睛的男孩”。实际上,突尼斯就业境况的改观需要3-5年。①Neil Macfarquhar,“Seeds of Tunisia’s revolt endur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ember 3,2012.于是,社会不满不断积聚。2012年11月底,突尼斯首都南部的锡勒亚奈(Siliana)要求就业和政府增加投资的抗议活动演变为持续数天的数千人暴力抗议活动,数百人在与警方的冲突中受伤。总统蒙塞弗·马祖基在电视讲话中承认政府“没有满足人民的期望”,担心动荡向欠发达的内陆城镇蔓延。所有阿拉伯国家都面临同样的恶性循环:政治动荡吓跑了投资者,而创造就业需要投资者。
二是伊斯兰民主将在中东大行其道。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哲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行为方式、道德规范和法律体系。1400年来,它既经历过繁荣时代的辉煌,也经历过衰微时代的屈辱,时至今日在伊斯兰世界仍发挥着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的功效。中东穆斯林民众既不想要宗教神权政治,也不喜欢世俗民主制,情愿选择第三种模式,即宗教原则和民主价值观共存。2011年涌入街头抗议浪潮的阿拉伯人特别是年轻人不期待建立宗教政权,他们认为“伊斯兰就是解放之道”还不够,“我们不需要祈祷、谢赫、大胡子,我们的教职人员已经够多了”。②Anthony Shadid,“In an Islamist stronghold,jobs now come before faith”,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February 16,2011.
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伊斯兰政党将走上务实的中间道路。随着中东国家选举的常态化,伊斯兰政党会不断增加,伊斯兰势力日渐分崩离析,因为它们都在争夺同一批选民的支持。由于争夺选民斗争激烈,没有一个政党能在民主进程中轻易独占鳌头,埃及和突尼斯情况已然如此,所有政党不得不面对现实,以便贴近广大选民。中东民众深信,伊斯兰教与民主在选举中可以携手并进。如果绝大多数人坚信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形式,那么伊斯兰分子就很难“劫持”选举,他们为了执政的合法性,就必须玩“民主游戏”。因为民众的理念向中间回归,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突尼斯“复兴运动”都处在这样的回归过程中。③Borna Zguric,“Challenges for democracy in countries affected by the‘Arab Spring’”,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Vol.23,No.4,October 2012.
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未来政治发展将呈现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交互影响、交互融合的复杂趋势,而不是简单的伊斯兰化。一方面,伊斯兰力量的得势与其自身的温和化、世俗化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屡受打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突尼斯“复兴运动”,对其原来建立政教合一国家、坚持暴力斗争等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的改造,积极融入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等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内容,走上通过合法选举谋取政权的政治参与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东政治伊斯兰化又何尝不是伊斯兰力量的世俗化?!世俗化和伊斯兰化仍是中东政治光谱的两个主轴,只是两者从过去相互排斥的两条平行线走向了交叉与融合。④“世俗与宗教角力: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不会全面伊斯兰化”,穆青资讯,http://www.muslem.net.cn/bbs/portal.php?mod=view&aid=8796.(上网时间:2012年7月27日)另一方面,中东民众史无前例地满怀国家主人翁意识。他们有能力提出诉求,并在独裁政权废墟上建立新的民主制度,以实现公民权益。阿拉伯公民在历史进程中不再像过去那样充当旁观者而是扮演参与者,“公民主权”(citizen sovereignty)意识开始深入人心。⑤Rami G.Khour,i“Building on the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ne 7,2011.2013年1月25日,反对穆尔西及其穆斯林兄弟会的左翼人士汉丁·萨巴希(Hamdeen Sabahi)就表示,“我们的革命还在继续,我们反对一党独大,我们对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国家说‘不’。”在苏伊士运河沿岸三大城市苏伊士、伊斯梅利亚和塞得港,数千名抗议者上街反对穆尔西政府。⑥Reuters,“Egyptians and police clash 2 years after revolt”,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anuary 26-27,2013.此外,中东国家的军队日益倾向世俗化。这对伊斯兰力量的政治崛起一直并将继续构成巨大的牵制。○